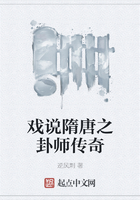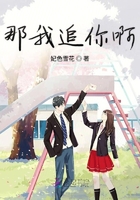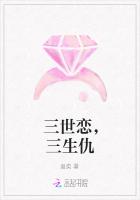风卷黄沙,驼铃传响。
道旁的榆柳枝梢早已枯干,随着变换不停的风向摇摆着。沿街寥寥散落几个货摊,摊上俱都是些手工粗糙的日用物件。行商的波斯胡赶着驼队远远地从街的那一端经过,他们已有多时未曾来到这座边关小城。五六个拖着鼻涕、衣衫破旧的大小孩子跟在商队之后,看热闹之余,更期冀着高鼻梁大胡子的异域商客扔下几枚糖果、几个零钱。
驿站伙计赵含生正蹲在门外偷懒犯闲,却见十几名军士披着灰扑扑的斗篷、骑马缓缓而来,径行到他面前。他们各自下马,斗篷里显出刀鞘、角弓的形状。
闻得人来,一个身形干瘪的女人走出门,正是老板娘秦氏。她身上红色的袄子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洗换了,各处蒙着污渍,倒与她下身沾满泥尘的灰色裙裤颇为搭调。秦氏与来客招呼几句,便不耐烦地大声喝令赵含生将马匹牵到马槽边,腰胯一转,将十几个客人引进门里。
赵含生栓好马,走进门厅,见客人们纷纷解下斗篷,“噗噗”地拍打着,逼仄的屋里满是飞扬的尘土。领头一个军士将腰上的名牌向秦氏亮了一下,秦氏没好气地安排了住房,窥着一行人各自回房了,便抄起硬梆梆、油腻腻的一块抹布,没头没脸打在赵含生头上,骂道:“军爷住店不给钱,你还搁那儿呆站着,招老娘嫌么?他娘的,今天来几个军爷,明天又来几个军爷,各个都似这般白吃白喝,不如老娘把店门关了,也操了家伙,去做个丘八好了!”
赵含生听了暗自发笑,又不敢出声,只得拿起抹布,装模作样地揩着桌子。他认得领头那个军士上个月来过,只是这次见他,额上似多了道伤痕。队里的人却大多是些生面孔,有一个黑袍人满脸刀疤,煞是可怖,赵含生只向他远远望了一眼,便再难忘记他的模样。
本来按照太仆寺的规矩,军士来到驿店里,只需记下姓名军职,自不用另付银两;店家记了费用,回头去找郡里销账便可。只是这几年来,似乎住店的客人里,竟有一半都挂了个军牌。一次有个肥头大耳的来住店,将一枚小牌儿在赵含生面前倏地一晃,便欲拿笔登记,赵含生较真,要仔细看他名牌,他竟暴跳如雷,掴了赵含生一掌不说,还砸了店里柜台。县衙遣人来查看一番,只推说是军中事务,便再没有下文了。
而秦氏报到郡里的账目,拿回手里的,最多也不过只得三四成罢了。赵含生想起方才见到斗篷下的刀弓,又想起那个满面刀疤的黑袍军士,暗道今日来住店的这一队人,倒是这几年来难得一见、正经带着军旅杀气的。
赵含生听往来的客人说起,如今胡人厉害得紧,出关的商队往往被劫杀在荒原上、尸骨无存,连关外六座汉军大营都被胡人围了,也不知还能支持到几时。也难怪只有波斯胡的驼队还敢出关行商,赵含生曾见过他们载运的货物,里面除了布匹、珠宝之外,竟还有不少刀枪军械,大概都是卖给胡人的。
赵含生还记得,前几年可不是这般光景。当日军神李同臻领着五百名铁羽军自此出关,每名军士肩上荷着精钢打造的、船桨一般的两刃刀,足有一人高、一尺宽,刃口反射着耀眼的日光,将这座终日灰头土脸的小城照得光芒眩目。每一列马匹也俱都毛色精纯,没有一匹驳色;马蹄轰隆隆踏过平日里还觉宽敞的长街,将一块块石砖都踏成了齑粉。一名铁羽军士策马走到街边,唤张铁匠过来,扔下一锭银两,让钉了新的马掌,至今张铁匠与人喝酒时,还时常吹嘘此事。
正遐思着,一个面目清秀的年轻军官走到柜台前。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函、一个灰色布囊,向秦氏道:“劳驾,我要将这信函寄到京里,呈卫尉寺卿;再将这布囊寄到吴郡余姚县,需要多少钱?”
秦氏瞥了他手中物件一眼,又打眼瞧了瞧这军官样貌英俊、礼数周到,便好声好气地道:“信函是寄官件,那就不花钱了;布囊是寄到家里去的吧?那就是寄私件了,得要四百文钱。”说着掂了掂那布囊,只听得叮当响声,想必里面都是些值钱物事。
那军官面露窘迫之色,道:“我拿不出这许多钱,可否算便宜些?”秦氏揶揄道:“哟,攒下这一袋子金银珠宝去讨好家里娘子,还拿不出四百文钱么?”赵含生见那军官脸上浮现几分怒色,从秦氏手中接过布囊、紧紧攥着,却不肯打开。
正在这时,有人将几枚铜钱拍在桌板上,推到秦氏面前。抬头看去,竟是那满面刀疤的黑袍人。秦氏与赵含生俱都不敢去看他脸,急急把钱收了,便各自低头忙碌。却没听那年轻军官向黑袍人说个谢字,他二人各自一言不发地回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