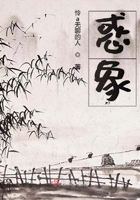胜吉十七年十一月初九,皇宫内城政事堂。
王安石仔细看了吕惠卿主持撰写的变法章程,然后递给参知政事秦源,笑着对吕惠卿说道,“吉甫的字越来越秀雅了。”
吕惠卿,字吉甫,胜吉六年丁酉科进士,与苏轼、苏辙、程颢、曾巩等人为同年。八月王安石组建制置三司条例司时,吕惠卿正任集贤殿校勘。王安石因和吕惠卿友好,因此向柴勐进言推荐吕惠卿,认为吕惠卿的贤能岂止在当今之人中出类拔萃,即使是前世大儒也不是能轻易比得过的。学习先王的道理而能用于今世的,只有吕惠卿一人而已。于是,柴勐便任命吕惠卿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为王安石、秦源之下,参与胜吉变法的第一人。王安石事务繁忙,秦源多不理变法之事,有关新法的解释及章程的撰写,便由吕惠卿一人承担。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度利害官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人虽然也有才干,但多安排至各路进行胜吉变法的督促巡查,于胜吉变法之大局便没有吕惠卿更为清楚,昨日众人商议到深夜,见吕惠卿考虑周祥、贴合实际,便公推吕惠卿执笔完成了各路变法章程。岂料,王安石对此章程并不满意。
当今官家颇喜书法,翻阅大臣奏折时,如遇书法新奇、赏心悦目之人,往往会加上朱批予以褒扬,长此以往,大臣以勤练书法为第一要务。吕惠卿之前担任集贤殿校勘,正是给皇帝编校书籍的官职,所以写的一手好字。王安石赞扬吕惠卿的文字,而非其中的内容,显然是对众人用一夜工夫写的章程不甚满意。
吕惠卿满心期待王安石的赞誉,结果得到了王安石委婉的批评,大座的皆是人中龙凤,一时间吕惠卿面子倒有些挂不住,脸色一红道,“敢请石相指教。”
王安石注意到吕惠卿的神情,也没有解释,看秦源看章程看得仔细,便问道,“秦相,你对吉甫此章程怎么看?”
秦源看得入了迷,过了一息才回过神来儿,“石相,吉甫大才,吾等不及也。”
王安石看了秦源一眼,略有些失望,但却没有表现出来,他叹了一口气道,“吉甫,汝之苦心,吾自然知晓,但若依诸位之章程,大周这二十八路变法得三年才可见其效。”
“石相,若可使我大周顺利施行强国利民之法,三年似也不多。”
“可我大周却不能再等三年,西夏、北辽畏我朝强势,兴兵只在这一两年,如我大周不能革弊鼎新、攻坚克难,则蛮夷兴兵之时,便是我黎民涂炭之日。”
“石相言重了吧。”秦源忍不住说道,出使北辽换来和平是他的功劳,他可不能允许被王安石轻易的抹杀。
“你看看这份折子,昨日刚到的六百里加急。”王安石从书案上捡起一封书信递给秦源。
秦源取来一看,却是幽蓟路制置使赵谦的奏折。秦源略微皱眉,打开折子,只看了一眼,便脸色大变,惊疑不定地问道,“这耽罗国与我大周何干,为何辽国责我大周毁约。”
“赵谦也没有耽罗方面的消息,只是北辽扰我边境,擒住辽人斥候才知道大概。耽罗乃北辽藩国高丽国所辖,今年突然反叛,高丽征缴时,说是被我大军禁军击溃,全军覆没。去年四州之战,有二万二千兵丁不知下落,现下看来,是被匪教掳到耽罗了。”
“可恶!”秦源神色复杂地说道,不知道他是针对北辽,还是匪教,还是沈括?“我等不如面见陛下,遣使臣前往,陈说详情利害。”
“北辽岂是因高丽事与我大周交恶,实乃我大周扫平陇右、河湟,击退西夏,使北辽畏我朝变法之功,欲攻我大周,以缓我变法之势也。”
众人默然。
“为今之计,必须快刀斩乱麻,皇亲国戚、权臣勋贵,值此国家存亡之计,应当知道取舍,况且,清丈土地,一亩只取税一斗,不及其利之一成,有何不舍?搜检隐户,一户仅缴纳四百文赋税,于乡绅富豪而言,仅是九牛之一毛。然国家有粮才能养兵,有丁才有兵源,以一家一户之微利换千秋万世之太平,此乃陛下之意,亦为吾等之计。”
吕惠卿等人的章程正是考虑到变法将触动到皇亲国戚、权臣勋贵以及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所以才拟定了一个循序渐进的策略,通过宣传、转化、引导等策略让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和佃户的权贵阶层逐渐接受。而王安石的决策则是动用国家的力量,在京畿路及二十八路强制推行。这么一来,变法派将得罪难以尽数的官绅,就算是他们认为改革势在必行,也不愿意直面士大夫的怒火。
吕惠卿硬着头皮说道,“是吾等考虑不周,变法确实应按石相的意思来办。”
王安石点点头,变法之事交付吕惠卿等人办理,自己把关即可,但军国大事却只能自己拿主意了。想着北辽和耽罗的军务,书案上一叠书信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好友司马光的来信,两天之内写了三封,洋洋洒洒三千言,他忙得没时间回信,如今倒有一处置方法。
片刻之后,王安石与秦源在留翠园见到了柴勐。在王安石的建议下,柴勐同意派司马光出使北辽,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说明耽罗之事与大周无关,攻击高丽的军队系流窜至耽罗的反贼;二是大周欲与北辽结百年之好,可增开槯场;三是为表示诚意,愿岁贡白银二十万两,丝绢十万匹,棉布二十万匹。起初柴勐并不同意第三条建议,但王安石向他解释了以这些浮财换取北边的安宁,以便于大周集中力量进行变法,平定西夏后,柴勐便不再坚持。毕竟这几十万贯的财货在北辽看来是一笔巨资,足以证明大周的诚意,但对于大周而言,还不及变法四路新增收益之十分之一,只要变法施行顺利,一切都会应刃而解。至于皇亲国戚、权臣勋贵从腰包里抖一些芝麻出来,在柴勐看来更是理所当然之事,没有国家、军队的保卫,皇亲国戚、权臣勋贵的利益谁来维系?总不能只让皇帝和百姓付出,皇亲国戚、权臣勋贵却一毛不拔吧。
~~~~~~
秦源回到秦府后,立即把秦林唤来。
秦林心怀忐忑地走进正堂,只见秦源和颜悦色地望着他,忙上前行礼。
“贤侄,这两日吃住如何?”
“甚好,大伯。”
“有什么取用,自寻秦管家,吾已安排,不必见外。”秦源随口抚慰了两句,然后步入了正题。“昨日,吾与贤侄聊及匪教与沈括之事,不和道贤侄怎么看?”
秦林有些不明所以,试探着问道,“小侄虽有心杀贼,但如大伯所说,现在或许还不是时机,需要徐徐图之。”
秦源笑了起来,“现在却有一个好机会。”
“请大伯示下,小侄必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哦,只是不知贤侄与匪教关系如何?”
秦林心如电转,以为秦源想让自己当奸细或招抚使,急忙道,“大伯明见,匪教杀我亲父、兄弟,与我有杀父之仇,我与匪教不共戴天;匪教最防叛逃,对叛教之人往往祸及家人,小侄的养父一家已被匪教全部屠灭了,虽然小侄在匪教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兵将,但也人人知晓,只怕一旦露出风声,小侄性命便也不保。”
秦源沉思了一下,“那如果有机会剿灭匪教呢?你可愿意?”
秦林心知现在朝挺无力对抗匪教,但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道,“小侄愿意。”
秦源喝退左右,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如果这个机会需要你放弃名节呢?”
秦林不知道什么机会能和名节相关,但他也知道如果此时退缩,将永远不可能得到秦源的信任,一念至此,一咬牙道,“大伯!只要报了家仇,个人荣辱算得了什么!”
“好!好!我秦家有后了!”秦源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看着秦林低声道,“如今,匪教势大,官家欲仰仗其势与辽国相抗,官兵无法讨伐匪教,但辽国却可以。匪教立教之初便明言天下,占四州之地是为救边民于危难,为与西夏辽国相抗,边地愚民深信之,耽罗原为大辽藩国高丽之属地,今匪教既夺高丽之地,焉能不与辽国结仇?况且匪教本就与辽国势同水火,辽国早欲除之而后快。如今,辽国袭扰我大周边地,似试探我大周的军力动向,若我大周意欲与辽国相抗,辽国必勾联西夏犯我大周,若我大周无意与辽国相争,辽国将会遣大军先铲除耽罗后患,如此,我秦家大仇可报一二。”
“朝廷欲派翰林学士司马光出使辽国,与辽国结好,以专图西夏。此行必获成功,但吾却不愿乐见其成。”秦源顿了一下,“吾欲让贤侄出关外,持我书信面见辽国北院大王耶律乙辛,让辽国继续攻击我大周,甚至将司马光扣留在辽国,不知贤侄可愿行否?”
秦林脑中仿佛炸响了惊雷,这可是通敌之罪,满门抄斩也还罢了,这可是要遗臭万年之举,“大伯?何以至此?司马学士出使成功,我秦家大仇便报了一半,为何反助辽国攻我大周。”
“我与辽国北院大王耶律乙辛有旧,大周与辽国此时应该休战,但促成此事的却不应是司马光。”
秦源不动声色,但秦林心中却充满了惶恐,为了一己之私,便将国家大事置若玩物,怎么说也不象是宰辅之所为。
“北院大王耶律乙辛权倾朝野,辽帝耶律洪基虽平定耶律重元之乱,但其胸无大志,只愿守成,辽人有‘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的谚语,吾观辽国动乱只在这几年之间。辽国已乱,我大周焉能置身事外,恐怕大周社稷危矣。”
秦源已位列宰辅,从他口中说出这番话,便有了谋权篡位的意思,可是大周不比一百年前五代十国时期,如今天下承平已久,百姓感念官家恩德,上下齐心,岂是可以谋反之时。秦源敢当着秦林的面说出此番话,自然不怕秦林走露了风声,如果秦林一言不合,只怕今天便会没了性命。秦林浑身颤抖起来,瞪大眼睛道,“大伯,此事非同小可,小侄烂命一条,侥幸才从耽罗逃得性命,既使身首异处,也无有亏损。但是大伯已位居人臣之首,何苦行这不可能之事。”
“不可能?!”秦源冷笑道,“如果辽国出兵相助呢?”
“此岂非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之举?”
“贤侄谬矣,辽国兵锋之盛,犹胜我朝,辽帝耶律洪基有意结好我大周,才保得十余年太平,若耶律乙辛夺位,举兵南下,以我朝官兵之疲敝,必不能敌,损失何止燕云之地?当今官家穷兵黩武,攻取河湟,让西夏引我大周为大敌;改变祖宗成法,士大夫无不引以为恨;宠信王安石、沈括之类的佞臣,致使百姓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柴家已失国运、官心、民心,若江山糜烂,匪教举手之劳,便可夺了柴家天下,此时,吾等莫要说报仇,连性命亦不得保,匪教杀了多少官兵,贤侄应当比我还清楚。”
“那辽国北院大王夺位也不是一朝一夕可成之事,大伯,我们秦家全系于你一人之上,这么做,太冒险了。”
“也没有让你怎么做,只是让大周使臣换个人而已,吾取代司马光出使辽国成功,枢密使一职,官家便不再吝啬,王安石一刚直执拗之辈,迟早要被官家罢免,界时,凭借吾在大周官场所积累之人脉,整个朝廷便全是我的势力。熙河军、秦凤军、延庆军、幽蓟军、新云军传一二文臣即可成为我秦家之亲军。耶律乙辛能做成的事,吾未必做不成,只是需要暗中准备罢了。”
秦林明知秦源想的太简单、太容易,但事已至此,稍不注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任务,以博个万一的前程。秦源见秦林应了,也非常高光,这番话憋在心里也有好几年了。秦求不堪与之议事,门生故吏没有亲近到谈论心事的地步,这秦林毕竟是秦家的子侄,造反之事,自然是同进退、共生死。秦源见秦林失魂落魄的样子,不禁笑道,“贤侄何必忧虑如此?昔日楚霸王见秦始皇车驾而生取而代之之念,汉高祖见秦始皇车驾而生大丈夫当如是之感,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事有不成,唯死而已,何须如此做女子形状?”
秦林面色一红,心中已有了定计,他微微一笑,对秦源说道,“大伯所言极是,大伯能将此等大事与小侄相商,小侄心领大伯恩情,敢不效命,然有一事,事关大伯私事,吾却不愿相瞒。”
秦源一愣,微笑道,“私事?贤侄且道来。”
“公子与姨娘恐有染,大伯难道没有察觉?”然后秦林把前天晚间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告给了秦源。秦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然后轻咳了一声,对于这个独子,他可真没办法,待回后院细问于氏,再做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