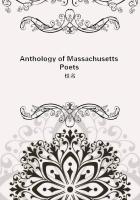欧阳翠冷笑道:“好,我就去看看,他究竟是怎样的……”
邢彬连忙接口道:“夫人千金之体,怎可轻易安迎接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
说到这理,突有所想的“哦”了一声道:“王二,你问过那人的姓名来历没有?”
门外语声道:“回邢爷,问过,他说我不配问。”
邢彬哼了一声,轻向欧阳翠说道:“夫人,还是我先去看看。”
“也好。”欧阳翠点头接道:“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可不能大意。’”
“我知道……”
说着,己自门而出,和门外那个叫王二的劲装汉子,向外匆匆走去。
但这两位刚走,一个面带纱巾的青衫文土,己缓步走进欧阳翠的房间。
欧阳翠入目着下,不由突的意起,注目问道:“你……你是谁?”
青衫文士笑了笑道:“我另换了一件青衫,却就是大门外那个‘骑白毛驴的黑衣人’。”
欧阳翠一皱眉头道:“我是问你姓甚名谁?”
青衫文士道:“我暂时还不想告诉你。”
欧阳翠哼了一声道:“不说.就算了,我问你,大年三十,深更半夜,擅闯人家内宅,是何道理?”
青衫文士的蒙面纱巾微微一扬道:“我,至少有三个理由。”
欧阳翠冷冷一笑道:“好,你就一项一项的说吧!”
青衫文士点点头道:“第一,我是一个有家归不得,也等于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此行,本来就是到这儿来投奔一个亲戚。”
欧阳翠含笑接道:“是投奔白永昌白老头局主?”
“不错。
“也是白局主的内兄?”
青衫文士冷然接道:“别自作聪明,我与白局主是何渊源,与你不相干。”
欧阳翠苦笑道:“好,我不问就是,现在,请说第二个理由。”
青衫文士道:“第二,我是追踪白毛驴的原主,听说他也投奔在这儿。””
欧阳翠反问道:“就是那个长的一付五岳朝天面孔黑衣人?”
“不错。”
“嘿,这个人,倒委实也投奔在这里。”欧阳翠含笑接道:“他的白毛驴,不是一百两银子,押给你了么?”
青衫文士苦笑道:“这个交易,我上了当,所以特地追来退货。”
欧阳翠道:“那白毛驴非常名贵,百两银子,可算得上非常便宜,为何还要……”
青衫文士接口苦笑道:“话是不错,可是它不让生人骑,花又不忍用武力去对待它……”
说到这里,邢彬已赶了回来,一眼看到那青衫文士,跟在他后面的王二,连忙抬手一指道:“就是他……”
邢彬目注青衫文士,沉声问道:“瞧你这摸样,也该算是读书人,却为何深更半夜,擅闯人家内宅?”
青衫文士慢应道:“我高兴。”
“好,”邢彬冷笑一声道:“我也高兴打人!”
话出招随,“呼”的一声,一拳击向青移文士的左肩,但他的拳势才出,眼前己失了青衫文士的踪影;而他的背后,却传来一声轻笑道:“区区在这儿!”
邢彬心头一惊;突的转过身来,膏穆实力却叉冷笑一声道:“别紧张,我还不屑出手教训你。”
邢彬脸色铁青的恐喝一声道:“有种,你就别躲。”
欧阳翠连忙沉声喝道:“邢彬,退过一旁!”
邢彬只好悻然退过一旁,并冷笑一声道:“这笔帐,我们待会再算。”
青衫文士笑了笑道:“待会,我一定成全你……”
欧阳翠正密接道:“阁下,继续你方才的话题吧!”
青衫文士微一沉思道:“你帮我想想看,像这样的情形,我不退还给他,岂非成了冤大头。”
“有理。”欧阳翠接问道:“第三呢?”
青衫文士道:“第三,我在半路上遇到一个打闷棍的小毛贼,这位仁兄,也算是倒霉,大年夜,不但没发利市,反而挨了我一顿打,也不知是我出手太重,还是那小毛贼太不中用,竟然无法行动了,像这样的天气,如果我丢下他不管准会活活冻死,所以我只好自认霉气,带着他走……”
欧阳翠笑问道:“想不到你还有一付菩萨心肠,只是,白毛驴既然欺生,那个小毛贼,你是怎样带着他走的。”
青衫文土道:“我把那人绑在驴背上,那白毛驴显然欺生,但对那个等于是活死人的小毛贼,却并不反对,那可以是‘物以类聚’,同了一个“毛’字之故吧!”
欧阳翠一皱眉道:“你对那个小毛贼,好像成见极深?”
青衫文士道:“它可以这么说。”
欧阳翠道:“即然如此,你又何必带着他同行?”
青衫文士笑了笑道:“待会,你就会明白的。”
话锋略微一顿之后,又轻轻一叹道:“你想想看,我牵着一头中看不守用的白毛驴,冒着狂风大雪,好容易走到这儿,却遇上你们那个狗仗人势的家奴,给我闭门羹吃,你说,我该不该光火?又该不该打人?”
欧阳翠笑了笑道:“他没告诉你,白家已经搬走了。”
青衫文士道:“就是因为投亲不遇,才更使我光火啊!”
欧阳翠冷冷—笑地:“如果阁下真是为了投亲而来,倒真值的同情。”
青衫文士幛面纱巾微微一扬道:
“夫人,能否请派个人,将那只白毛驴牵到草房中去,还有,那个小毛贼,也请带到这儿来……”
欧阳翠截口冷笑道:
“你说得那么一厢情愿,好像人家非接待你不可似的。”
青衫文士笑道:
“大家都是出门人嘛!何处不能予人方便,何况,那小毛贼,如不带进来,可快要冻死了哩,大年三十,弄出人命来,可不太好啊!”
欧阳翠低声一笑道:
“这几句话,还能勉强听得进去,只是,那个小毛贼,你要带进来干吗?”
青衫文上漫应道:
“我还有话要问他。”
欧阳翠点点头道:
“好……王二,你去将白毛驴牵到马房中去,那个小毛贼也带到这儿来。”
“是……”
王二恭应着离去之后,青衫文士却又扬声说道:
“王二,我警告你,别惹那白毛驴!惹翻了他,你可吃不消不远处,传来王二的一声冷笑,却没答话。
欧阳翠卸向邢彬笑了笑道:
“邢护法,还是你去辛苦一趟,顺便将小毛贼带到这儿来!”
“好的……”
邢彬恭应着离去之后,欧阳翠才向青衫文士媚笑道:
“现在可以请教尊姓大名了吧?”
青衫文士幽幽地一叹道:
“风雪漫天,归程何处?你就叫‘风雪未归人’吧!”
欧阳翠‘哼’了一声道:
“这名字倒是非常别致,不过,未免太颓唐了一点。”
青衫文士漫应道:
“是么!我自己倒不觉得。”
欧阳翠皱眉自语着:
“‘孤独客’,‘风雪未归人’,倒算得上是无独有偶。”
青衫文士又轻笑一声道:
“夫人,深更半夜的,我不便要求酒食,坐位总得赏我一个吧?”
欧阳翠掩口媚笑道;
“真是失礼得很!只顾说话,却怠慢了佳宾。”
微微一顿话锋,才微笑接道:
“‘风雷未归人’请坐啊……”
她的话声未落,门外却传来邢彬的怒喝道:
“大人,快宰了那匹夫!”
欧阳翠一楞道:“什么事啊?”
“你瞧!”
随着这话声邢彬己像一阵风似地,卷入室内,臂弯中还托着一个脸色苍白得有若死人的中年人。
欧阳翠没加思索地接道:“这就是那个小毛……”
“小毛贼”的“贼”字尚未说出,却突然俏脸一变地,话锋一转道:
“这……不就是万俟使者么?”
原来这个“小毛贼”,就是那位“灭绝神君”手下,四大使者之一,亦即“江湖四大恶人”中的”冷面人屠”万俟剑。
但目前,这个有“人屠”之称的恶人,不但穴道被制,而且负有不算轻的内伤,兼以又在风雪中冻了那么久,尽管他武功有根底,不致有生命之虞,但要想复元,则恐非一两个月所能奏效的了。”
青衫文士似乎楞了一下道:
“怎么?这个人,也是你们的人?‘使者’这个职位可不算低,怎会做劈径小贼呢?”
欧阳翠冷冷一笑道:
“阁下,装胡佯,也得适可而止!”
邢彬将手中的万俟剑向旁边坑上一放,一面恨声接道:
“夫人,邢彬请命一战。”
“不!”欧阳翠冷然接道:
“现在,救人要紧,而且,我那岁尾年头,不动刀兵之旨。一切过了明天再说。
接着,目注青衫文士淡淡一笑道:
“阁下,你那位“天涯孤独客’朋友,可能已经入睡,我派人送你去他们隔壁安歇如何?!”
青衫文士轻笑一声道:
“夫人,你错了,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天涯孤独客’,所以,我已不必同他住在一起。”
欧阳翠道:
“你们认不认识,我不愿过问,但至少你们之间,曾经见过面,还做过一次交易。
“交易?”青衫文“哦”了一声道:
“夫人所说,就是那位将白毛驴押给我射黑衣人?”
欧阳翠道:
“对了,现在你是否愿意同他们住到一起去呢?”
青衫文土道:
“不!我自有住处,有关退货之事,也到明天再谈。”
欧阳翠注目问道:“阁下准备何往?”
青衫文士笑道:
“再有个把更次,就天亮了,我还能住到那儿去呢?”
欧阳翠笑问道:
“那你方才,如何说另有住处?”
青衫文士道:
“我所说的另一个住处,也在本府之中,由这儿东行,绕过一个荷花池,不是有一幢精致的静楼么?”“不错。”欧阳翠注目接问道:
“阁下对这儿的情形,好像比我还要清楚?”
青衫文士道:
“可以这么说,而且,我还知道,那静楼本来是白敏芝姑娘的香闺。”
欧阳翠笑了笑道:“这些,是否也另有解释?”
“当然有。”青衫文士又点点头道:
“那是因为你是鹊巢鸠占的外人,而区区我,却是白敏芝姑娘的表兄……”
欧阳翠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接着,又歉然地一笑道:
“可借你迟来一步,那静楼,现在是我自己起居之处。”
青衫文士轻轻一叹道:
“那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就住这一间吧!”
欧阳翠抿觜一笑道:
“不管你是佳宾,还是恩客,即然己提出要求来了,我这作临时主人的人,自不能太自私。”
微微话锋,扭头低声喝道:
“阿琴,送这位贵客,去静楼安歇。”
“是!”
随着这一声娇应,隔壁房间中,走出一位妙龄青衣侍女,向着青衫文士微笑说道:
“这位相公,请随我来。”
说着,扭着水蛇腰,当先向外定去,欧阳翠又扬声说道:“阿琴,吩咐厨房,准备精美点心,给贵客宵夜。”
青衫文土边向外走边笑道:
“倒真有点‘宾至如归’的味道,在下谢了……”
那妙龄侍女将青衫文士领到那静楼中一间起居室中之后,才笑问道:
“爷……是否要准备香汤沐浴?”
青彩文土道:“不必了,出门人,那能那么讲究。”
妙龄侍女掩口媚笑道:“那么,婢子去替您端点心来。”
青衫文士仅仅“唔”了一声,他的注意力,似乎完全贯注在这房间的陈设上。
这房间的陈设,华丽中不失典雅,而且,还继续漫着一股如兰似麝的淡淡幽香,其为白敏芝姑娘所住的香闺,那是不会错的了。
隔着一座花园,就是“天涯孤独客”与胡玉二人,所住的客房,虽然地离水算近,但透过窗口,仍可看到那客房中所透出的微弱灯光。
青衫文士没来由地,忽然发出一声轻叹,他一拳将案头烛火击灭,又立即将它点燃起来。
可是,当他这房间中的灯光,灭而复明之后,那“天涯孤独客”所住的客房中的灯光,却忽然熄灭了,而且,熄灭之前,就没复明。
当然,这情形,显然有点奇怪,但那位送他来的妙龄侍女己下楼而去,不曾看到,至于暗中是否另外有人看到,那就不得而知了。
盏茶工夫之后,那妙龄待女端着一个食盒,走了进来。
食盒中,有四色精美的点心,四盘腊味,和一壶烫好的酒。
那妙龄待女将食盒中东西,—一搬上一小桌上后,才嫣然一笑道:“爷!没有什么吩咐么?”
“没有了!”青衫文土挥挥手道:“你回去休息吧!”
妙龄侍女目睁一笑,翻若惊鸿地,一闪而逝。
青衫文士低声自爱着:“即来了,则安之,且填饱肚皮再说说着径自行斟好满杯美酒,端起来,就向唇边送去。忽然,门外传来一声娇笑道:“喝不得!”
青衫文士停杯讶问道:“为何喝不得?”
门外娇语笑道:“你,只身孤剑,身处龙潭虎穴中,就不怕这酒食之中,下有毒药么?”
青衫文士呵呵一哭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这酒食之中,纵有穿肠毒药,又何惧之有!”
说完,举林就喝,一饮而尽。
一声娇笑,欧阳翠己穿窗而入,拇指起翘地笑道:
“有种!这一份胜概豪情,令人由衷敬佩。”
青衫文士笑了笑道:“多承夸奖!”
“不过。”欧阳幽幽地接道:
“这捞什于却使人看了不舒服;也使人对你产生一种小家子气的感觉。”
说话同时,拍手指了指他的幛而纱巾。
青衫文士笑问道:“夫人是想看看我的本来面目?”
欧阳翠点点头道:“不错。”
青衫文士道:”并非在下小家子气,也不是是故装神秘,只因在下这件尊容,实在不堪入目;所以才不得不……”
欧阳翠截口笑道:“我不信!”
青衫文士若间笑一声道:“那我只好让你瞧瞧了,不过,瞧过之后,你必须三刻离去。”
“为什么?”欧阳翠注目接问道:“欧阳翠就那么使人讨厌?”
青衫文士轻笑一声,又摇摇头道:“非也!夫人雪肤花貌,足有颠倒所有臭男人的魅力,区区也是臭男人之一,怎会讨厌你呢?”
欧阳翠这才嫣然一笑道:“那你为何要赶我走?”
青衫文士樟面纱巾一扬;沉声说道:“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密室共处,当提防人言可畏。”
欧阳翠“格格”地媚笑道:“我都不在乎,我一个男人家,还怕人家说什么闲话?”
“不!”青杉文士坚决地接道:“你如果想要我揭下幛面纱巾,就必须接受我的条件。”
欧阳翠勉强点点头道:“好!我答应你……”
青衫文士抬手徐徐揭下幛面纱巾,含笑接道:“现在你该满足了吧!”
“不!”欧阳翠美目一触之下,连忙接道:“这不算!”
原来呈现在欧阳翠眼前的青衫文士;是一张腊黄的脸,两撇扫帚眉,几根山羊胡;为状致为猥锁,但一口牙齿却是整齐雪白,双目更是奕奕有神,与他那猥锁的面貌极不调和。
这情形,任谁也看得出来,那是戴着一份制做不怎么高明的人皮面具,所以。欧出翠才不由脱口说出:“这不算”的话来。
但,既使这一张戴着人皮面具的画;也是那么惊鸿一瞥地,又让那幛面纱巾遮住了,青衫文士并且轻轻一叹道:“夫人别横扯,还是走吧!”
欧阳翠道:“可是,我除了看到那丑恶的人皮面具之外,什么也没看到。”
青衫文士再度一叹道:“纵然是完全让你看清楚了,也是多此一举,夫人,你我立场互异,说不定明天还得拼个你死我活哩!又何必一定要看清我的本来面目!”
欧阳翠连忙接道:“不,在这岁尾年头,我们不谈那些伤感情的事,应该痛痛快快的……谁?”
突的喝出这个“谁”字来,那是她察觉到有人悄然逼近房门外。
她那声“谁”字一落,门外传入邢彬的语声道:“夫人请出来一下。”
欧阳翠一顿莲足,向青衫文士投过深深的一瞥之后,才打开房门,匆匆离去。
欧阳翠一走,青衫文士才如释重负的,长叹一声道:“孙夫子说的不错,‘唯女子和小子难养也’……”
重新斟好酒,干了一杯之后,又摇摇头道:“酒也凉了,这东西带的久了,可真不自在……”
说话间,抬手准备卸下脸上的伪装,但他想了想,又起身将门窗关好之后,才将幢面纱巾,和人皮面具一齐卸了下来,原来这位青衫文土;赫然竟是那有“书呆子”之称的胡天赐。
因为他天生一双异于常人的碧目,那就怪不得他于人民面具之外还得加上一层幛面纱巾,也怪不得他方才在欧阳翠面前揭开纱巾时,那么匆促的,连目光也不让对方看清楚……
他,伸了一个懒腰,重新入座,显的极为轻松的,自斟自饮起来。
“今这个年,过的真够惨,却也够新鲜……”
但他自语还没说完,却突然脸色一变的,当空一掌,将案头烛火击没,并匆匆将纱巾带好,一面却低声问道:“什么人?”
他住的这间房,是两面开窗,南面的窗子向着花园,北面的窗子,则向着隔壁的胡家,也就是胡天赐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