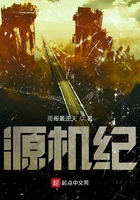顺妃抬头,透过玻璃支摘窗可以看到外头影影绰绰、飞扬飘洒的鹅毛雪花,风扑棱打在窗上,发出啪嗒之音。
她将手里的暖盅递交给身边的婵杏,说:“来时外头雪霁风停,一派祥和明净的天地,转瞬间又是柳絮因风起,真真儿是摸不准的。”
皇后斜倚在软榻上,道:“那你们便留下用个午膳再走罢。”全妃同顺妃对视一瞬,一道齐声谢了恩典。皇后问顺妃:“你不是说有事要禀么?”
顺妃软声应了一句是,先接过了婵杏递交过来的紫铜镀金捧炉,将手暖着,才徐徐说:“听了皇后娘娘吩咐,刻意着人留心太平宫、慈宁宫两处动静。恰好昨日江公公领着君悦出宫去,臣妾也就差了两个小太监出去盯梢着。江公公同君悦除了办自己的事,就是帮衬宫女采买些物什,或是置办旁的,都是寻常事。这些也不必拿来说嘴,只那两个小太监说偶然听到江公公同君悦说起些什么‘胎气’、‘养胎’、“娘娘”等事来,他们留了心回来报,臣妾亦不敢隐瞒,特来禀告。”
全妃本低着头,骤然听了这几个字来,猛地回神说:“莫不是德妃其实是有了身子了?”她心下微微发急,“若说是婧婕妤,她的胎一直安安生生的,有什么好拿来说的。何况,她还不够这个资历能让太平宫的首领太监,背地里也敬称一声‘娘娘’。”
皇后也是脸色一凛,沉沉道:“也不一定是德妃,她的身子不好,侍-寝的时候也不多。而且她在呈乾二年的时候还小产过,应该是怀不上的……”她嘴上这么说着,心里止不住地思索起来。
“可是怎么没来由就突然罚入万寿阁,而且是六月之久?就是要责罚,大可不必进慈宁宫的,未央宫是她独居,闭了宫也便宜,但偏生要关进慈宁宫去,可不就是大有用意?”全妃不依不饶,“何况六月之数未免过长,现在想想,十月怀胎之数,六个月犹嫌不够呢,这也能讲得明白了!”
“在此猜着,也是没个正经说法的,只是偶然得来的一点风声,保不齐就是婧婕妤,不过是江公公敬称了一句娘娘,顺口念叨了她的胎相罢了。”顺妃淡淡然说,“若实在要追究明白了,再过不几日就是除夕家宴,合宫里几乎没有不去的,太后娘娘理应一道儿出席。那慈宁宫可就有空缺可以钻了去,都说天下没有密不透风的地儿,加上除夕之夜人难免懒怠些,松懈了也是常理,届时差派个人偷偷去查探了,不也尽数明白了?”
皇后随手拿了一只柑橘来徐徐剥着,静听她二人的议论之后,也不立时发话,只送了一瓤入口吃尽了,才闲闲说:“都说这橘子酸甜与否,都得亲口尝了才知道,正如这德妃的事儿也得查验了才都明白。”
全妃嘴角蕴了一缕森冷:“要是德妃当真有孕,可就是大为棘手了。江公公知道,皇上必定也知道。连带着皇上也一起帮着相瞒,来日真叫德妃生下那孩子来,若是公主也罢了,若是皇子可怎么得了呢?”
顺妃恭敬起身,接过皇后随手赐来的柑橘,用了两瓣儿才说:“这也不一定,依我愚见,若是当真遇喜,这样大费周章地保胎,大概是因为德妃的身子过于孱弱的缘故。若是明面上晓谕六宫了,只怕经不起折腾,所以才要秘而不宣的。”
她缓缓擦拭着沾湿了汁水的兰指:“全妃妹妹可仔细想一想,皇上虽则宠爱二皇子些,却也没有越了规矩去。归根结底,是爱屋及乌,心疼德妃得紧了,所以这样。德妃从来是三好两歹的,若是这胎出了差池,难保不会损伤母体,坏了元气。所以保胎要紧,出不得差错。”
全妃冷嗤了一声,心里却泛起酸来。皇后亦陷入长久的沉默与嫉妒中去,顺妃的话一针见血,抽丝剥茧地露出刺人心的真相来,到底是皇上拿心去爱护德妃,所以不惜金屋藏娇。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阁外是万家灯火,明灯高悬,红亮的灯火将浓黑点墨的夜照得昼亮一般,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大明宫的笙箫歌曲,还有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热闹。
万寿阁内也小小地置办了一桌,韫姜最近开始害喜,有点不思饮食,所以多是清淡饮食,不过也不缺了寿字燕窝、红白鸭丝、什锦鸡丝等吉祥菜,韫姜还特地温了一壶屠苏酒给愈宁与双簪饮用。
愈宁同双簪先跪下说了吉利话、贺了新岁,复才起身来,韫姜笑意满面,拉着她们坐下,情谊深深说:“你们都是我贴心窝子的人,我当你们同姊妹一样的,姑姑更如我的长辈一般的,我们也别客套拘那些虚礼,一道坐了,用些年夜饭菜。”
簪堇拊掌而笑,敛了裙就坐下,看似调笑一地样说:“今年虽只咱们几个,可过得一样舒快。娘娘从前就懒怠应付那些繁文缛节的,家宴酒席上彼此举杯换盏的也是无趣,如今好了,不必那些个麻烦,吃得才痛快呢。”
韫姜盈盈看了她一眼,碧水漾波一样明净的眸子里倒影着暧-昧的烛火,鲜亮而明媚:“正是这个理儿的。也别顾什么了,爱吃什么且都吃罢。”她随手搛了一箸奶白鱼片入口吃了,味鲜美肉丝软,入口即化,十分可口适宜。
她没得思念起徽予来,喃喃道:“我身子很不大爽利,这里物什也不齐全,所以今年没有打了福包送给皇上。”
愈宁知她思念皇上,宽厚的手轻柔搭了上去,婉声道:“这里物什几乎都是皇上示意置办好的,娘娘可不能辜负了皇上的美意,得好好保养才好。”
韫姜将眼尾闪烁的泪意隐了去,讪笑道:“是了,也不知是不是孕中格外多思些,反而比从前矫情多了。”
簪桃不停地往韫姜跟前的浅碟里夹菜,劝她多用些补身子。
愈宁笑着拧她:“叫娘娘吃这样多,反而要倒胃口害喜了。这红烧明虾娘娘爱吃,奴婢替娘娘剥几个。”
四人围坐一团说笑着将饭吃了,韫姜只喝燕窝银耳蜜枣羹,愈宁同双簪用了小半壶屠苏酒,也是喜气洋洋的。
之后撤了饭菜,换上打发时间的玩-物来,韫姜率先提笔写了两幅“春条”作贺,簪桃心灵手巧,手指翻飞间就打出了一个福字缨络来,也算心意一桩。
簪堇剪了几张“福寿康宁”、“福禄祯祥”的窗纸,愈宁则披了斗篷出去捧了两束红梅进来,入了白釉高颈瓷给韫姜观赏。
馋嘴的簪堇还不忘朝炭火盆子里添了些栗子、红薯、香芋进去。逗乐得韫姜直直发笑,指着她嗔骂:“好一个促狭鬼,才用了半桌子菜,就来煨香芋、埋栗子,好好的梅香清冽,都被你这满屋子的尘俗气掩盖去了!不晓得的,还以为这万寿阁是慈宁宫的庖厨之地呢!”
“就是,好好的坏了愈宁姑姑辛苦摘来的红梅呢。”簪桃笑吟吟的,没有什么怒气,只是调笑着,愈宁道:“也罢了,把红梅折了丢炭火盆子里,叫这霜雪美人给那些个俗物染些谪仙气罢。”说着带笑把红梅取了一枝来,一朵朵攀折了丢入炭火盆子里。
韫姜只看着笑,腹部泛起的不适也略略纾解了好些。
她只随意朝窗外看了一眼,忽见猛然闪过一个黑影子,她不禁吓得尖叫失声,满堂的笑声也随之戛然而止。韫姜失声:“外头有人!”愈宁胆大兼之稳重,早在双簪心神不宁之前就率先抢出去拿人,韫姜定下神,由双簪搀着也出去瞧,簪桃不忘抓过一件银鼠毛大红猩猩毡给韫姜兜头兜脑地罩住,见外头已有个男子身形的人将一人按压-在地。
韫姜警觉地立在廊檐下,高声喝问:“是谁?”
愈宁拿了一只羊角宫灯提心吊胆地去看,见竟是御前的小城子,那小城子押着人过来,不便给韫姜行礼,只在口头上恭顺地问了贵安,才说:“皇上早料有小人要趁着慈宁宫守卫懈怠之际前来万寿阁作祟,特命奴才来守着,不枉奴才一身猫脚功夫在,拿住了这个鬼鬼祟祟在万寿阁窗前探头窜脑的狗奴才。”
他一把抓住那贼子的头发,强制他将脸子抬起来给韫姜过目,韫姜仔细去瞧,只见是个容长脸蛋、面生的奴才。小城子怕韫姜遇了风寒,于是请韫姜进去议事。
那奴才先是守口如瓶,问而不答,只当个锯了嘴的葫芦。韫姜呛了两口寒气,不住嗽了两声,小城子只怕审得久了误事,于是将那奴才的左臂反手一提,随手抄过一块擦了脏污的布块塞入他的嘴,只听咔嚓一声,生生断了他的左臂。
韫姜裹着貂皮风毛的毯子取暖,露出一丝不耐烦来,问道:“在万寿阁外鬼鬼祟祟所为何事?若再不答,另一只手也休想保住了。”
那奴才的嘴被脏布堵着,只呜呜呜乱叫,小城子将脏布撤了,喝了一声:“快说!”那奴才疼得涕泗横流,哭道:“奴才该死,是奉了贵妃娘娘的命,前来查看万寿阁的情况的。贵妃娘娘只教奴才一应都看着,回去详尽禀告了就是。奴才不曾想,才溜进来就叫人拿住了,奴才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瞧见的。德妃娘娘您大人-大量,饶了奴才罢!”
“呵!看来贵妃娘娘使得银子还不多,本宫这儿还没使人动手段呢,就把幕后主使都和盘托出了。可见是泼了人脏水了!”韫姜悻悻冷笑,不留情面。
她抿唇静思了片刻,大觉不对,只怕外头的人已有些了疑窦,故而来核实的。她一颗心突突窜着,见小城子仍不懈追问,抬手止住他道:“已经一目了然了的,不必非要宣之于口才都明白了。”她冷眼瞧着那奴才,道,“你是个好忠心的奴才,只是蠢钝了些。”她带上些许微笑,“小城子,真是辛苦你了,大冷天还守在外头,提了他去见皇上同太后娘娘罢。”小城子答应了一个是,麻溜地提了人就走了。
送走了小城子,韫姜沉声道:“恐怕颐华宫的那位起了疑心了,百密一疏,终究是走漏了风声了。”
愈宁搓暖了手,思忖道:“这是迟早的事,等月份大起来总有疏漏的时候,只是不想这样早。”
“这样也罢了,总比她们暗地里知道了动手脚,杀个猝不及防来得好些。”韫姜就着簪堇的手喝了两口安神汤,舒缓了紧绷的神经,“有皇上在,本宫不会怕的。何况她们未必就能躲得过我们的眼睛。”
酒席上趁着空档时分,容贤附耳过来对皇后说:“差派去的小河子没有按时回来,恐怕是叫人拿住了。”
皇后饮酒的动作缓慢地停了下来,面上仍是波澜不惊,挂着端庄的笑朝堂下看了一周,落在顺妃身上时,刻意停留了片刻,顺妃接收到她饱含深意的目光,举杯示意,看似敬酒实则给身边的全妃递了个意思。
“本宫料得不错,不论是慈宁宫出人,还是太平宫出人,总还有个盯梢的在。看来当真是有些猫腻在,并不简单了。”她随手搛了一片厚薄适宜的火腿送入口中,“若是安安生生养身思过,怎么会这么警惕?若真像传闻的那样,德妃是一丝两气,快要没命了,何必防得这样密不透风,毕竟早有传言,也不必这样费心再瞒。”
容贤松口气:“好在那奴才同咱们颐华宫毫无瓜葛,也不是咱们出面去差派的,出了岔子也理论不到咱们来。”
上座的徽予亦听了江鹤的转述,低声惑然:“那奴才说是贵妃?”他的视线不自觉飘忽向了恪贵妃,她一身烁烁光影的深银红吉服,袖口掐出雪白无瑕的雪兔风毛,一身优雅又不失华美的衣裳衬得她如鲜艳的玫瑰,一瓣瓣凝着鲜血一样的红,千秋无绝色,悦目是佳人。她神态自若,兀自搛菜饮酒,毫无异动。
伴随着轻微而短暂的沉吟,徽予说:“不是贵妃。”江鹤垂手恭谨而立,没有接话,只听徽予继续说:“后宫的事朕从来是懒怠管、懒怠听,并非是一无所知。韫姜被罚入万寿阁,贵妃近来又得宠,这二者毫无冲突不说,把话往坏里说了,对贵妃十分有利,她又何须刨根问底,要追究德妃是在万寿阁内是何情景?”他的话里带了几分浅淡的嘲讽与淡漠,像春日里偶然会刮起的一阵转瞬即逝的料峭寒风,刮得人一个激灵。
江鹤面无表情,只细如蚊声地应了一句是。他从徽予冷静而清隽的面容上看到了一星深刻入骨的厌弃。
他不敢妄自多言,只待徽予的动静与吩咐,徽予抬眸扫了他一眼:“为什么闹出这事端来,必是有人起了疑心了,是何处走漏的风声?”为避免风声走漏,徽予刻意不许和如命前去照看,只让出入慈宁宫的院判还有华惠允顺势过去伺候,一切都是隐秘为之,太医院旁人若想窥伺,是绝无可能的。
江鹤思来想去也寻不到一个缺漏,不解道:“太医院有院判大人封着口,旁人既拿不到药方子,也看不到记档;慈宁宫更是不必说了,因今儿是有意请君入瓮的,才刻意松懈了些,寻常自不必说。太平宫这头知道的,只有奴才同奴才几个贴心窝子的徒儿,奴才同他们的嘴,纵使是大罗神仙来撬也是撬不开的。”
“难保你同他们碎嘴时,没得叫人隔墙听了。”徽予似怒非怒冷笑了一声,江鹤被这一句哂笑惊得绷紧了脸,才想脱口解释,猛然想起出宫时,量着在外头就随性讲了几句,吓得是一颗心都要窜出来了,小声说:“奴才该死,前头日子出宫时,奴才同君悦随口谈论了两句,不知是不是叫有心人听了去了。”
徽予将商银雕花碧玉箸一放,声音还是一例的沉静,语气中已有迸发出火星一样蠢蠢欲动的怒火了:“真是了不得了,眼睛都盯到太平宫的人来了。”
江鹤敛声屏息、提心吊胆地站着,殿中纷纷的歌舞升平听来只觉嘲哳,他截断自己纷乱的思绪,双目虚空、不再赘言。
过了元旦的庆贺典仪和祭祀之后,徽予才抽得出空,过来慈宁宫给太后齐整地问了大安。彼时韫姜正倚在窗口往外茫然地看,万寿阁坐落在慈宁宫正殿承-欢殿西边,透过干净的水晶窗子可以将外头的前院收入眼底,若是放下卷起的湘妃竹帘,就能将屋子内一切情景隔绝于外。
小-腹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垂垂隆起,比同月份的见小些,而韫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瘦下去,曾经养得如一把浓墨瀑布一样的青丝,也不知在何时变得棕黄起来,晨起时会在枕头上发现散落的一把又一把的发丝。
梳头时愈宁总很沉默,一边陪侍的簪堇也悄悄儿地把散落的发丝,以迅雷之势一股脑儿收了去,韫姜装作不知,其实她都知道。
万寿阁不大,以落地罩与一架八折绣屏隔做三处,为正堂,内寝,以及小憩的偏堂,华惠允同院判有时同愈宁等人的私语,她可以略听到一二,所谓“绵惙气竭”等云云。
她在恍惚中失神,乍听宫门口有些动响,忙要放下竹帘遮住时,见竟是御前的人跟着慈宁宫的司侍进去先行通报。
她的心骤的一停,等候了半响,见乌泱泱一众人拥簇着一个英挺颀长的身影进来了,细细定了眼去瞧,是徽予。
他披了一身黧色底边滚三指宽掐金瑞兽纹暖裘,束着一个紫金镂雕麒麟缀碧玺冠,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人如玉。
韫姜一时扶窗哑然默声,想去唤一声,可怎样都发不出声音来。愈宁进来见了,扶住韫姜的肩,一手亟亟把勾着竹帘子的银钩子扯了,啪嗒一声竹帘子散下来,韫姜这才回神。
她呆呆地在旁边垒起的软枕堆里躺了,自嘲道:“是我失态了。”
她有满腔子憋闷的郁闷,凝结成冰一样的硌心窝子。
她将愈宁递来的烘暖了的小软垫伏贴在隆起的腹上,有气无力地说:“我原以为,我决意要生下这孩子时就断了念想了,就是一生下了孩子就撒手人寰也无所畏惧。可现如今,反而这样不舍起来。我不住地想皇上,可是你瞧瞧我的样子,补药进的是往日的数倍,人还是一样消瘦下去的。”她抬起暴起青筋的手,托住几乎凹陷下去的面颊,朝向悄悄儿揩泪的愈宁,笑着问,“是不是丑了?别瞒我,我心里都知道。在万寿阁里随意度日,所以铜镜前不多滞留,为着这肚子里的孩子,妆粉、燕支、檀膏等是不用的,可我知道我一定不比从前好看了。”她伏倒在香枕上,“我只怕我走的时候,是这样不堪的样子,他见了,不会记住我最好看的样子,不会记我一辈子。”
她拨弄着有些褪色了的蔻丹,失神道,“汉武帝的李夫人殁前以纱遮面,自死不肯以癯惙病容见他……”
愈宁半跪在脚搭上,给韫姜捏发了肿的小腿,按捺住满心的哀叹凄凉,强笑道:“娘娘快别想这些了,皇上疼爱娘娘,又不是为着娘娘姿容绝丽的缘故。就看那姝贵嫔江南水秀一样的相貌,也不比娘娘得宠多少。皇上待娘娘是诚心的。”她适中的力道舒缓了韫姜的愁绪,“娘娘吉人天相,一定会母子俱安。至于姿色之说,娘娘天生丽质,将来补一补也就都回来了。”
韫姜浅浅一笑,没有再说。
她没有察觉到徽予的到来,徽予在软榻的空档上坐下,只见韫姜茫然地抬起头看他。
韫姜枯黄的发以一支碧玉簪定住,因她不施粉黛,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她苍白中泛着青黄的清癯面容。
愈宁乖觉地敛裾退了下去,徽予拉住韫姜枯瘦的手,心疼道:“瘦了好些。”韫姜懵然回神,往后挪了挪:“你怎么过来了?”
“来给母后请安,坐着聊了会子。母后体恤,叫朕悄悄儿过来见见你,也好叫你安心养胎。”徽予见那珍珠钏儿与冰花芙蓉玉镯戴在她骨瘦如柴的腕子上空空荡荡、居无定处似的,心中不免发酸,“你怎么瘦得这样厉害?”
韫姜仍想着瞒下-身子不利的事儿,打着弯儿绕着,不愿提这事,只笑道:“予郎怕是嫌我丑了。”
徽予突然觉得,这是还在从前和她随意说笑的时候,不自觉笑了一下,一见她骨瘦枯槁,又不笑了。他欲言又止,想劝韫姜又不知如何开口。
韫姜察觉出他纠结沉痛的情愫,反握住他的手,柔声问他可有难处,徽予讪笑了一下:“没有……朕是瞧你怀相差,怀得实在是辛苦,太医们说是你底子太虚的缘故,本不是遇喜的好档口,这孩子来得不巧……”
听徽予萦回言语,韫姜一下子直起身子,声音庶几微不能闻:“你是不是……”两人四目相对,近十数年的情分默契,让二人一霎时就彼此明了,韫姜黯然下来:“和大人到底还是说了……”
徽予见捅破了这层纸,忙拉住韫姜的双手,紧紧包在手掌心里:“姜儿,孩子往后总会有的。等你养好了身子再……太医说你气血衰竭,必得猛药下去你的身子才撑得住,可不知这烈性再勾出什么旁的病症来。”
韫姜苦笑了一下:“只怕反反复复再不能好了,以后也没有个真正能适宜养孩子的时候了。现下只好信和大人他们,万一都好呢?”
她说得委婉,但心里已经下了狠心,徽予知道若贸然动了手,只怕不仅伤了身子,更是将她的心也寒透了,于是说:“只当为着我吧,可得仔细养着。补品药石这些东西你别怕,哪怕是要凤毛麟角,琼浆玉液,朕统统给你寻来。你只消受用,把身子补好了,元气养足了。”
一扑入他的怀里,韫姜就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安心与安稳,她鼻尖一酸,应了一声好,说:“我是真想一直陪着你……”
徽予轻柔拍着她的肩,哄着她:“你别怕,那奴才的事朕都一应处置好了,该敲打的都敲打了。你在慈宁宫这儿住着,比未央宫里虽无趣些,不齐备些,可是最安全稳妥的了。”
“苦了太后娘娘保我,若非我任性妄为,也不必如此。”韫姜摩-挲着徽予食指上的一只金镶玉的约指,徽予反抓住她的手,拨弄了一下她的蔻丹,柔声道:“你别多想这个,太后是真心疼你的,不觉得烦扰的,你也别自寻忧愁。”他朗声笑了一下,“这也不单单为着你,一边也是为皇嗣计,应当的。”
“外头清欢妹妹的胎怎样呢?”韫姜抬头看徽予,他一例很注重仪容,下巴光洁得没有胡茬,看着丰神俊朗,恍如蒹葭倚玉树。
说话间愈宁上来奉了一盏蜜枣茶,徽予饮了两口,蜜甜不腻,润口生津,才徐徐说:“她的胎很稳,朕三不五时地去瞧瞧她,明年五月份约可临盆,与你相近。”
韫姜轻笑了一下,心里松快了好些。
外头临近黄昏之刻,夕阳却如晨辉一样生气蓬勃,织了一天彩锦丝绸一样的晚霞在天,浓郁的红没入远端的蓝白处去,融成一幅溢满希冀的画卷。
韫姜不能出阁,倚立在门口送徽予出去,她看他渐渐消失在宫门口,而后静默抬头看了看一天的旖旎多娇,簪桃过来给韫姜披了一身银红八棱西府海棠苏绣纹暖裘,扶着她的肩伴在身边。
说是罚禁在万寿阁内,实则无人守在万寿阁外看管,偌大慈宁宫是由着韫姜走动的,只韫姜恐招惹麻烦,从未出过门子。
“娘娘想是有心事。”簪桃见韫姜长久不言语,小心开口说了一句。
韫姜回神,面上渐渐泛起了神气与潮-红,道:“我是见这霞光真好,许久没见这样美的晚霞了。看了晴天散馀霞,以后还想再看一看雨后烟景绿。”她将头伏在扶着雕花门框的手上,“我想看着阳儿长大,看他娶妻生子,也真心想着常伴君侧,孝敬太后。”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憧憬,“我总是作了最坏的打算,然后惶惶终日,日日想着些不好的计较,真是舍本逐末了。”她转头来朝着簪桃灿然一笑,道:“进去罢,外头冷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