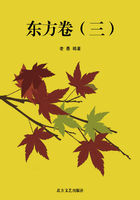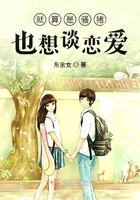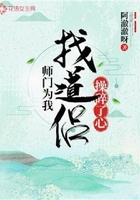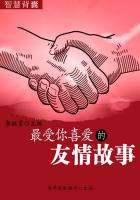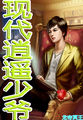北京人说春天是“春脖子”,当然是说春日的短暂。但去年北京的春天似乎迟迟莅临,又转瞬即逝,简直是连“脖子”也没见到,就进入了烈日炎炎的夏天。头一天,身上还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袄,第二天穿上短袖却还是挥汗如雨。只是眼前的植物郁郁葱葱,仿佛春天里它们没有享受到尽兴的表演,攒足了劲儿就在夏天里疯狂地长。若不是知道节候是夏天,觉得嗅到的该是浓浓的春的气息了。
记得去年春天里去了一趟白洋淀。因了小说家孙犁写过的荷花,白洋淀在我印象里总有茂密的芦苇在风中摇曳着,荷叶田田,花团锦簇,人在荷花丛中穿梭,荷花的清香里就有一阵阵歌声响起。然而到白洋淀一看,面前的芦苇只浅浅一层绿芽,荷花却不见踪迹,几枝倒竖的荷花秆因为天冷,孤零零的,连鸟儿也不愿光顾。主人好客,让我们坐了游艇。坐在飞驰的游艇上,水冷风寒,刺骨得很,感觉时光倒流到了寒冬腊月……游兴倍增是到了孙犁纪念馆。孙犁老人很孤独地坐在那里,眼前的荷花一瓣也没有,也是一脸失望,仿佛对我们说:你们来得不是时候。又仿佛说:这也好,清静,我就喜欢这清静呢!……同样让我失望的还有去年在胶州。桃花盛开是胶州人春天的一件盛事,当地人也郑重其事。不然,《青海湖》的朋友们就不会邀请我专门去看桃花节了。然而,到了胶州,成片的桃园却是树影稀疏,株株屹立的桃树上的花儿缩头缩脑的,正在打着苞蕾。主人仿佛不好意思,带我们转了转有桃树的山头。桃树逶迤了一山头,一眼望不到边,想着如果此时桃花盛开,灿若云霞,这一山的桃花肯定就是蝴蝶、蜜蜂的世界了,可惜这只是想象中的曼妙。
没看到荷花与桃花,但春天确实来到了我们中间。春夏秋冬是四季的转换,喜怒哀乐是人心情的转换,物事时序自有其规律,春天的到来总给人明显的昭示——我还清楚地记得二〇〇四年春天到来的情形,我这样说是因为那天立春我是在麻将桌上度过的。那是新年的正月十四,再过一天就是元宵节了。古人说“六合同春”,立春时,我真的感觉东南西北、左右上下,全是春的消息,春天无疑不可抑制地进入了身心。但我却抓了一张臭牌,可见春天也不是总给人带来喜悦——再说,现成的例子就是二〇〇三年的春天,美伊战争将春天弄得乌烟瘴气,肆虐的“非典”仿佛给世界陡然减少了一个春天——去年由于迟春而错过两场花事,如此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
去年的秋天还看了白皮松。那是在山西潞安侯堡镇的时候,那天中午喝了点酒,有些醉意。吃过饭,小说家葛水平不由分说地就将我拖上了车。车子在山西大地上奔驰,不一会儿就到了长子县一个名叫“白松坡”的地方。远远望去,白松坡上一株株松树在秋末的阳光里泛着白光,阳光如水,白皮松漾在那水里炫目得刺眼……松树常被人比作龙,那些松树就像一群白龙在山上盘踞着,有一种神圣高洁的感觉。我细细打量或轻轻抚摸着,面前一片梦幻。地上的青草已经枯萎,间或一两株黑黑的松树,却是枯死的白皮松。生者晶莹,死者漆黑,白皮松仿佛只生存在黑白两极,黑白分明,斑驳的树皮就剥落成一丝丝“道”意。山上有一座庙,但我没进去,只是在废墟上捡了几块瓦当……但回来好久,脑海里还是那一片白皮松,晶亮晶亮的,十分懊悔没有进庙。
或因花事蹉跎,或因醉酒,这几次旅行显然都留有遗憾。
但没有想到,这种遗憾在去年的冬天又如期而至。《北京日报》副刊部组织几位作家去山东文登看海,然而在近观大海那天,海上一片浓雾,太阳红黄黄的,在雾里就像一只陈旧的指印。海滩沙粒细细的,十分干净,海浪一浪高过一浪地铺天盖地而来,其声如雷,波涛汹涌,似乎在涨潮。远处一片茫茫白雾,摸到大海的边却看不清大海的全貌,朋友们三三两两地走在海边,都有些失望。脚踩金黄、细软的沙,心与海贴得很近,近得几近虚无。主人后来把我们带到了昆嵛山下。这昆嵛山是王重阳的道山,有老子、七子的踪迹,我们却是擦肩而过,于是主人嘴里啧啧着,连说“遗憾,遗憾”。
未能问“道”如山——我常把这种旅行称作“未完成的旅行”。我这样说,人们肯定觉得我对此充满懊恼和后悔,其实不是。游历天下的徐霞客在云南丽江蹲了十七天,玉龙山近在咫尺,他也只是遥遥致意。读李密庵的《半半歌》:“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悠闲……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我想,这“半”在这里就是“未完成”之意,里面蕴含了一种无以言说的大美——要说,我们住在文登海边,浓雾之后就是晴天,是有机会看海的,同游者中就有兴致勃勃去看海上日出或日落的,我却静静地站在窗前,没挪动脚步——这并不是懒惰,而是因为我感觉这样有想象的空间,有一种缺憾的美丽,我很是喜欢。
2010年11月25日夜,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