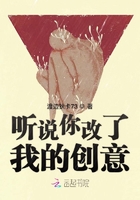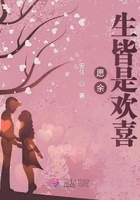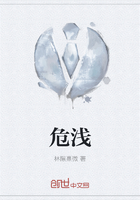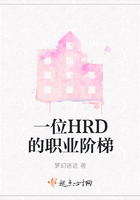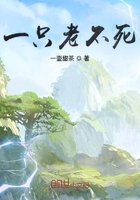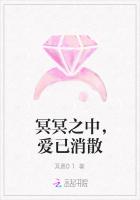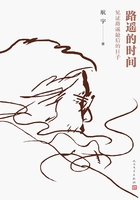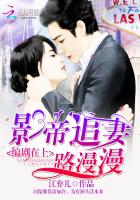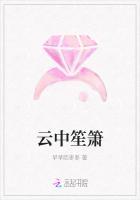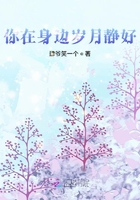1
从亦心家里出来已是十一点半,路过烧烤摊,我觉得自己又饿了,无奈身上只有一块钱,便心安理得地进小卖部要了两根红塔山。回到家已近十二点,我坐在床沿上抽掉了一只烟,脑袋开始有些晕乎,本想倒头就睡去,但还是强忍着看了一会儿书。这是规矩,也是习惯。不看书我不能安然入睡。
说实话,我看的书倒是挺多的,毫不夸张地说,就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一年的课外阅读量能及我十分之一的人寥寥无几,当然,极个别资深的网文爱好者除外,这种人的存在在我看来是一种社会疾病,他们一面自称知识分子、文艺青年,一面却又吹捧着三观扭曲的腐朽文化,大肆向无辜群众传播这种时代的毒瘤竟然好意思宣称自己是读书人。就算是数量上超过了我,深度上也远远不及我。老师也不例外。不是我盲目自信,实在是我深有体会。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读的书太少,所以拼命地读书,短短初中三年,我读遍了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名著,结果上了高中才发现,读了那么多书除了在写作文时用上点以外,竟然几乎没什么用处。看同学们一个个陶醉于手机短视频沉迷于网络游戏,我感觉自己仿佛被孤立了。我每天靠着几本书聊以**,偶尔一个人听听音乐发发呆,笔和纸便是我最忠实的伴侣。可是我费尽心思写出一篇作文,而别人随随便便从网络上抄一篇作文,在老马看来我的心血就显得不那么出众了。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都丝毫不影响有些人的学习,考试成绩出来,照样有人比我高。曾经有一个成绩比我好的女生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就没看过除了课本以外的任何一本书,她甚至还劝我少看点书。似乎看书成了影响考试成绩的罪魁祸首,所以各科老师都严厉禁止课外书,就连语文老师老马也表示,只准看作文书。在这种严峻的形式下我不得不戒掉在课外读课外书的坏习惯,又不得不挤出睡觉前的半小时看一会儿书。只想说:我太难了!
高一那年暑假我偶然在书店看到一本叫《挪威的森林》的书,由于我喜欢的一首歌也叫《挪威的森林》,我便买回家读。自那以后村上春树便成了我最钟爱的作家之一。最近我读的是他的一本叫《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书,读了不及三分之一,我便被彻底折服:看来要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实在不容易。好在我并不打算成为一名小说家,在我看来写小说是最没有出息的职业,小说家们就像是马戏团的小丑一样费尽心思胡乱地编造各种故事拼了命地讨好读者,迎合各类人的阅读偏好,考虑各种人的阅读兴趣,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想表达的,还不如散文家呢。不过村上春树是个例外。要我说,最好的职业还是诗人。我喜欢读各类诗,同时也佩服每一位好的诗人,我觉得他们简直是这个世界上历史上最厉害的一群人,不受任何人约束,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尽管严格来说诗人并不足以称之为一个职业,而且大多数诗人物质生活上极度匮乏,根本不足以养活自己,但是从精神层面来看他们却比任何人都富有,纵使异于常人的奇怪行径让他们看起来像极了疯子和精神病,他们仍然不惮世人的批驳甚至迫害,以孤高的姿态傲首阔步,冷眼睥睨世界,单这一点就足以深深吸引我了。所以我励志做一名诗人。
我在十五岁那年夏天写出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首诗:
阴暗了天空的满天乌云啊:
你们——走吧!
那树在寒风中挥舞着
山朦胧着,悲沉着
等你走。
等你走后
是满山的嫩绿
漫山的野红
从此我便一发不可收拾,疯狂迷恋写诗。我觉得较之写文章来说写诗要有趣且快乐得多,当你沉浸于写诗的过程中时,你浑身上下几乎每一个细胞都仿佛要冒出一句诗来,你随心所欲地加以修改,慢条斯理地进行斟酌,使其自然而然,恰到好处。而你简直乐在其中了。自不待说,诗是最接近艺术的文学形式,或者说,诗就是一种艺术。每个读诗的人几乎都有这么一个特定的过程:由格律诗,到长短句,再到近体诗,最后则是现当代诗。我也不例外。一开始我读唐诗,喜欢那种规规整整的句式和朗朗上口的音律格调;后来我又喜欢读宋词,喜欢那种或凄美或雄浑的洒脱意境;直到我读了徐志摩郑愁予郭沫若的诗,读了顾城北岛汪国真的诗,我又一步步地踏入了现代诗的田园,为了一份不可名状的殊荣而乐此不疲地阅览着一首又一首诗,结识了一个又一个诗人。很难说,我真正读懂了它们,但毋庸置疑的是我确确实实因此而感到快乐。我最终明白,我所追求的无非自由,真正带给我快乐的与其说是诗本身毋宁说是藏在诗中的自由因子。诗,这个奇妙的东西,它救赎了我,让我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不至于迷失沉沦。我终于是坚强地活着,活到了现在,这无不仰仗于诗。我曾衷心地说过,诗是我在此世界最大的恩主,我甘愿做诗的奴隶。这句话不带有半分的虚伪和夸张。诗确确实实奴役了我的精神生活的几乎全部。
我读了不少诗,自然也写过不少。但较之写诗,我是更爱读诗的,因为写诗实在是件劳神废心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可取的技巧,而全凭灵感(当然对有些写诗的“专家”们除外,他们能凭借诗中存在的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而轻轻松松就造出批量的诗来,这实在颇令人费解。但想想现今机器人都能写诗,那专家们的批量生产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灵感这玩意儿稍纵即逝,不是人所能够控制的,因此写诗也就不能随时随地随心随性了,这是我最忌惮的了。不过我也很明了,违背灵感而强行写诗是写不出来好诗的,为了一句甚至一字而费尽心思地推敲,这样的诗是不具有灵魂的。所以对于写诗我也便不加以要求,提笔有灵感便写,不然则做罢。因此,数年来我写的诗尚不足一个笔记本,不过大体上都还算满意。我每次写诗都是随手写下,或在试卷上或在书本上或在一张废纸上,后来我把它们裁剪成一般大小,装订成册放在床头的一个纸盒子里,这是我的一个秘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从来也没有人发现过,任何人都不知道。亦心也不知道。
2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写诗全是因为那个女孩,那个大我两岁的女孩。
我曾经为她写过很多诗,写过一整个春夏秋冬的诗,春花,夏雨,秋月,冬雪,我写满了一个米白色的厚厚的笔记本,那几乎是我最有灵感时期写过最多且最好的诗,我打算送给她——在她临走之前。可一直到高考完她离开的时候,我还是没有送出去。后来我把那个笔记本当作笑话丢到赤水河当中。
3
早上六点起床去学校;和亦心吵吵闹闹;放学和杜衡、陆离吃饭;晚上到学校背后抽烟;有事没事就跑去亦心家;周末打篮球或爬山;夜里一个人喝酒或看书。这便是我机械一般的生活,谈不上有趣,也谈不上无趣,反正我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么度过的,也早已习惯,自然不会去想什么改变什么革新,偶有逃离的想法,也只是想想,未曾实践。或许已有人发掘,我是不是漏写了什么?不错,我漏掉了最为重要的家庭。试问一个人的生活怎么能离开家庭呢?的确是,每个人都有父母妻儿都有兄弟姐妹都有家庭,我也不例外,但倘若把家庭视为个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我除外。不过我还是打算多多少少讲一些与家庭有关系的事情。我有父有母,有一个生病的姐姐和一个古怪妹妹,也有长年住在乡下的爷爷奶奶,至于姑表亲姨表亲什么的,则和正常人一样,照例都有。我每天中午都要花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穿过大桥到河的左岸去父母那里吃午饭,和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姐妹围在一张不大不小的矩形木桌前,一边嚼着饭菜一边听他们讲一些琐碎的事情。除了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以外(当然,这种情况很少),我一般不说话只低头吃饭。我会花很短的时间吃完饭,而后做一做擦嘴或者挪凳子的动作表示自己已经吃完,母亲总要关切地问一句是否已经吃饱,父亲则会停下他手中的筷子,以右手摸出放在西服内侧口袋里的一叠钱,再数几张零钱递与我,多少不等,不过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十二块。这十二块钱便是我当天下午和隔天早上的伙食费。我一边站起来一边伸手接过钱,整个过程利利索索,十分自然。之后我便离开了父母家,再花半个小时到河的右岸去。一般情况我在父母那里停留的时间就十分钟左右,最多也不超四分之一小时。并且如果不是学校的要求我几乎从不曾主动开口向父母要过钱,给或不给全由他们,当然他们从来都不曾少给过我,偶有一两次父亲吃得专心忘记了给钱这一重要环节,而母亲恰好也忘记提醒,我便仍要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最后空手离去,饿一下午的肚子。任何人都知道,我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正常人。
尽管如老师们所言高中生活所剩无几,决定我们人生的高考也一步步逼近,但我不认为这于我而言是一种压力和动力,我觉得这对我反倒是一种无形的桎梏,让我身心不安。因此我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当然也不认为自己的人生会被改变。我曾对自己的这一想法坚信不疑,甚至将其视作某种真理写在笔记本里,直到后来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意,在偶然的某一天我翻到了当初在笔记本上写下的类似于这样的一番番话时,我才明白当时自己的想法有多么幼稚,错的有多么离谱。
4
我就这样一天天消磨着时光(其实称不上消磨,但也差不多),一个夏天就悄然从我身旁溜走。到底是我没有抓住,还是我不经意放松了手?反正又是秋天了。我铺垫了整整一个夏天,而故事终于要开始了。
她离开已有三月:六月、七月、八月,也就是一个夏天。怎样形容这样一个夏天呢?我不能用快或慢这样机械般的字眼,我仅用一个词:
空白。
如何空白?我不知道。或着,我说不清楚。反正映像里那个已经逝去的夏天不同于往年的夏天,它阴冷、灰暗,且不停地下着雨。反到是秋天,天气郎润,微风清扬。
5
陆离和杜衡不间断地对我冷嘲热讽。
杜衡早已走出了他的失恋的阴影,陆离则一帆风顺,甚至到了买避孕套的地步。
那天下午放学,我们在学校东侧一家名叫味蕾的砂锅店吃饭,吃完饭出来又绕至学校背后抽烟。我们一边抽烟一边聊着和女生有关的话题,陆离就讲他和萱儿之间的事情,比如怎样在街上牵手啦,怎样在公园接吻啦,怎样在超市搂搂抱抱啦,最后他声称再一次一定把萱儿睡了。
按照惯例我们抽完烟就向东回学校,可是那次陆离却拉我们朝西走。朝西是去往医院的方向,陆离这是要干什么?我心里已经猜出七八分。果然,他拉着我和杜衡进了医院旁边的大药房。就这样我们三个身穿校服强装淡定地买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盒三只装杜蕾斯,粉色玫瑰味,我们三人一人一只。
至于后来陆离是否真的把那个杜蕾斯用在了萱儿身上,还是别有用处,我就不得而知了,他没再提起,我也没再问过。至于我的那个嘛,我则留了下来。
6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我终于决定联系那个女孩。
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为此,我已经写出了很多剧本,拟定了很多计划,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一个好的时日把电话打出去。
周一到周五不行。她还在上学,不能打扰她。
早上不行,她可能还在睡觉,不能打扰她。
晚上不行,她可能已经睡着,不能打扰她。
最终我决定在星期六中午吃完饭十三时左右打电话给她。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时间的到来,以及把欠的电话费交上。
我的手机停机已有两月,两月以来我不曾使用手机。由于我不存在非联系不可的朋友,也不存在非使用网络不可的情况,所以自停机那日起也就一直没有开通的打算。
我的这只SCH—1759手机名义上虽是智能手机不假,但实际上只能当普通手机使用。它最早版本是在2012年,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伦敦奥运会上罗温·艾金森先生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偷偷拿它拍过照,所以在当时它确实是挺先进的一款手机,但在七八年后科技爆棚的现在还能有多少人使用它?我想除了我之外再无二人了。我的手机没有QQ微信,也没有网络游戏(有也不能用),只有电话和短信,另加一个音乐播放器。
我的通讯录里一共五个联系人,和我联系最频繁的是中国移动。
时隔二月,我再次打通了她的电话,她依然那么热情洋溢,耐心地答复着我的询问。我的欠费金额为五十二元二角三分,她说。
于是从星期二早上我开始攒钱。不吃早餐,不吃晚餐,一天下来可以攒十二块钱,到星期六下午就可以攒够钱交话费了。这样我先向陆离和杜衡说明,我暂时不和他们一起吃晚饭了,他们表示理解,于是到星期二晚上我攒下了第一个十二元。我一边啃着中午从父母那里拿来的大饼一边看书。我欣慰地笑了,笑着入了梦乡。
星期三下早自习,早餐时间,我准备倒在课桌上睡觉,亦心递给我一块面包,她知道我没吃早餐,但她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没钱。我说,父母昨天忘了给钱。我让父母背了黑锅。
中午的时候父亲掏给了我二十元,因为没有零钱。他叫我吃一顿好的。我很高兴。
下午放学,十分钟过后,人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我,还有亦心。
亦心问我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去吃饭,我说我不饿。
亦心叫我和她一起去食堂吃饭,我说我要去打篮球。
亦心问我要不要她捎点什么给我,我说不用。
亦心去食堂吃饭了,我去打篮球了。
球场上人很多,我的确很饿。
我接连地输球,尽受嘲弄,实为狼狈。
我在厕所里吸了一支烟,摸摸裤兜发现我的二十块钱不见了。我慌了,在篮球场找了好几圈,又在厕所里找了一遍。没有。
当我饥肠辘辘地返回教室时,亦心提着一份盒饭站在教室门前。她微笑着招手,叫我过去吃。
我愤怒极了:不是都说了不要吗!
怎么一点道理都不懂?我要攒钱!
我郁闷地回到座位。
亦心把盒饭给了曹决明——我的宿敌。曹决明这个家伙之所以是我的宿敌不是因为他做什么事情得罪了我,也不是因为他经常考第一名我嫉妒他,而是因为他视我为他的宿敌。他之所以视我为他的宿敌不是因为我做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也不是因为他害怕我抢他的第一名,而是他天性如此——他敌视所有人,瞧不起任何人。总之曹决明这家伙争强好胜且目中无人。如果说他真的有实力目中无人的话,那我非但不会讨厌他反而会崇拜他,但事实上呢?他就是一个碌碌之徒等闲之辈。他与别人说话总是锋芒毕露自以为是,并且开口闭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甚至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话题也能被他扯到这上面来——他有这个能力——于是我们私下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马克思”。如果他要是真的对马克思主义深有研究的话,那他在夸夸其谈时我也愿意洗耳恭听,可是有一次我们谈论共产主义社会,我提到信誉势必成为核心竞争力(这句话是《资本论》里的,我在一本杂志上恰好翻到过,就了记下来),而他就此表示质疑,还拿《资本论》批驳我,说我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我没有拆穿他,不过打那时起我就知道了他是一个十足的卫道士。
不光我、陆离和杜衡讨厌他,班上很多人都讨厌他。
亦心这样做显然是故意的。
上晚自习前十五分钟,夕阳西下时。
亦心走过来说,你惹我生气了。
我说,走开,走远点。
亦心走开了,走得很远。她出了教室门。
陆离说他看见亦心在操场上哭,叫我下去看看。杜衡也这样说。
我说,随便她,与我无关。
就这样,我和亦心再次闹矛盾。
但是我不觉得自己有错。
星期四下午,我没去打篮球,亦心没去吃饭。我趴在窗户边不知道谁的座位上睡觉,窗户半开着,窗帘半掩着,风轻轻吹着,不一会儿,我睡着了。委实睡着了,睡得很舒服。
亦心突然坐了过来,一下子惊醒了我。
我揉揉眼睛,她正笑对着我。
她笑着说,你想吃啥?
我不予理睬,转过头继续睡觉,不过这次我没有很快睡着。我听见她重重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她出了教室。据某个知情人士说她又在操场上哭鼻子。
星期六,我终于凑足了五十五块钱。
中午吃完饭,我在一家手机店里交上了五十五块钱的花费。之后我立即跑了回我的住处。
花费余额二元七角七分。
思量许久,我决定不打电话,我决定发短信。这是我的方案之一。
我于星期六十三时零一分发出一条四百五十二字的长途短信。
大约十分钟后,我收到了一封来信。
提示音是Pure bell,震动是Waltz,仍然是熟悉的那个声音。我心头猛地一震:她回信息了。
她会说些什么呢?
她会说多少呢?
默念十秒,然后打开。
中国移动:您的手机已欠费……
我垂头丧气地将手机重重地摔在了床上。我已经被气炸。
下午放学。我没有去打篮球,也没有去爬山。我向陆离要了五块钱,花掉半小时去左岸又充了五块钱的话费,再花掉半小时回到右岸,已是七点半。
只要把手机关机再开机,我就会收到她的来信。我想。
我端坐在书桌前,把手机摆放在书桌上。此时太阳正悬在我的玻璃窗上,阳光从纱制窗帘渗透进来,落在我的左手上。
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我足足等了有一分钟,手机才开机,显示出SIM卡的正常状态。我又等了足足十秒,Pure bell提示音和Waltz震动音再次响起。这次我索性直接打开。
果然还是中国移动。
这么说,我白白忙活一场。
她没看见吗?还是她看见了不想回复?也许,她根本就不在乎,对她来说那就是一条垃圾短信。根本不予理睬。我苦苦地笑了。这次我没有摔手机。天已渐黑,我上了四楼的天台,坐在水泥地板上,靠着一面同样是水泥的墙壁,仰头望明月,没有明月,只有星星。星星闪烁着,在我的眼眸正中央,渐渐变得模糊,成了团状,像被裹上了一层雾。
我哭了?不知道,反正不停地掉眼泪,掉了半个小时。
我蹲在厕所里抽烟,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是亦心。她怎么来了?
我提了裤子回到房间,灯依旧亮着,和半小时前一样,手机放在书桌上,屏也还亮着。
亦心坐在两张藤椅之中靠窗户的一张上,翻看我的书,那本淡蓝色封面的《月亮和六便士》。另一张摆在床头的藤椅上摞着我的几件衣服。夏亚卡坐在我的衣服上。
夏亚卡是亦心的朋友,她是一个文静端庄的女生,高高瘦瘦,张着一对虎牙,笑起来十分迷人。她之前和亦心合租在一个公寓,后来亦心搬走了,她就一个人住着。我们见过很多次面,很聊得来,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六月帮亦心搬家的时候,那次我们就一本书聊了很久,我发现她实在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孩子。这次她突然来我家,我颇感意外。
“是她硬把我拉着来的,说她一个人不敢来。”夏亚卡用她那细腻的嗓音说,“你们两啊,怎么回事儿?”夏亚卡起身走到亦心旁边,亦心把书合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想,她刚才根本就没有在看书。
“讲了个啥?”
“啊?”
“我说书,你刚才看了不是,讲了个啥?”
“我不知道。”
“来干什么?”
她瞪着我,足足有五秒。
“那我走了。”她起身就走。
“你这是干什么!”夏亚卡又推她坐下,“还是我走吧,反正我来也没什么用处的。”
夏亚卡走出了门,转身又对我使了个眼色:“好好说!”
我坐在床头的椅子上,正对着亦心。
“本来想着去找你的,有事儿耽误了——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手机刚刚开通。”
“怎么想着开通手机了?不是说讨厌现代科技吗?”
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看得出来?我刚刚哭过。”
“为什么?”
我拿起手机,翻出发出去的那条短信给她看。
“所以你开通手机就是为了联系她?”
“嗯,我攒了一周的钱,不吃不喝就为了交个话费。”
“所以你因为这个就生我的气?”
“我没有生你的气,只是情绪这东西吧,有时候由不得人。”
“是啊,就像我,跑到操场上透气,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哭了——你还不知道吧?”
“对不起。”我说,“听说了。”
“准是陆离那家伙告诉你的,也真讨厌,哭了还叫人给看见了,真丢人。”
“为什么要哭呢?”
“你说,我做错什么了吗?怕你饿着好心好意给你买了饭,反而受了一顿骂。舔着脸又来主动问你,反而不招待见,倒成我的不对了。好吧,如果是我的不对,现在我来给你道歉了,你说,我哪里不对,要是我做错了,我改!”亦心越说越激动,差点没哭出来。
“你没有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理我了?”
“心里挺烦的,所以就想着先把事情解决了再说。也是故意气一下你。”
“所以你是故意的,你知道我会伤心?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对我满不在乎,其实你知道是吧?你知道我一个人躲在操场上哭,你知道我因为这个伤心了好几天,你明明知道,却跟没事人一样对我漠不关心,你怎么这么坏!”亦心仍然很激动,声音在颤抖,仿佛被某种无形的东西灼烧着。
“用不着别人说我也知道,我也感受得到,我还不了解你?不要说你哭了,就是你皱一下眉头,我也明白什么意思。”
“我倒情愿你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心情还好受些。你说你这样气我,何必呢?”
“就是想气你。”
“你太坏了!”
“你不是也故意气我了吗?”
“哪有?”
“你把盒饭给谁不好,偏给‘马克思’那家伙?”
“谁让你先惹我来着……我没错。”
“好,我的错好了吧……”
我送走了亦心,已经八点多。
我安安静静躺在刚才亦心坐过的那张椅子上,望着外面的浓浓的黑夜,点上一支烟,祭奠我苍老的悲哀的心灵。
我知道,有些事情终究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