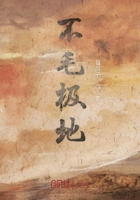又一炷香时间过去了,万历帝还没出现,这让早早在门前候着的礼部、国子监的大臣们有些熬不住了,有的身体素质差的,不断在流汗,甚至有人晕倒了,晕倒的那人直接被其他人拖到一边阴凉处躺着,好生休息。
钱缤英嘀咕道:“这万历帝果然是老宅男,做事就是磨叽,难得出来一下还这么慢。”
声音很小,但被张峰听到了,张峰悄声说:“知道就行了,别说出来,人多耳杂,免得生事。”
钱缤英没有继续说,只是在发呆。不知过了多久,西安门突然大开,前面开路的是整齐的御林军,后面跟着是一台大轿子,轿子旁陪着几个太监,看着轿子华丽的外表,想必也是皇上的御轿。看到仪仗队出来了,两旁恭候多时的大臣门纷纷凑上前去,跪拜,钱缤英来到这还一次也没跪过,也就没有这个习惯,但众人皆跪,只有他一人站着,显得很尴尬,在短暂的思想斗争之后,钱缤英还是选择跪下。
众人皆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历帝不愧是我行我素的典范,看到这么多人跪下,只是挑开帘子看了看,然后很快又合上,和贵妃洽谈起来。众人没有听到皇上说起来,谁也不敢先站起来,仅仅低下头,左看右看,不知如何是好。突然,轿子的帘子被挑开了,万历帝笑着说:“刚刚是朕疏忽了,忘了众爱卿还跪着,都平身吧。”
众人站起来,和声道:“谢皇上。”
众人站直了以后,都跟在队伍末尾走着,钱缤英和北镇抚司的两人则是走到轿子旁边作为侍卫,张峰一开始没有注意钱缤英动向,就以为和大臣站一样的位置。钱缤英发觉了,小跑到他身边,焦急地说:“张大人,我们是皇上的侍卫,不是大臣的侍卫,你站后面干什么?”
张峰有些慌张,说道:“我我我,不知道啊,第一次经历,那我们应该站哪?”
钱缤英说:“我们锦衣卫站在轿子的四角,一人站一角,你马上看北镇抚司两个人站哪,剩下来两个就是我们的。”
钱缤英说完转身就走,张峰点点头,赶忙跟着他前去。这一幕被不少大臣看到,其中有人就说:“这锦衣卫没见过大场面吧,位置都能错。”说着旁边几个大臣也纷纷笑起来,方从哲在大臣队伍的最前面,听到他们笑声,就回头白了他们一眼,那些笑的大臣看到方从哲,赶快停止笑声,恢复严肃。
队伍正走着,从后面走上来一个人,跟在轿子旁边,说道:“皇上,臣有事禀告。”
万历帝探出头看了看,问:“没见过你啊,你是何人?”
那人说:“回皇上,臣是今年刚调任国子监监丞,杨志和。”
万历帝说:“原来是杨监丞,有何事禀告?”
杨志和咽了口口水,像是在下决心,用颤抖的声音说道:“皇上,臣昨日夜观天象,西北方有星位移动,似摇似坠。”
万历帝有些好奇:“这是何解?”
杨志和脸颊上有汗在往下流,说:“代表西北方有不祥之事发生。”
万历帝大惊,说:“你可知具体是何处?”
杨志和说:“星位于京城正上空,偏移之位也在京城之内,恐怕就在城中。”
万历帝说:“你的意思是,发生在城中西北?”
杨志和点了点头,说:“为了皇上安危着想,今日祭拜不妨取消,择个良辰吉日再定。”
万历帝大怒,指着杨志和鼻子说:“四天前由于地震取消了,当时也是你们国子监说今天是个吉日,现在又说今日必有凶兆,你们国子监是干什么吃的?”
杨志和说:“皇上息怒,选错日期确实是我们的过错,要责要罚回去任由处置,只要皇上取消就行。”
万历帝怒道:“不论今日是何兆,任何人都不能改,要是再提改日,我就让他告老还乡。”
杨志和还欲劝阻,从后面又来一人,拉住了杨志和,杨志和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国子监祭酒,祭酒直接将他拽到后面,杨志和埋怨道:“李大人,为什么要阻止我,要是让皇上继续往大隆善护国寺前行,万一出了差池,岂不是酿成大错?”
李祭酒说:“皇上这在气头上,你这时候去劝他,不仅没用,还会把你搭进去,还是不要再劝为好。”
杨志和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李祭酒质问:“那只是你一人之见,前几日其他人一直观测,都不觉有什么异常,要是错了,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杨志和知道自己说服不了他们,只能叹着气往队尾走去,李祭酒见杨志和回队尾,放心了许多,也往后走去。
这一切钱缤英听到了,作为一个接受过新时代社会主义教育的人,自然是不相信占卜、观星这一说,只是记下了,并没有太在意。
突然,天空阴沉,太阳光芒黯淡了下来,明明是正午时分,却就像清晨一样,天蒙蒙亮,随即而来的狂风大作,仪仗队最前端的一面旗子,忽然折断,掉在地上。
杨志和在队尾看到,深知此乃大凶之兆,又想要向皇上谏言,正要走,李祭酒再次拉住他,向他摇摇头,杨志和只得长叹一口气,不敢妄动。
坐在轿子里面的万历帝,听到外面动静,问轿子外的太监:“王公公,外面发生何事?”
王公公如实回答,万历帝心中不安起来,但自己刚刚才说过,不能取消,怎么能打自己脸呢,于是把情绪埋在心底,只与郑贵妃说笑。
钱缤英看了,内心忐忑起来,史书上没有记载,二月二十日发生了什么大事,所以前方到底会发生什么,也不甚清楚。
王公公悄声说:“皇上,这天气异变,恐怕大雨将至,要不先回宫,祭拜取消吧。”
万历帝有些动摇,但还是回复:“既定之事,如何改动?朕意已决,切勿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