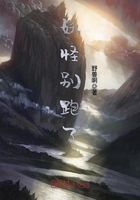听到文桂的声音,父亲快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招呼文桂和金发来客厅里坐下。王欢和两个长辈打了招呼,然后拿起桌上的茶壶,去院子的压水井里冲洗。把昨日的茶叶倒掉后,从橱柜上拿出散装的铁观音抓了一大撮,再冲上保温壶里的开水,给父亲和两位族人各倒了一杯茶。
父亲叫王欢也坐下来一起聊聊天,王欢本来不大喜欢和大一辈的人聊天说事,父亲既然当着几个长辈的面邀请自己,王欢也不好躲着客人走开。王欢给自己倒了一杯浓茶,父亲进到杂货间把瓜子和花生端了出来,问金发和文贵要不要喝点白酒。两人拒绝的很坚定,仿佛急着赶时间要说一些事情。
父亲在上席坐了下来,文桂第一个打开了话匣:
“吴明豪这狗腿子,这次总算收拾了他一回!”。文桂兴致勃勃地说。
父亲很好奇:“怎么了?打了架吗?”。父亲也希望有人能教训一次吴明豪。
金发倒不似文桂的急性子,他娓娓道来事情的缘由:
“过了年之后,村里没什么人赌博了,这个吴明豪就开始来偷运木材赚票子。我们村尽头的那个山坑,杉树都被他砍的差不多了。这几天晚上,我和金发把车子往路上一停,晚上在车里蹲着他。这王八蛋也怂了,最近都不敢来偷运杉树了。”。
文桂拍了一下桌子,理直气壮地说:“他要是敢运,我们就把视频录下来,发到森林公安去,要是想打架,我们俩还怕他?捅出去了,村书记的侄子偷运杉树,还打人,看看他吴长贵的书记怎么当?”。亢奋地说完后,文桂喝了一大口茶水。
父亲给文桂添了茶,冷静地分析起来:
“吴明豪不敢惹大,他可能晚上看到了金发的车子,停在路中间,知道我们要堵他。就转头回去了。”。
“没错,上次夜晚喊人来打了富生,不要找他点麻烦,他还以为我们好欺负?”。金发补充一句,然后转过头,问正在认真听故事的王欢:
“欢古(古,客家话中对男孩的称呼),听说你在单位上班,蛮不错啊,读了书就是好。在哪个县来着?”。
“在瑞水县。不远。”,王欢谦逊又带点自豪地回答。
“有时间来我家玩。”。金发说。文桂和金发很有默契地把杯子里的茶一饮而尽,然后起身要走,父亲留他们吃饭,他们爽快地拒绝了,然后父亲和他俩攀谈着走出了院子。王欢也跟了出去送客,目送他俩往村口人多的路口去了。
王欢在自家庭院门口站了一会,在半坡里的几跺草地上,他惬意地微微俯视这处错落有致的村庄。眼前这个他从小长大的地方,房子已经逐渐稠密了起来,在两条小溪和村道交汇的T字路口,原先只有一排低矮的土坯房,两家供应店隔着一条三米宽的小河遥相对峙,山腰上和对岸的田野之间各分布着十几户人家。
九十年代开始,村里陆续有年轻人出去打工闯荡。那时候要去达广东的沿海,需要坐两天的班车,中途还要在一个山区的小县城住上一晚,第二天再转车。那时,村民去的多是汕头潮州一带,往一些生产半成品的手工厂或者模具厂打工。待他们赚了些钱回来过年后,村里其他的年轻人看到,就都效仿了起来。通过第一批吃螃蟹人的介绍,后面去的年轻人,也在那边找到了工作。尽管只有几百块一月,但比起在家里种田,还是强了不少。
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大浪潮下,大概在2005年开始,外出打工的工资也涨到了一千多块一个月。大部分的村民慢慢还清了在家种田时侯遗留的一些债务,逐渐有了些积蓄,便开始筹备着给儿子结婚,或者把土坯房换成钢筋水泥的房子。现在,村头T字路口的两边已经建成了两排整齐的水泥房,房子贴了白色的瓷板,楼上的阳台还装了不锈钢防盗网。以前是一片甘蔗地的屋后,也建起了高高低低的房屋,还有半山腰上、对岸沿河的田地里,都成了居住区。好几家的农户因为转让土地给本村人建房,受益了不少钱。当然,也有“后进”的人家,2015年之后才开始凑资建房,现在还是没有装修的红砖墙面。也有建好了住宅又开始加设的,比如开供应店的王德敏家,他就在河边两层半的新水泥房旁,谋了一块三十几个平方的地,打算建一个储存室,石砖钢材都已备好了。
王德敏是一个脑子灵活会算计的人,近些年沙子的价格长的迅猛,他寻思着,若要建起一栋小房子来,按照八十一方的价格,保守估计也要两千块钱。倒不如干脆买些甄沙的装置,在屋后河边的浅滩里自己掏些沙子。屋后小河流至两水交汇处,刚好是一片平地,水流向的左岸冲刷形成清冽的崖壁,右边则是一片近百平方的沙滩。王冬敏把甄沙的工具往沙子的一放,自己动手,用粪箕把大小不均的沙子舀起,撒在甄沙的细网上,漏下嫩小柔软的沙子,倾泄于地上的另外两个箕具里。然后,冬敏的老婆春秀拿扁担一抬,两箕沙子就过了桥,运到储藏室的施工地里了。
王欢站在自家院子门口,清晰看得到德敏夫妻俩勤劳忙活的身影。突然,河边的沙地里传来了吵架的声音,德敏家守店的老母亲也走过去了,还有德敏隔壁的刘舒贵,刘连生,也都听到声音赶了过去。
父亲听到吵闹声,从院子里走了出来,他和王欢说:“冬敏是本家人,过去看看出了什么事。”。王欢和父亲与其他邻居一样,见冬敏只是与人争吵,并没有动手之意,便只是站在桥头劝架评理。
与德敏吵架的,是王家湾的本族人宏生。冬敏和宏生一样,从王家湾的半坡里,搬出到离村口更近的位置定居,两家新建的房子相距不过百米。冬敏开了便利店,宏生则是接一些水泥工匠的活儿为业。他们两家的父辈,因为林权的事情不合,早在王家湾的老屋住的时候,两家也不甚往来,如今搬到了村口刘家人聚集的坝上小组,就更是鲜有走动。
本来宏生打算在河滩装满一箕沙子就走,却被不到十米外的德敏夫妇喊住了。德敏觉得宏生是故意给他添麻烦,他也不顾德敏同族人的情面,开口就毫不客气地嚷到:
“我说宏生,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本来做屋沙子就不够,你还要来我这挖,那边不是还有?”。
宏生听到这话,也是来气,他反驳道:“你这又是什么意思?这块地方就你能挖?我离这里近,来这里挖点沙子怎么了?”。
德敏把手上舀沙的容器往地上一丢,一副怒火中烧的神情,他差点要骂出脏话来:
“你就是故意碍我的事!以前在老屋住的时候,你一家人也是这样,就是看不得我家好。我来做屋,算好了的沙子,你就来挖!”。
德敏的老婆也念念叨叨补充了几句:“哪里都是沙子,你怎么一定来这里?这边我都填好了路,劈开了草,做事要有先来后到吧?”。
宏生本就内向,见德敏夫妻俩夫唱妇随,合起伙针对他一个人,他感觉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竟说出了要提起锄头和德敏拼命的气话。幸而是被上前的连生拦住了,父亲也劝动了宏生先行回去,这才把冲突平息下了。
吃过晚饭,王欢的父亲正想把院子的木门反锁上,就听到宏生就打着手电筒来敲门的声音。父亲察觉到了宏生的意图,他肯定是来说白天和德敏的那次争吵,想叫本族人评评理,好占据舆论上的主动。父亲招呼宏有坐下喝茶,宏有带着气愤的口气讲了一大堆德敏的坏话:说德敏以为自己开了店,建了三层房子,就很了不起,一块沙子地都要占掉;父辈赌博输给他的那块林地,也不肯还回于他,等等。父亲听宏生发了好几分钟的牢骚。宏生说完就起身要走,也没有等父亲表完态,他略驼背的身影就消失在黑夜中了。宏生来去匆匆,父亲也没有过多挽留,他知道宏生只是来找自己倾诉一下。宏生只有一个女儿,已外嫁邻县,唯一一个哥哥也几年前病逝了,身边能陪他谈心的亲友并不多。
送走宏有,父亲还没来得及再次把院子的门栓反锁,门外又响起了德敏的声音。德敏亲切地喊着父亲的名字,父亲也热情地招呼他进来,把刚刚和宏生喝过的茶杯拿到压水井冲洗了一下,再给他斟上还未冷去的浓茶。德敏在靠上席的位置坐下了,他换去了白天运沙子时候的工作服,改成了守店时候常穿的灰色西服。脚下的皮鞋虽然不新,但是看起来材质和质量都很不错。德敏从兜里掏出一包红色包装的“金圣”烟,递给了王欢的父亲一根,娴熟地点上火,慢悠悠又态度坚决地说:
“那个宏生矮古啊,就是多做怪,自己鸿水脚子(家族衰落的子孙),就来碍别人做事业!”。
父亲见德敏说人的口气有些重,赶紧来劝:“大家同一族同一房的,要和气一些。沙子的东西,给他挖一点去也到不了哪里。”。
“我垫好了路,清完了草,一看就是我要那块沙子,他就冷屁股捡热凳子坐?”。德敏还是据理力争。
“要这样讲,就算你锄的路到沙坝,沙子还是大家可以运的嘛,宏生好像是搞一两担铺水泥沟,用不了几多。”。父亲为宏生辩解。
德敏依然耿耿于怀:“不是沙子的问题,要两担沙子,他往下游多走几步也有。他就是故意碍我,本来沙子就不太够,他还来挖墙角。”。
德敏又聊到了几十年前的事:“他爸和我爸是堂兄弟,那时候两个人喝醉了酒打赌,他爸把宋坑的一块林地赌输给我爸了,现在那边在开发果业,能拿到租金,上个月,他就问我要回来,说本来就是他家的!”。
父亲也听闻过那件陈年往事,他劝德敏:“今天说沙子的事就好,不要扯那么多过去的事。”。
德敏沉默了一会儿,又点起了一只烟。然后两个人聊了一会儿重建祠堂的事情后,德敏礼貌地和父亲告了别,也回去了。
第二天是4月4日,农历传统的清明节。一大早,王欢和父亲忙着杀鸡歃血,母亲备置小碗里的菜果,各小碗分别是豆腐包、回锅肉、鱼包,白酒和苹果。王欢在草纸上用细的毛笔写上先辈的称呼和名字,然后匀称地在每张草纸上沾几滴鲜红的鸡血。再和父亲一起,在客厅正上方牌位下面的香座旁祭烧了几张。然后,王欢把剩余部分装到一个大蛇皮袋里,连同几个装了菜果的小碗,再带上一把割草的镰刀,打包好上了父亲的摩托车,去村子北坡爷爷的墓地,和隔壁乡太爷爷的墓地清扫和祭祀,顺路还要去太祖母和太爷爷的兄弟的墓地里祭扫。王欢跟着父亲翻山越岭,每到一处墓地就要用镰刀劈开荆棘,拔掉墓碑上的苔藓,短暂的一天过得劳累又充实。祭扫完回到家,王欢快速地吃过提早了的晚饭,拎起母亲打包好的腊肉和豆腐包子,搭乘同村人的顺路车去了县城。他要坐晚上七点办那趟去瑞水的车,好赶在明天一早到达单位上班。
五月,村里的文桂去了潮州的模具厂做事,文桂不在,家里搞种植的金发,自然不会独自去拦吴明豪运木材的货车。不过没想到的是,吴明豪竟换了一个赚钱的行当,他在三岔路口往南八百米的学校拐弯处,找到一块两百平米的荒地。和吊虾公的赌友“葫芦”各自租来一辆翻斗货车。到傍晚的时候,就能听到他们轰隆隆的货车声从村道碾过。第二天一早,那片空地上已经堆了好几跺没有滤过的沙子。几天后,那片不大的空地就被沙子填满了。
村民们先是感到好奇和疑虑,尽管吴明豪在村民那广而告之他的沙子只要45元一方,但是村民还是不敢去买那些来路不明的沙子。直到开供应店的德敏,试探地买了几十方,用来填补他建储藏室的不足,几天后依然相安无事村民们才逐渐相信起来。
王家湾的生才交了五千块给吴长贵后,建房的地批了下来。于是,春节后他也就没去广东,一心留在了家筹办建房的事。看到德敏买了吴明豪价格实惠的沙子,生才也塞了三千块钱去,先预定了60来个立方。吴明豪得钱后,很爽快地迅速把沙子装到了生才楼下。比起在沙场上买,生才硬是省下了上千块钱。生才时常在村民那说起自己多么会打算,却也招来了不少人的口舌。买完沙子后的第二天中午,生才和金发在连生的店子里打牌,金发就开始奚落他:
“生才,吴明豪上次刚和你哥打了架,你又在他那买沙子啊?他那个沙子可不一定合法哦,小心被抓了。”。
生才有些尴尬地笑笑,转而又显得很豁达:“谁会跟票子过不去,能省到一千还不好用啊?再说了,要抓也是抓他,我又没多少责任!”。
“不要那么喜欢贪便宜,生才叔佬。”。尽管两人年纪相仿,但是若按辈分,金发确实要喊生才一声叔叔。
“打牌打牌,不要吵死。钓主!快点下。”。生才知道金发是在狎他,赶紧转移了话题。
不过金发却还是对这个事情饶有兴致,他前年建房的时候就是在沙场买的沙子,花了七十元一个立方。他感慨地说:
“现在的沙子是一年一个价,去年还80,前几日又话涨到90了。难怪吴明豪偷的沙子有销路,沙场的沙子太贵了!”。
坐上席的店主连生带着老花镜,一副谆谆教诲的口气:
“周塘的大老板黄虎,花了三千万,买下了凉江所有沙子的开采权。听说城投公司,每个立方还要收三十块的分红。不卖贵点,黄虎怎么回本?”。
“沙子被周塘老板垄断了,钢筋被东江的老板垄断了,我们老百姓,搞痢疾!”。金发讲话总是那么耿爽又冷静,就像他爱打抱不平的性格一样。回到瑞水上班的第一个中餐,王欢就把一罐子的腊肉带到了单位的食堂。他只身一人在这边上班,心想着,一罐子肉一直放着也不是事,不如带来食堂下饭,还在增进些胃口。只是这诺大的单位食堂,带菜来的人并不多,更何况是王欢这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吃完饭,王欢走过食堂侧边的花园,打算去办公室休息一下,顺便在电脑上看看篮球的新闻。在木制步道旁靠近一座凉亭处,他看到了林彤。她正往停车场的方向走去,应该也是刚吃完饭,打算骑车回家午睡。
王欢慢跑了过去,步子踩在地板上蹬蹬作响,直到王欢走近了林彤,轻轻喊了她一句,林彤才回过头来。林彤微微一笑,王欢转而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脑子里灵机一动,鼓起勇气问她:
“你那么早回去吗?在这花园里散散步吧,消化一下”。
林彤有些迟疑地说了一句:“好的”。于是,两个人沿着步道把花园走了一圈,边走着,王欢谈起他清明回家的一些趣事。王欢琢磨着,林彤应该会对农村的习俗有些兴趣。花园不大,聊天间不觉已走了两圈,竟又回到了起初那个亭台里。林彤转身在亭子下面的凳子里坐了下来,她说:
“休息一下吧。”,她的神情有些惬意,也是是因为不冷不热的春季阳光正好。王欢对自己提出的散步的建议很满足。
王欢在林彤边上坐了下来,两人隔着近一米远。她怕林彤会介意,所以不敢挪得太近。刚坐下,王欢突然就叹了一口气。
林彤转过头,瞪大了眼睛问:“你怎么啦?”。
“就是对家里的一些事,有点感概。”。王欢仿佛找到了一个契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觉得自己压力挺大的。我们老家那边,传统观念,宗族观念很强,家里对我的期望比较高。感觉自己这种小科员,提拔很难,可能就平平凡凡过一辈子了。”。
林彤安慰起王欢来,她说:
“你现在有一个正式的工作,还可以了。而且,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不用管太多别人的想法。”。
“可是。”,王欢有些迟疑,转而又坚定地回答:“一个男的,不太可能不去管别人的看法,就像我家那边一样,自己有出息的话,家人族人都不会挨人欺负。”。
王欢微微转头看着林彤的眼睛,马上又闪躲开了,他又补充了一句:
“一个男的,如果什么都没有,怎么让自己喜欢的人过得开心?”。
林彤有点晃神,好像理解了王欢的意思,也许也没有,特别是王欢说的最后一句。林彤沉默的样子,思考的样子,在王欢眼中总是那么动人,淡黄的长发,微圆的脸颊,还有不时眨动的温柔眼神。
林彤站了起来,打破了凝固的气氛,她微笑着说:
“那我先回去了?下午还要上班。”。
王欢有些措手不及,他好像还没和林彤说完想说的话:村子里采砂的故事、扫墓的习俗、或者别的什么。他也赶忙站了起来,手中红塑料袋子里的罐子沉沉地挂了他一下,这倒提醒了他,他拿起袋子,举到腰间的位置,喊住了林彤:
“等一下。这个送给你吧,家里自己做的,腊肉腊肠鸡爪,都有。”。王欢拿出罐子的手有点抖。
林彤举起手臂摆动了好几下,礼貌地拒绝了:“不用不用,你留着自己吃。”。
“我走了哈,拜拜。”,林彤优雅端庄的步子,踩在木道上也蹬蹬做响,她穿的是增高的黑色皮子鞋。
王欢仿佛感觉到方才林彤礼貌拒绝的时候,也许还有一丝尴尬的味道。他看过院子里参加了工作的男女,他们谈恋爱,多是送花,送蛋糕,或者买衣服之类。自己第一次给林彤的东西,是一本十块钱的地摊书,这次,又是满满乡土气的腊肉。王欢觉得,刚才说的那种只顾自己开心,却给不了爱的人快乐的人,好像说的就是自己吧。
花园里的橘树开了白色的花,引来了几只蜂蜜,和一个白色的蝴蝶。王欢许久没有见到蝴蝶了,他拿起手机,赶紧跟随那只蝴蝶,想拍几张照片。刚调好拍摄的角度,那只蝴蝶就悻悻地飞往围栏外了。王欢只好只身回到办公室里去。
独自在外地上班的日子闲适又无聊,少了家人亲戚的唠叨,但同样远离了能够撸串饮酒的好朋友。上班时候的同事,下了班基本上没有交集。单位下班的时间其实挺早,比起高中时候九点半才结束的晚自习,已经算再也舒服不过了,下午不到六点,就可以去拥抱一晚上的夜生活。起初来到这个老家隔壁县城的那几个月,王欢对这个城市充满了新鲜感,县城的每一个公园,每一条繁华的街道,包括略有名气的上点档次的网吧,他都走了个遍。
瑞水比起禾县要繁华不少,城区里,放眼望去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只有在城市在尽头,能看到隐隐约约的群山。而禾县就不一样了,禾县县城绕水而建,依山而修,窄小而失大气。尽管单身的日子,有如此多自由的时间,但是王欢能想到的娱乐方式倒不多。因为没有多少志趣相投的玩伴,中学时喜欢打的篮球,也有大半年没碰了,上次打球,还是过年的时候,和高中同学在老家学校的院子里。不仅打篮球凑不齐朋友,就是两个人可以玩的台球、羽毛球,也很难邀到人。于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逛完了大大小小的公园和街道,看腻了热闹的广场舞和带孩子的夫妇后,王欢对晚上出去溜达,也就失了兴趣。他开始一下班就往网吧里跑,轻盈的电动车停在网吧楼下,找个冬暖夏凉靠空调的位置一坐,点一杯奶茶,玩上一晚的英雄联盟。再尽兴不过。
连续上了一周的网,再好玩的游戏也会腻。难得一次早早回到住处,锁了门窗,开启窗台灯,靠在床上刷刷朋友圈,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当然,刘永也会偶尔给林彤发微信问候,只是有时候对方回的并不及时,或者只是简单回复“嗯”或者“好的”。这让王欢觉得,自己似乎应该减少打扰对方的次数。
五月初的一个晚上,王欢还是照例在高中同学群,聊着nba转会市场的新闻,只见“王家湾子孙群”里,难得热闹了起来。好几个老乡发“点赞”或者“鞭炮”的表情在群里,仿佛发生了什么大好事。王欢好奇地把聊天记录往上翻,只见一条标题为《我县成功破获一起非法采砂案》的《禾县资讯》栏目新闻链接格外显眼,是金发在晚上七点零六分发出在群里的。随后,文桂,章明,还有王欢的父亲,都发出点赞或者庆祝的表情,王欢好奇地点开了新闻链接,细细阅读起来。
原来是村里的吴明豪,偷来的沙子没卖到半个月,就被矿管局的执法大队发现了。前天夜里,执法大队队长章子平亲自带队办案,河口镇派出所也派了两个民警来协助,一个是副所长刘晓文,一个是协警刘勇。打探到吴明豪一般晚上九点开始运沙,执法组一行六人掐好了时间,把警车和矿管执法车往村道上一横,等着吴明豪和“葫芦”的货车自行投网。
晚上九点刚过,村道与省道交汇处,通往沙坝的那条小路上,就响起了轰隆隆的卡车声音。两辆载满沙子的卡车从杂草丛的小路开上了村道,正打算加速往东庄方向开去。前车打头阵的吴明豪一开远光灯,正照见路前一辆白色的警车和矿管的执法皮卡。在车上的刘勇发觉目标出现,立马打响了警报。站在马路两旁的执法人员,迅速往打头那辆货车的驾驶室围了上去。吴明豪见情况不妙,欲掉头绕道,无奈车宽路窄,后头还有“葫芦”的车累赘着,只好选择下车开门逃跑。车门刚打开,还没来得及跳下驾驶舱,执法大队的章队长和派出所刘所长就上前把他拦住了。章队长出示了执法证,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严肃又正气凛然地说:
“我们是执法队的,下车,接受检查!”。
刘永和矿管局的另外两个工作人员也把后车的“葫芦”围住了。那吴明豪和“葫芦”尽管腰宽膀圆,见执法队人数不少,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乖乖地上了警车。章队长把两辆运沙车开到路边贴上了封条。
当晚,吴明豪和他的同伙以“涉嫌非法采矿”罪,被扣留在河口镇派出所接受审讯。那晚是刘永和副所长一起值班,把两个人押送进派出所的时候,吴明豪冷冷地看了刘永一眼。刘永虽然没和吴明豪打过交道,但是他断定吴明豪肯定也认得他,毕竟小小的东庄村就一两千号人,自己在派出所上班,差不多村里都传了个遍。吴明豪那冷冷的带着杀气的眼神,还是让初做协警的刘永不寒而栗。
第二天一早,矿管局的黄副局长和章队长从县城下来了,他们和派出所黄所长一起,亲自受理这个案子。因为人证物证具在,还有被处理过的举报人的录音,吴明豪非法采砂的罪名也就做实了。询问的过程中,吴明豪表现的很淡定,他没有做任何的反驳和抵抗。由于认罪的态度诚恳,加上所盗采的沙子并没有带来太多违法所得,同事说,吴明豪可能就是被看守所拘留一段时间,再罚款几万块的样子。
已经到了上午下班的时间,黄局和章队才在所长的陪同下从办公室里出来。刘永也刚好下班,正巧在门口遇见他们一行,刚要与所长打招呼,父亲就打了一个电话过来,刘永拿起了手机。
电话那头,父亲的语气听起来有些着急,他问刘永:
“永古,昨天晚上你们是不是抓了吴明豪?”。
“是啊。怎么了?昨天刚好我值班。”。刘永有点纳闷,消息怎么传得那么快。
“今天一早吴长贵到我们家,他说你到抓了他儿子!”。父亲一副摊上了事儿的口气。
刘永对父亲的反应感到有些惊讶,他赶忙解释到:
“昨天我值班,而且这个任务是临时接到的,我和副所长去的,什么叫我抓了他儿子?我哪有那么大权力啊。他也知道我只是个协警。”。刘永有些委屈地解释着,他发觉自己讲话的声音有点大,为防被同事听到,他加快了步子往后院的停车场走去。
父亲还是很坚定自己的想法,他劝刘永:
“话是这样讲,但是你当时毕竟在场,而且大家又是同村的,你也晓得吴明豪和吴长贵的关系。吴长贵和我讲的意思是,你最好打给电话给他,解释一下,说说情况。”。
“我为什么要像他解释啊?难道他还要我向他道歉?”。刘永有些怒了,他俨然已经感觉到了吴长贵给父亲的压力。做为家里的独子,如果父亲被人威胁甚至恐吓,他哪里坐得住。挂完电话,刘永就骑着摩托车,迅速往东庄的老家去了。
中午十二点半,回到家的时候,父亲在幽静的厅堂里一个人吃着饭,见到刘永回来,父亲露出了笑容,他站了起来,问刘永:
“永古,回来了啊。吃饭了没?”。
刘永这次没有和平常回到家一样愉悦,因为父亲电话里的内容,让他高兴不起来。他和父亲说自己还没吃饭。父亲就转身想去橱柜里给刘永拿碗筷,刘永说:“等一下我自己来吧。”。刘永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拿碗盛饭,他悄悄地走进大厅左侧的房间里,那是女儿专属的小房间。他看到六周岁的女儿朵朵,躺在挂着蚊帐的床上睡着了。肉嘟嘟的脸蛋下,是被爷爷铺得满满实实的小猪佩奇粉色毯子,看到女儿一天天长大,头发都长得稠密柔丽了起来,刘永心中涌出无限的喜悦。他凑过头,对着发出轻微鼾声的女儿自言自语:“爸爸,爸爸。”。
刘永把女儿的被子又往上提了一点,然后轻轻走出房间,随手关上了门。他拿起碗,盛了不满的一碗米饭,一边坐下一边问父亲:
“妈呢,又去做小工了吗?”。
“是,去吴坑吴小有家挑沙子,那里有饭吃。所以我也没炒菜,随便搞了一点,没想到你会回来。”。桌上是一碗菜干烧肉,一碗过年腊的鱼干,还有一份清炒花菜。看得出,父亲只是炒了一份青菜,再把昨天的两个菜热了一下。
刘永说:“没要紧,我随便吃点就好。”。父亲发觉了刘永不大有精神的表情,他感觉得出,是自己刚才那个电话给儿子带来的压力。
父亲开口和刘永说:“刚才我说的那个事,你要是不想去和吴长贵说,就算了,我就是那么随口一提。”。
刘永问父亲:“那吴长贵,没有说你什么吧?”。他对吴长贵的工作作风,也素有听闻。
父亲赶紧摇了摇筷子,说:“没有没有。”。
父亲继续问:“对了,永古,静雯那个调动的事,镇里安排的怎么样了?”
“上次所长和我说,镇里罗书记已经和人社局王局长沟通好了,等过几天陈副县长回来,签个字,差不多就可以了。”。刘永嚼着又硬又油的菜干,提到这个话题,他的神情又轻松了许些。
父亲放下了碗筷,说:“那就好。”,他轻轻叹了一口气,继续补充道:
”是这样的,永古,这个调动的事,我上次也托吴长贵到找罗书记吹吹风,等于也算帮了下我们。昨天叫你打个电话给他,说说他儿子昨天被抓的事,也算是一个人情,毕竟你参与了。并不是我刘健发会怕他,你不要误会了。”。
吴长贵在自己妻子的调动上是否起到了作用,刘永还是持怀疑的态度。既然父亲说了,和吴长贵“道歉”的事就此作罢,而且自己家里,也没有受到吴家的威胁。刘永也就不想再过多纠结此事。只吃了一碗饭,刘永就放下碗筷站了起来,他对父亲道别:
“爸,所里还有点事,我去上班了哈。”,刘永一抬头,看到客厅中央的橱柜上面,放着一瓶喝剩一半的剑南春,边上有个半黄半红包装的酒盒子。
“可以啊爸,难得看到你喝这么好的酒。”。刘永说。
父亲的回答有点闪躲和结巴:“噢,那个酒啊,是那个,你那个舅爷送的,他来村里送帖子,刚好路过我们家。”。
“好吧。那我走了哈。”。眨眼的功夫,刘永已经拎起钥匙走出门外了。
“开慢点。”。父亲嚷出一句,伴随着一声摩托车的轰鸣。
五月,中午的街道已经有些闷热。刘永骑了20分钟就到了镇里,路过自己租房楼下的荣诚商行时,他停下了车,打算进去买一包烟,然后去所里准备上班。老板娘依旧穿着那件蓝色防水的工作服。他要了一包金圣瑞香,正要扫码结账的时候,无意中看见老板娘身后的货架上,摆着一瓶和刚才父亲那看到的,一模一样的剑南春。
刘永顺带问了一句:“老板娘,那个52度的剑南春多少钱?”。
老板娘回头指着那个上黄下红的盒子,问:“你说的是这个吗?”。
“没错。”。刘永说。
“四百多。”。老板娘看得出,刘永并没有多大的意愿要买。
“上次你爸到我这也买了一瓶去,这个酒蛮好。”,老板娘碎碎念地补充道。
刘永很惊讶,父亲不是说那瓶酒是舅爷送的么。他怀疑是不是老板娘记错了:
刘永疑惑地问她:“不是吧,你确定没认错人?”。
“你爸,基本上每次圩日,都会来我店里买东西,我怎么会搞错”。老板娘一副阅人无数的样子,他的回答很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