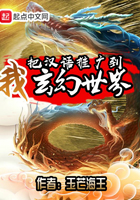十四
大约两天后,我已经是一家酒店的服务员(也兼传菜员)。这是一家连锁酒店,听同事们说,它的总部在罗湖区,在一处非常繁华的商业区。
这家酒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它的宴会大厅,这间宽敞的大厅最多能同时容下四百余名客人用餐,能摆放四十多张餐桌。而也就在我来了不到四天,这里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当时来用餐的客人就超过三百多人。也许让我这么长久的记住它,并不仅仅只是它的宏伟,而是这里在大多时候都是这家酒店最安静的地方;婚礼不可能每天都有,但包厢里的各种请客应酬每天都会发生,而做为一名“特殊”的新人,我总觉得自己没办法与这里的一切融合,我永远是一个另类。而做为一个另类,我需要的不再是交谈,而是独处的宁静,刚好,这间宴会大厅就很好的满足了我的要求。
我记得那时我常坐在它的西北角下,这里总会被隔板隔成一个个小包厢来应对酒店包厢常年的供不应求。可我总觉得领导方有些多此一举,因为没有几个客人愿意坐在这里,她们当然有很多理由,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里没有卫生间。我觉得她们很有远见,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客人一打开门就看见我坐在黑暗的角落里而不被吓到的,而且非常巧的是,这里的门非常难推开。那么你们就可以脑补一下,当一位漂亮的女士在惊慌失措时想要逃离,可门怎么也推不开,她们的表情会有多夸张?她们的心情会差到什么程度?总之她们以后是不会再来这家酒店用餐呢。幸运的是到我离开这里之前,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这也许是她们的幸运,也是我的幸运的。试想当你在无穷地感受宁静带给你的安慰时,你有多不情愿被人打扰。
有时候,或者说也是直到今天,我总会去想,这家酒店身处在繁华的商场内,你不用走出大门,就能被外面的喧嚣笼罩着。可这间宴会厅,与那扇大门之间只有一条不到十米的笔直的过道,而你坐在它的墙角下时,像完全来到另一个世界。我想当时除了我,没有人再来这里感受它独有的魅力,他们仿佛是与他们服务的客人一道来的,现在也应当一道离开,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从未想过去寻找他们,如果我感觉到乏味,我会推开里间的大门,在红地毯上朝最远处的舞台走去。当然,我也想过将所有的灯打开,然后为自己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那样的话,我的领导们将会成为我的第一批观众,也会是最后一批。老实说,我不想唱给她们听,就算她们付过钱也不行。这个时刻只属于我自己。我曾经见过一些人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她们演得很好,技术非常到位,但我总觉得她们缺少点什么——对,就是自由!这个舞台不管有多华丽,它毕竟太少。如果她们能跳下舞台,在客人间自由的穿梭,那一定会迎来更多的尖叫,只不过事后,她们可能会在精神病院里呆上一段时间。而我与她们不同,现在这里没有客人,所有的餐桌都被收进了库房,要是我愿意,在这里踢足球也没关系。这样你们就能想到,这个时刻于我来说有多重要,不过可惜的是,那时我的心仿佛被一张坚固的铁网死死的锁住了,尽管我很想像我说的那样,结果却是我很绅士的双手插进口袋里,慢悠悠地在红地毯上踏着自己的碎步。那样子真像是铁定心要踩死路上所有的蚂蚁。
这样的闲散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再次感到乏味,之后我就会走到舞台边,挨它很紧,非常近。我抬起头看着它后面的大屏幕,以及就在我左前方不远处的讲台,我不知道我从这些东西上察觉到了什么,我只是觉得此刻非要在它们身上用尽自己的时光。也许我会想到这些:当我每次推着餐车从舞台边走过时,我从来不抬头看它,我发现在那个时候它的身上透露出一种威严,这种威严只有在这里用餐的客人中的佼佼者才会拥有;他们或很有钱,或有高地位,或有才华,或者生来就很宝贵。在面对他们时,我会自卑,这种自卑发自心灵深处,正因为此,我才会将这个舞台当作他们的化身。每次躬着卑微的身体从它面前走过时,我都有点无地自容什么的。这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我曾想过对我的领导们倾诉,我想请她们教我战胜它的方法,可我很清楚她们一定会说“要自信!你跟他们一样!”这句话很有道理,但对当时的我来说类同废话。也许现在倒是一个好机会,是向自己证明自己的好时刻。然而问题又来了,我到底要向自己证明什么?证明我跟他们一样,很显然,这个并不需要证明!证明我很自信?这个恐怕证明不了,自信应当付诸于某件具体的事物上,而我现在纯属无聊。所以只好笑着叹了口气,便提腿迈上舞台。请注意!这是历史性的时刻,是我第一次登上它,如果你能感同身受,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内心正被一股强烈的激情所冲击,它迫使你想要做点什么,比如大吼几声,比如手舞足蹈,比如将讲台推翻,比如一拳打烂电子屏,再比如,躲在讲台下屙一坨屎。好吧,这真是太恶心呢!如果我真这样做了,我不为自己感到羞耻,那说明我一定是疯了。幸好我想到这些时,我用力地摇了摇头,然后傻笑一下,便仰望着天顶与那些装饰豪华的吊灯。
这样子看上去一定像个工地的监工,实际上我能看见的部分非常有限,差不多就是每个灯槽的边框。而连我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那样入迷地望着它,而且一站就是半个多小时。更加吊诡的是当我垂下头颅后,我会感到无比的失落,就像五脏被人掏去了似的,这让我感到非常无措。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坐在台沿上,像与余婷坐在广场舞台的台沿上一样,只是现在我扭过头看见的是舞台的另一头。
其实我非常缺乏勇敢,每当以这样的方式想到她时,我就恨不能找块蛋糕撞死自己,可谁都清楚,再多的蛋糕也撞不死我。最后我还得面对眼前的一切!我实在不想再面对这些,我多想抛弃它,然而当你真的能够狠下心时,你又有点舍不得它。仿佛它是你身上原本就有的,只是现在它病了,可不管这病带给你多大的痛苦,你也无法将其丢弃,因为你一旦失去它,你就失去了活着的全部意义。这听上去真是很糟糕,但幸运的是已经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了,我能奢望的,就是任时间流逝。这个过程也许很漫长,可如果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只有我一个人躲在漆黑的角落里,就算再漫长,也不会增加更多的煎熬。反而越往后,这种简单的时间疗法变成了我人生中的一种享受,正如我之前说的那样,我享受这里独特的宁静,相比于这里的豪华,它更为难得与珍贵!
所有的改变在我来到这里二十余天后悄然发生。这天我难得的在休息之时来到包间的过道里。那时这里一样非常安静,如果你推开门,就会看见每张沙发上都躺着姿势各不相同的酒店的员工。我没想过打扰她们,我当时的目的只是想在过道上走走,因为我已经非常厌烦躲在角落里了,我很希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还没想过与别人交朋友什么的。
那天我走到二楼第四号包厢时——现在想来我真的不该往那里走,毕竟当时我已经看见它的大门没有关——我好奇地朝门里张望着,但什么也看不到,我没有多想就往前走去,刚走到门口,一位名叫曹蓉的女服务员冲了出来。她见到我后,抱怨我吓到了她,然后又当作无事地走了。她绕开我的同时,我听到里头有人在问外面是谁,其中一个声音非常熟悉,像我的室友张红海。我本想走开的,无奈我的另一位名叫郭树青的室友与一位名叫李伟的传菜员就走了出来。我不知道他们是何时将我当成他们的好朋友的?或者说他们是从哪个方面认为我已经是他们的好朋友的?这两个家伙莫名兴奋地说了一句你来了,然后不容反抗地将我拉进了包厢。我觉得自己被侵犯了,如果当时你也在,那种愤怒之情肯定很快就会化成一脸的疑问:因为出现在我面前的情况,仿佛他们正在进行一席酒会,所有人都胡乱的坐在大餐桌同围,餐桌上的东西是客人们剩下的,但并不是全都出自这个包厢,而是从别的包间收集过来的。我当时非常惊讶,但更多的还是不好意思,我决定要走,可张红海却从锅里捞起一块硕大的羊肉,走到我跟前请我吃下。我觉得他太客气了,这么大一块我根本吃不下,我当时很想跟他说“要不你用刀切小块一点!”可还没说出口,我就先吐了,吐得一塌糊涂。所有人见了都觉得好奇,但也表现出了我认为正常的一面:她们从餐桌上下来,将我扶到沙发上,并且送来了开水,而本包间的负责人没有一点怨言的将我的呕吐物清理走,再将米白色的地毯洗得干干净净,像刚从厂里送出来的一样。
这天过后,我突然对我的室友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本来平时我们话不多,而现在我居然怀疑他们会在哪天晚上将我杀死,然后分尸,卖给黑心包子店,做成人肉包子。我想我一定是《水浒传》看多了,总担心这社会有很多像张青夫妇这样的人存在。但不可否认,那种恐惧的感觉太真实,以至于从那之后好长时间里我的睡眠也被完全搅乱,经常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似地睁开眼偷瞄眼前的一切。有时我还会故意咳一声,意在告诉屋里的人,我还醒着,要杀我没那么容易!
说真的,我那时差点把自己弄疯,因为失眠已成常态;每天都以一副疲乏的状态应对工作,好多次被客人骂,最后都是我们的经理来帮我解围。每次她帮我解围之后,我都担心自己要走人了,可每次她只是很和蔼的说了我几句,就让我回去接着工作。提到我的这位经理,我得在这里介绍一下她,她可真是我见过最好的一位大姐。她姓徐,名少英,河南南阳人。我认识她时,她已经三十有六,虽然平时她一般都只化淡妆,但姣好的肤貌让她看着像个二十出头的女孩。也许吧,我没有在那个艰难的时期离开这里,有一部原因在于她的体贴与包容,否则我很有可能又一次流落街头。尽管这样,我也没有将自己的担忧告诉过她,我选择一个人承受,毕竟我也很快找到了一个他们不敢杀我的理由。这个理由非常简单,他们杀了我之后,他们就永远也回不了家,这里的警察会按酒店里从他们身份证上抄录下来的地址去他们家里逮人。有了这条理由之后,我开始试着改善自己的睡眠,我越来越希望能用一个好的状态去面对徐大姐,去面对我的工作。
不过在完成改变之前,有一件事情不能改变,那就是我仍会不时的查看一下他们,这次不是担心他们会来杀我,而是看他们何时能睡下。因为自从长时间失眠之后,宿舍不能得到彻底的安静,我就无法入眠,唯一能保证这一点的,就是这两个家伙先睡下。事实上,他们从不在我最佳入睡时间到来之前安静下来,那么很显然,这个晚上我铁定又要失眠。不过这次的失眠跟之前的有点不同,之前的原因全在我,我没有可谴责的对象;这次责任在他们,所以每次被搞得睡不着后,我都会怒为中烧,但每次我都忍住不发作。因为我觉得还不到时候,毕竟我还是会担心他们有那个想杀死我的想法,就算之前没有,往后被一激怒,说不定就有了,那样就真是自取其祸!为此我在等待时机,可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什么时间才算好的时机,也许只有不断地包容才是最好的机会?
关于我这两位室友,我想介绍的并不多,他们的名字我刚才也都提了,一个叫郭树青,一个叫张红海,都是非常一般的名字,而且还多少有点土。至于他们的为人,毫不夸张的说,他们肯定是我见过能将厚颜无耻处理为坦然的最强能手。这也许是他们的优点,因为很多客人都喜欢他们,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们能经常拿到小费。虽然公司规定私自收取客人的小费是要罚款的,但在徐大姐仁慈的管理之下,这已经成为我们所有人默认的条文,甚至在很久之前,这里的人就将拿到客人小费作为评判能力的标准。
有时候我很想请他们教教我,要怎样做才能更好的服务客人,但一想到他们那种厚颜无耻的笑容时,我走到他们所在包厢门前的腿也会立即转向徐大姐,然后我就非常纳闷的坐在她对面。她几乎从不教我圆滑处世的技巧,也不提倡人要精明老练,他甚至更不提倡这里人常说的“眼观八方”的机灵。她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人要真诚,她认为最好的服务就是真诚,如果你真诚了,你就会全心全意为客人着想,如果你做到了全心全意为客人着想,你就没有服务不好的客人,那你也就是最优秀的员工。她这样说完之后,我在心里非常叹服,我真搞不懂她为什么不去竞选村干部,以她如此洞察人性的功底,干好一个村长完全不在话下。
也许全中国会因为她没有去竞选村干部而使一个村子少了一位好领导,但在这家豪华的酒店里,我却多了一位心灵上的导师。我想她并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心灵导师,也是这里所有人的,不同的是,这里很大一部分人都对她怀着一种高远的敬畏之心,认为她太高大上,可望而不可及。这当然是她们的愚昧之处,可也很能看出,她非常有管理才能。一位出色的领导并不一定要霸气外漏,儒雅厚爱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管理方式。这大概就是我小学时听过的人性化管理,不过老实说,我长这么大也只见过这一次,而且之后也没再见到过。
但这样的幸运已经非常足够,在与她的十数次交谈之后,我终于有勇气把自己的怒火发泄出来。
这天凌晨左右,那两个家伙还在叽叽喳喳的聊个不停,内容全部都是色情,是关于他们前些天跟某个在酒吧认识的女孩子发生的一夜情。我当时像根木头似地从床上立了起来,走到张红海的床边,一把抓住他上层的床沿,疯了似地摇动。他被我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过了好一会才一脸无辜的问我干什么,我没回答他,朝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回自己的床上躺着。这个简单粗暴的办法果然很有用,我看见他俩相互觑了一下,整个房间就安静了,而且是从未有过的安静。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是来这近一个月里睡得最香的一次,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
谁说不是!自从那晚之后,这两个家伙居然用正常人的态度与我说话,而不是莫名地把我当成好朋友。谁都知道那是他们对待陌生人的常用套路,意在麻痹对方。现在终于见我不吃这一套,他们便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对待我,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他们最真实的一面,但我想离真实也不会太远。虽然多少有点遗憾,我还是很欣然接受他们了,毕竟我也觉得需要交几个新朋友。
与他们做朋友并不容易,这两个家伙都是老江湖,每次与他们处在一起,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幼稚园的孩子。与其他人相处也差不多,虽然我几乎每天都会在休息时出现在她们当中,但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我很相信自己于她们来说很像一幅挂在墙上的画,或者摆在角落里的一棵假树。虽不碍眼,却也足以算是无视。这种尴尬是漫长的,漫长到终于有一天她们已经公认我就是个不善言词的呆瓜,漫长到我自己也相信不说话才能更好的与她们交往。反之,我也只好再次回到宴会厅的角落里。
转机发生在除夕夜的晚会上。这晚我们八点半就下班了,在将手头的工作收尾之后,九点钟之前所有员工全部集合到宴会大厅。原本是有表演节目的,但大伙都太累了,于是所有节目都改成了抽奖,当然,还有一席丰盛的酒宴。
那晚我很有幸与这两个家伙坐在一起,这不是酒店特意安排的,而是我发现这张桌子最偏僻,想着坐在这里就不会与他们碰在一块,谁料这两个家伙因为客人走得晚,将包厢卫生清理好之后,其他桌子都坐满人了,他们能选择的就只有我这一张。他们来时显得很匆忙,满头大汗,看得出来,他们非常重视这次晚会。也许正是出于重视的原因,他们平时那种嘻皮笑脸的风格瞬间霁为一种严谨而深沉的作风。这让我在短时间很不适应,我觉得他们是在装的,但每次看见他们认真的注视着台上抽奖的样子时,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
所有人都有抽奖的机会。我那晚运气不怎么好,跟所有运气不好的人一样,拿到了一厢日用品。这算是酒店给员工的福利,因为所有人都有。那两个家伙运气稍微好一些,每人各得了两百元钱,另加一厢日用品。他们拿着奖品回来时,依然很严肃,至少我没见他们笑过,但这时我能从他们脸上看见非常明显的克制。毕竟没有人得了奖而不高兴的。当然,他们也表示了自己的大度,将那个硕大的红包递给我们每个人欣赏了一下。当那东西传到我手上时,我就想把往里头吐一泡口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觉得这么大一个红包,里头居然只有两张人民币,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太夸张。如果说获得这个奖品的人是我,第一眼看见这个大红包时,我一定认为里头至少也得有两万,那样的话,我顶多干完这一个月,然后辞工,去外面好好享受几天。可当我发现里头只有两百块之后,我觉得自己被人戏弄了;我当时会忍住,但下来之后我就会偷偷地把它撕得粉碎。我稍微瞟了一眼这个红包,就将它递给我左侧那个家伙,他当时已经非常迫不及待。
红包传递一圈之后,张红海站起来,举起酒杯要给我敬酒。我本想拒绝他说自己从不喝酒,但我发现那时没这个勇气——在这样欢庆的时刻,说出这种话,一定会让人家误认为我看不起人家——所以我也起身,拿起酒辈与他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这应该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这一杯刚下肚,另一个叫李家兴的家伙又来了,接着是郭树青,再接着……我忘记他名字了。反正这种事情有了开头,就会持续下去,不同的是不再是他们敬我,出于礼貌,这次是我回敬他们。
坦白说,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喝过酒,记得最近一次,还是一年多前与同学们在深圳那家五金厂上班时。那时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去夜市喝个两三次,总是不醉不归。虽然那时我们只能喝一些质量低劣的啤酒,但更多的是感受那种欢快的气氛,如果那时你也在,一定会觉得我们跟天上的神仙没什么不同。不过这次,虽说也喝了不少,但气氛终究太平淡,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在酒桌上是没有大喊大叫的。这样的酒桌我不喜欢,可却没办法退出或者使其停止,我们就这样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感觉那不像在喝酒,而是喝着某种特制的白开水。而且仿佛永远也不会喝醉。
————————
工作与生活又一次相对于过去那段糟糕的日子来说真正意义上的走上了正轨,至少我不再需要独自躲在宴会厅的角落里才能打消休息时的无聊,更不必担心会有人趁我睡熟之后取走我的性命。我的行为变得自然起来,就像回到大哥的工厂,但多少还是有点差距的。这点差距我说不好是什么,总之它非常真实的存在,而你又没办法将它找出来,像这种差距是永远都消磨不掉的。
不过这也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不太清楚从哪天起,我也像其他人那样称张红海为阿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虽然我还是不敢确定我们之间的友情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或者这种友情是否牢固,至少在除去特殊的情况下的大多时候,我们就像——或者看上去像一对关系非常要好的朋友。
当然,与郭树青也差不多,但他有女朋友,虽然他几乎每天都住在宿舍里,可总觉得跟一个有女朋友的人在一起,永远也处不出那种非常有味的友谊。我说不好这是为什么,大概只是我想多了,反正就是觉得他们跟我们这种光棍不是同一个世界的。而且时间久了,我也发现他与阿海的关系并不像我之前认为的那样亲密;而且越往深的了解,他们之间的罅隙就越大越深,仿佛你会突然认为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真的成为了过好朋友,之前你所看到的都是他们演出来的。也许未必,至少当一方生病之时,另一方会请假来陪他。这看上去非常让人感动,但却很难真正的打消我的猜疑,我始终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很不愉快的分道扬镳。
这当中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刚才不是提到了郭树青并不常与他们女朋友住在一块嘛,这段话看上去没什么毛病,但如果你问他们在一块的时候会在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们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会去旅馆,而是郭树青会把她带到我们宿舍,然后他会让我们出去,等他们干完事了,他才会让我们进来。我记得有一次,下着大雨,天寒地冻的我们在走廊里等了一个多小时。进去之后,他女朋友居然还躺在他床上,眼神无辜的看着我们,就好像是我们突然闯入她家里似的。那次阿海没有与他争吵,但我看得出来,他已经忍无可忍。其实我是很能理解他们的,一个月几百元的收入,根本不足以在外面租房过活,他们选择在宿舍里满足彼此的欲望就变成了唯一可选的方式。
也正是出于此,每次在外面等他们完事,我都没有抱怨过。有时我还会提议阿海去外面上上网,但每次他都嘟哝着蹲了下来。就像一位淘气的孩子在生大人的气似的。那时我就会趴在护栏上,望着对面房间的窗户,回想着什么;我大概会想到阿黄,他俩还真有几份相似,都是个子矮小,相貌有点怪异之类的。不过阿黄要比他单纯太多,虽说他已经四十好几的人呢,却像个十几岁的少年,你总能从他身上得到许多天真的念头,有时这些念头会令你哭笑不得。就拿他常说的那个大仙,我是从来都不肯信的,这世间会有如此的神人,就算有,这等人还不用自己的法力去挣大钱,怎么会那么好,宁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替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做好事。这样想来,他说的这大仙不仅法力高强,而且人格也特别伟大。我当时怀疑过,这会不会是阿黄幻想出来的:他受到的迫害太深,所以才会幻想出这样一个厉害的人物来替自己报仇。就像我们传统中国人喜欢看武侠小说一样,总会幻想一位大侠替自己除掉恶霸与贪官。这两者是一种精神上的意淫,是自我的安慰,听上去很是搞笑,细想不觉的心酸。
而这样想来,郭树青与他女朋友的事情与阿黄的事情这两者之间有形异质同的意思,它们都体现出了做为一个像他们这样下层人的无可奈何。也许光是了解到这些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如何从更大范围的去包容他们。因为人性总是很容易由给予而变成习惯。接下来这件事情就很能说明事情:
我不清楚那是哪一天,大概是两个月之后吧,那天晚上我跟阿海从网吧回来。进去之后看见郭树青光着身子搂着他女朋友坐在床上,灯亮得很大,进去时门也没有上锁,仿佛他们这是有意让我们看见的。我当时有点惊讶,这是我第一次实质性的看见女人的裸体,虽然只有上半身,但也足以在我的大脑里产生强烈的**。但由于道德标榜的正义的力量,我变得很无措地扭头要走。可很意外的被郭树青喊了下来,他告诉我们他女朋友今天要在这里睡一个晚上,让我们不要出去,还说习惯就好。我本想对他说这个我习惯不了,却被阿海抢了先,他恶狠狠地瞪着他,然后很克制的讲出了所有我想说的话。就算在今天看来,他说的都很正确,可当时郭树青根本不理会。他觉得只睡一个晚上没什么大不了,只是我们还不习惯,只要他坚持下去,一切还是会跟过去一样。他可真是很聪明,完全没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可我们又能拿他怎样?去向酒店反应,然后让他滚出宿舍?那太残忍,要知道他离开这里,可能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或者是将他狠狠的揍一顿,让他彻底明白我们的底线?这显然太野蛮,而且很有可能事后,我跟阿海都会去警察局蹲上几天。所以最后我们都妥协了,但前提只限今晚。
那晚过后,他的确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没再要求我们四人同睡一间宿舍。这个我真该好好的谢谢他,但说来也真是奇怪,他不带女朋友在宿舍过夜,而他自己也不再出现。我们当时都怀疑他在外面租了房间,后来才知道是他女朋友的一位老乡要生孩子就回家去了,但租的屋子里东西太多,而且日后还会再来这里,所以就请他女朋友代为看着。更重要的是,往后几个月的房租也都预付过了,他们只需要交一些水电费即可。对于郭树青来说,这可真是意外之喜,现在他终于不用那么麻烦的请我们出去了,那他这只野兽,就真的可以无法无天了!
对于我们来说,这又何尝不是意外之喜。但这种意外之喜多少有点缺憾,仿佛这个房间里突然间少了些什么,而缺少的这些是这里原本就有的。我当然知道缺少的那点是什么,但重要的不是将他找回来,而是努力去适应新环境。而且在努力的同时,我们都抱着一个期望,就是等待他回来,因为那是迟早的事情。
现在,我能深入交流的人只有阿海了,老实说,他确也是个很有故事的人。他的故事一半有些黑暗,一半有点滑稽。比如说这件:
此事发生在五年前,那时他与那位女孩子聊得很好,女孩子告诉他自己的家在浙江诸暨,家里经营着一家快餐店,但家里人手一直不够,而信得过的人又太少。所以她非常希望阿海能过来,她说他是自己最信任的人。那时他也真是年轻,居然一点都不怀疑对方,于是把房子退了,坐车往诸暨赶来。到了之后才知道是一窝传销骗子。这帮人非常无耻,他们先是给他洗脑,用一种很迂回的方法让他给亲人打电话,让他们寄钱过来。虽说当时还年轻,可阿海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经历,他没有上他们的当,在无数次劝说无果之后,他们的态度突变。他对我说,他们将他关在一个小屋里,不给他饭吃,等他睡着之时,就往他头上泼冷水,然后让人脱光他衣服,先是给他拍照,接着就是揍他。他不记得自己那段时间被揍了多少次,每次被打之后,他都会卷缩在墙角下恸哭。而且还不敢被人看见,因为被他们看见又是一顿毒打。后来他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将他放出来的,放出来之后给了他几百块钱,让他坐车回来。有趣的是,离别时他们居然还向阿海道了歉,说这是没办法的事,都是为了生活。阿海当时一定恨透了他们,可听到这样一说,也就只好长叹一息,拿着钱,闭上嘴,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