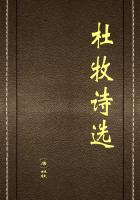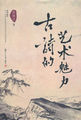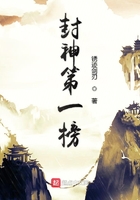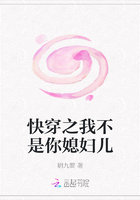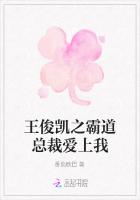当青春行将离去,总有些东西让你记忆犹新。在我短促的高中和大学期间,我饱受了偏头疼和肋部疼痛的侵扰,这让我痛苦不堪的同时,开始体验到想象中死亡来临的危险。在一次无可救药的疼痛之后,我在一首命名为《我看到了死亡的影子》的诗歌里写道,“疼痛在梦里如轻骑兵一样突然出袭”。我将我的头疼归因于无限制的阅读和思考,而肋部的疼痛则是渲染青春的一种色彩。在后来的阅读中我很容易就在其他的地方得到了验证。
诗人西川在文章《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中写道,“当我结束了我被偏头疼折磨的青春期”。西川将偏头疼用来修饰青春期,可见它带给他的痛苦和印象之深了,这使它成为他青春生命中的一道深深的印痕,并在记忆中轻易就浮出水面。西川在回忆好友海子时则将他的死因的一部分归结为海子临死前出现的“幻听”“幻觉”。幻听使他“总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搞得他无法写作”,幻觉则使他“觉得自己的肺全部烂掉了”。西川又将这种幻听和幻觉归因于海子的练气功,但我想这可能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他过度的阅读和写作。诗人骆一禾在谈到海子在短短五年间写下了200多首高水平的抒情诗和七部长诗后,将他这一点比拟为“亚瑟王传奇中最辉煌的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这个年轻人专为获取圣杯而骤现,唯他青春的手可拿下圣杯,圣杯在手便骤然死去,一生便告完成。”骆一禾用过分诗意的话评价了海子的一生,不知他有没有想到如此急促的写作会不会严重地损害海子的身体。西川谈到海子“一晚上可以写出几百行诗句”,而诗歌的写作除了需要技巧之外,更重要的是激情,是火,也就是一项极其耗费体力和精力的劳动。这相对于叶芝“一天只写六行诗句”或菲利普·拉金“一两年才写一首诗”,难道不是一种“自杀式写作”吗?所以我想海子可能不只是幻听,可能还有偏头疼,也不只是幻觉,可能他的肺真的已经烂掉了。那么为什么是肺呢?这呼吸的器官?
诗人陈东东在他的自传性文章《回顾,从1995年3月》中说得更加明白。他说,“从1995年3月末梢的一张病榻上回首往昔,我看到胃疾——作为我过去生活中一再出现的突出事件——提示我认清以诗歌写作为命运的来路”。在这里他完全将自己的疾病与诗歌的写作联系起来了。他带有总结意味地说,“似乎兴奋的写作总是找溃疡病出任拍档,而诗篇的诞生一定得付出血的代价。我不知道是否可以从胃疾及其象征入手去阅读、阐释和批评我写下的某些诗篇”。最后他说,“对我来说,它们有时候简直就是胃疾的一部分”。而我认为如果从象征入手的话,事实上胃疾应当是他诗篇写作的一部分。正是这在他的叙述中已经带上强烈宿命色彩的疾病,使他的写作留下了深深的青春烙印。无伦如何,在剩下的篇幅中陈东东便不厌其烦地将胃疾和诗歌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的这种认真甚至是偏执在我的印象中是很少见的。
在更多的人那里,我没有读到关于青春病的描写,但是我想,并非青春病事实上不存在,而是大部分人将其作为一种隐私,属于个人的秘密藏进了记忆深处,当年老的时候,便会随着对青春的怀念而面目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