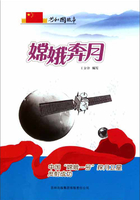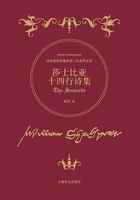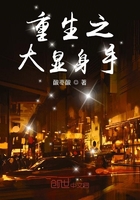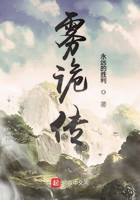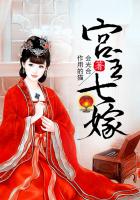一
都说电子书会取代纸质书,我总不肯相信。如果说读书只是为了获取知识,那么还有可能。实际上纸质书早就不再单独作为一种知识的载体存在了,特别是对于书痴们来讲,美丽的书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更何况因书还衍生出了不少更有趣的玩意儿,比如书签、藏书票、毛边本、签名本。真想不出如果有一天,真的只剩电子书了,怎么制作毛边本?作者签名售书时又签在哪里?签在阅读器上吗?想一想就觉得无趣。
更何况纸质书还能牵出一段又一段美好的书缘。
就以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为例。去年8月,上鼓浪屿玩,在晓风书屋买到一册古剑的《书缘人间——作家题赠本纪事》(山东画报社2010年9月出版),读后非常喜欢。古剑,本名辜健,祖籍泉州,193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十岁落籍厦门,1961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曾任华侨大学助教,1974年漂泊香港,历任《新报》《东方日报》《华侨日报》副刊编辑,《良友画报》《文学世纪》主编。因为写作及工作的关系,古剑与许多华文作家颇有交往,“作家人情半张纸”,因而也得到不少作家的签名赠书。作者此书正是以其收藏的大量作家题字赠本为引子,去写这些作家,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种种“书缘”,读来真是让人神往。
虽然我收藏的作家题赠本不多,但一直很感兴趣。在我看来,这样一本专门写作家题赠本的书,必须有作者的题赠,才称得上完整。但如何得到作者的题赠呢?要说现在得到作家的签名也并不困难,有些作家满天飞,到处签名售书。但那多是畅销书作家或著名作家,对于古剑这样既非畅销也不特别著名的作家来说,恐怕还是有点难度。查百度,意外得知古剑几年前曾来过厦门,可惜当时不知——知也无用,那时书还未出。因为古剑曾落籍厦门,与厦门颇有渊源,猜测以后古剑或许仍有机会来厦。朋友中南宋兄与各地作家交往较多,因而特意交代其如古剑来厦,告知一声,帮着索个签名。不料南宋兄出个“歪招”,说你何不写篇文章,放在博客上,或许能引起他的注意,说不定还能联系上。想想颇有道理,于是就写下了下面这篇文章,用的题目仍是《美好的书缘》。
二
如果嗜书是种病,那么,很明显我的病情加重了。病征之一是,看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书,总是忍不住会多买一本备藏。藏来做什么呢?不知道。只是有这种强烈的冲动。细思,其实也没什么用,两本一模一样的书,总不至于这本翻两天,那本读两页吧。如果说是怕一本翻烂了,找不到新的替代,则在我还从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读书是很爱惜书的,不说读完新若未触,至少除了扉页的签名以及内页的批注,不大会留下别的什么痕迹。如果说是怕朋友借去不还,早早备着,这种担心却也大可不必,虽然不是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但概率毕竟极低,因为现在朋友之间也是很少借书的。
想来想去,只能说是一种病。
最近犯病是因为一本古剑的《书缘人间》,书的副标题是“作家题赠本纪事”。在鼓浪屿晓风书店买了,过轮渡时就着黄昏的光看了几篇,很喜欢,回家又认真读了几篇,更喜欢,胸中于是充满了抑制不住的激动,人都要飘起来了,迫不及待地想上网再订购一本。
我知道又发病了,所以我忍。
忍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终于还是忍不住又买了一本。新书到手,满心的欢喜,但是一模一样的书,我又能拿它如何,只好委屈其暂时束之高阁,继续读先前买的那本。哦,对了,买两本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有备藏的书在,我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原来的书上乱批乱画了。然而批完,画完,反而感觉还是批画过的更亲切,也更喜欢,因为这本书不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刻上了我的痕迹,沾上了我的汗渍,变成了独特的,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一本书。而那本崭新的新书呢?它与书店里那些还没有卖出去的新书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连在上面盖个章写个名字我都不舍得呢!
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多想也在上面留点属于我独有的痕迹,让它也变成一本独有的书,但是至少截至目前,我还没有想出来要怎么办。所以只好继续委屈它寂寞地躺在书架上。
说起来,我其实是做了一件残忍的事。
回头说这本书,我之所以觉得这本书好,除了因为它是写书,写文人的交往,符合我的口味外,还因为作者古剑的文章写得确实好。如何一个好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不好说的。我曾推荐几本书给几个爱书的朋友,推荐时我热情洋溢,但他们却反应冷淡,读完之后说感觉也没有我说的那么好。我于是知道,读书本就是口味问题,好与坏,除了那些众口一词说好的,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呢?《追忆逝水年华》《百年孤独》这样的名著还多次被退过稿呢!
我觉得古剑的文章好,主要是觉得其语言简洁、节制,有一说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从不乱铺陈。有时我辈觉得大有文章可做之处,他也轻轻一笔带过,初觉可惜,回头细品,反觉余韵悠长,让人不能不服。比如他写董桥,文末说“董桥赠书给我,都题上数语,尤可玩赏,录一二供同好欣赏。”果然就录了两则,两则后立马收住,道“不录了,文人意趣尽在其中,多则无味,正如粤语所云:少食多滋味。”文章至此戛然而止。此语或正可印证我所言其语言的节制。
看来古剑追求的就是这种“少食多滋味”。他评聂华苓,看重的主要也是这一点。他评《三生三世》,“剪裁大刀阔斧,删繁就简,跳接留白,显得轻灵鲜活,不求完整,但求突出,落墨不多却人物生动。整部的文字简到不能再简,行文有诗的韵味,没有累赘的交代却处处明白。”他说的是聂华苓,我倒觉得这段话用在他身上也合适。
我是把他这本书当作写作的教材了。
回头再谈这本书的内容,陈子善在序里说得很明白,古剑写这本书可能是受了他写《签名本小考》的影响。以作家题赠本为引子写文人之间的交往,这是个多么好的角度。可惜这样的角度,并非人人可写。陈子善在序文就有区分“签名本”和“题赠本”的不同,题赠本“作者与受赠者之间大都有交往,非师即友”,该书共写到大陆、台湾、香港、海外96位名作家的题赠本,除了古剑,有多少人能做到跟这么多名作家有交往呢?这是让我等一般读书人遗憾的地方,也是让我等羡煞的地方。这自然跟作者编辑的职业有关,因而也让我羡慕起编辑这个职业来,以书结缘、以书续缘,对于读书人来讲,这是何等美好的事。
说是写了96位作家,写出来的却是97个人。这第97个就是作者。按陈子善序里的说法,这本《书缘人间》应是古剑在大陆出的第一本书,难怪以前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也从未看过他的书。
黄永玉因“古剑”这个笔名,给古剑画了一个古代剑客,题词“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听来甚为铿锵、慷慨。古剑是个文人,“手起剑落”这种事自然不会去做,但按其说法,心直,倒也不无侠客之气。心直有时难免会伤到人,比如他提到第一次去北京,拜访汪曾祺,临走时汪说我画张画给你,说着起身入房,古剑想也没想就说:“已画过给我了,谢谢。”说完就下楼。汪曾祺“不作声,回身送我下楼,一直送到大路边,看我上了车才回去。”多年后古剑暗自后悔,那句话或者伤了汪的好意。其实不止他后悔,我读到这里,也感觉黯然,为汪的“不作声,回身送我下楼”。
其实文字节制,要的就是收敛自己的感情,尽量做到平淡如水,处理得好,自有韵味,处理不好,或者感觉冷淡,或者会觉得乏味。古剑文字崇尚节制,是后天修炼,还是性格使然?
三
可惜文章放到博客上,久久未有动静,遂渐渐死了心,不再奢望。不料转眼到了去年6月26日,偶然在微博上结识长安吕浣溪,吕兄与古剑先生常有联系,遂从其处得到古剑先生的电子邮箱地址,当日即冒昧发上一信,表达热爱之意,并顺势向其索要签名。
不料当日即得到先生回信:
遂涛先生:
得你来信并读大文,很意外也很高兴。谢谢你。厦门是我少年生活读书的地方,留下美好的印象。此后漂泊至上海(读大学)、泉州(华大教书)、汕头(下农村)、香港、珠海。厦门好像回去过两次。想写些忆念厦门的小文,终于未写,那里的蚵仔煎、花生汤麦乳常在念中。厦门除了当官的舒婷外认识的很少了。想回去走走也没有熟人了。有,也没联系了。
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就是好文章。你的这篇就是情真。随笔就是要自然。
我的这本小书反应不错,在刊物、报纸、网上看到四五篇谈它的文章,都说喜欢。这是我没想到的。我只是游戏,却契合了一些爱书人的了口味,得其欣赏,纯属巧合。一个作者的书有人喜欢,有不认识的评说,总是高兴的。
你的书可快递寄来,我去邮局不便。
祝好
辜健
2012年6月26日
读后大喜,当即快递将书寄上。几日后即收到古剑先生题签后寄回的书。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契机,迅速实现我的梦想,心中十分的欢喜。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书写文累了,站起巡视书架时,我总会忍不住抽出先生题签过的那本《书缘人间》,打开扉页,是先生钢笔竖写遒劲的字体:
今我如金农所云:闭户读书忘岁月,人如流水少知音。忽遂涛兄从家乡寄书来索签名,一本小书得数不相识的知音评述,乐何如之。谢谢知音人!
古剑
2012年6月29日于珠海
签名下是“古剑”篆体阳文印,题签右上角还钤了一白兔肖形章,应是指其生肖为兔(1939年为己卯年),没想到古剑先生还有这样的童心。
因书而结缘,真是一件再美妙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