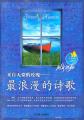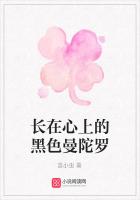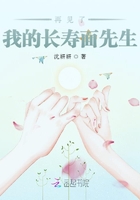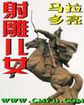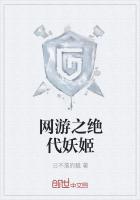淘书的乐子,这是多么平庸的一个题目呀,有多少书痴书虫乐此不疲地写过它。可是现在要享受这种乐趣也不容易了。首先,去哪里淘呢?淘不是买,新书是称不上淘的,哪个爱书人不是把新书店逛得比自己家还熟悉呢?哪本书在哪个位置,爱书人有时(应该说很多时候)比书店的店员还熟悉。书痴们逛书店,一眼就知道新来了什么书,哪本书卖掉了,哪本书被人换了个位置。因为逛得太勤,说句实在话,逛书店的乐趣都削弱了。我现在就痛苦地发觉,每次逛书店,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我也知道这未免太快了,但是天啊,我已经极其耐心地把所有的书都又重新浏览过一遍了,你还能要求我怎么样呢?
旧书店呢?对,旧书店用得上淘这个字,相比于新书店,旧书店像个神秘的海洋(可惜更多的时候像池塘),我们经常没办法一眼望到底。但是一个城市的旧书店实在少得太可怜了,而货源又那么的短缺,哪里经得起我们一淘再淘呢,淘了两次也就变成逛了。对于书痴们来说,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我说的淘,是指披沙沥金,满足的是一种发现的愉悦,如果能够幸而捡个“漏”,那就是更完美了。所以前年,我去上海、苏州、杭州,就只逛旧书店,新书店是一概不进的。
就像吃不到美味的人经常会怀念美味一样,我就经常会想起高中时代的淘书生活,那时校门口有一大片旧书摊,负手对冷摊,倒经常会有一些不错的收获。只可惜,那时不大懂书,买的多是大路货,现在稍微懂了,却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这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但是没想到,前几天竟然又有一次这样的饕餮大宴。那天是朋友请喝茶,请的都是爱书的虫子,茶过三巡,朋友突然神秘地说:“你们有没有兴趣到楼下看一下,楼下有些旧书,如果发现中意的……”
话还没说完,我们就像装了弹簧一样跳了起来:“怎么会没有兴趣?”朋友这才发现对形势估计有误——话说得过早了,她忙说:“急什么,喝会儿茶再去嘛。”“茶?茶随时都可以喝的,书嘛,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于是我们不顾主人的百般挽留,决绝地冲下了楼。
到了放书的那个房间,我们这几个爱书人不由惊叫一声:“天啊,是谁这么没有天良,竟然这样对待书!”只见一捆捆的书胡乱捆扎平摊在房间的地板上。因为刚搬的家,屋子空荡荡的,只有地上一大片摊开的书。可是连日的阴雨,已让屋子里潮得流水了,书们,简直就等于直接躺在水窝里了。容我用一个不那么贴切的比喻吧,我触目所见,简直就是一群如花似玉的美女(其实已经满面皱纹,但我毫不觉得)被人强捆着,委屈得直掉眼泪,可怜兮兮地,只等着我等怜香惜玉之辈赶快搭救呢!
我们二话不说,立刻弯下腰动起手来。这下你终于明白我说的淘书的真正含义了吧。这堆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海洋呀,我们就像一个打鱼人,能打到什么,简直完全要凭我们的运气。书都是旧书,50年代的、60年代的、70年代的、80年代的,台版的、港版的、陆版的,政治的、地理的、历史的、文学的、宗教的,五花八门,我觉得每一本都是好书呀,即便对内容没兴趣,光版本的价值就足以让人欣悦了。只是我哪里能表现得那么贪婪呢?我总要找我喜欢的吧。哦,这是一本科学出版社1956年11月1版1印的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封皮还是朴素的手写体呢,不错,收。那一册是什么?哦,原来是台版孟森的《清史》,书名还是胡适先生题签的呢,不错,收。等等,这里竟然有一本1985年1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董乐山翻译的《1984》,奥威尔的这本反专制的名著可是我的最爱,同样是董乐山翻译的我已经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了,但是远远没有这个版本年代这么久远呀。注意看看四周,还是不要让其他书虫知道为好,免得他们眼红,呵呵。嘿,那本小书是什么?那么雅致,哦,原来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月1版1印的何为的《小树与大地》,这是个福建老作家,读过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第二次考试》,他的书自然是一定要收的,读不读倒是其次。噢,《周佛海日记》,周佛海,不就是那个汪伪汉奸吗?书籍印刷的一般,算了,不要。“周佛海的日记谁要?”一激动我竟然举着大叫。有人接过去之后我才猛然想起,前不久刚刚读完苏青的《续结婚十年》,据说书里那个戚先生影射的就是周佛海,证据之一就在周佛海的日记里,可是我怎么就这么随便送人了呢?但是现在再后悔已来不及了,总不至于再要回来吧?算了,以后需要借回来看。继续埋头翻找,不错,又找到两本雅致的小书,版式比《小树和大地》还要小,看起来也更旧,但品相是好的。什么书?一边拿起来翻看,一边暗暗佩服着以前的出版社,真大气,这么薄的小书也肯出版。我是最喜欢这种小册子了,既雅致,读起来又舒服。打开一看,原来是臧克家的两本诗集,一本是作家出版社1962年7月1版1印的《凯旋》,一本是作家出版社1958年4月1版1印的《一颗新星》,啊,这书要是让喜欢臧克家的人看到,还不得眼红死?
感觉还没翻多少,手里就一大摞了,拿不动,放在一边。不敢直接放在地板上,怕湿掉了,就直接放在一堆书上,又怕和那堆书混了,想走开,又怕不小心被那群书痴重新挑走了。竟一时拿不定主意呆站在那里了。“你傻站着干什么呢?能挑只管挑,反正不挑也是当废纸卖掉,化成纸浆。”朋友只当我是不好意思,笑着鼓励。她是完全在看我们的笑话了。和她比较起来,我们是真正的一群破烂王了,她倒优雅得只肯站在旁边闲看。
经她一鼓励,我又一头扎进书堆里了。书铺得太开了,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用脚把书挪开,叉开腿弯腰站着,倒像南方水田里的农妇。站了一会儿,腰酸了,背疼了,衣服被汗水湿透了。直起身,用手背捶捶背,继续弯下腰捡。哦,这本是什么,《大众文艺》,没听说过,打开扉页,啊,1928年的杂志!第一期!郁达夫主编!上海现代书局发行!这一系列字眼一个一个地敲打着我脆弱的神经,简直要让我的心脏跳出来了。我强忍着极大的欢喜打开目录,第一篇竟赫然是鲁迅的翻译作品。“天啊,”我终于忍不住叫出来了,真有这样的好事吗?我竟然找到了一本民国杂志创刊号!我的惊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立刻感到被一束束羡慕的眼神包围了,连一直优雅地闲站着的朋友似乎也颇动了一下容。
“如果真是创刊号,可是能值不少钱的!”一直手也没怎么闲着的苇老师说。
“××知道一定后悔死了,让他来他不来。”朋友也说。
我感觉身子已飘起来了,我几乎按捺不住自己,但是毕竟脑子还清醒,强力又把自己拖回了地面。但是明显已经有点心不在焉,心神全被那本抱在怀里的《大众文艺》牵走了。但是很显然,幸运之神还没远离我。我又翻了几本,啊,这本又是什么?那么细薄的封面,“萧军”“十月十五日”“文化生活出版社”?难道是民国版的吗?赶快打开版权页,还真是,虽然不是“民国”二十六年六月的初版本,但毕竟也是“民国”三十七年八月的第三版呀。该书属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集,该集共16册,萧红的短篇小说集《牛车上》同属该集。可是我不免贪心地想,如果是萧红的《呼兰河传》该多好呀!正想着,又一个熟悉的封面映入眼帘,不用想就知道是王云五主编的“万有丛书”,打开一看果然是,不过是一本科学方面的书,周昌寿的《天体物理学》,属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12集简编500种,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十月初版,二十八年十二月简编发行,薄的可怜,但也是我想拥有的一套书中的一本呀。还有这本粗牛皮纸样封皮的是什么书,哦,原来是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六月第一版“耶稣传”(《人之子——一个先知的传》,卢特维喜原著,孙洵候重译)。
啊,一连串的惊喜已经把我打晕了,我觉得实在已经没有力气把身子伏在地面上了,看着手里又是厚厚的一摞书,我没有心思再继续淘下去。实在是太幸福了!这种幸福感让我眩晕,我实在没办法一下子消化掉这种持续的巨大的幸福感。还是不要让我一次中500万吧,中也要让我慢慢地中吧,我实在“害怕”了这种一下子降临得太多的快乐,它让我感觉不实在了起来。
但是,但是,我错了,我实在不应该太这样飘飘然呀,因为很快,良兄就在我刚才淘出《大众文艺》的地方也淘到两本创刊号民国杂志了,哎呀,很快他又在我淘到《十月十五日》的地方淘到一册1954年人民文学版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了,哎呀,在我张皇失措的时候他又趁热打铁淘到了一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的《胡安·鲁尔福中短篇小说集》。要知道,这本书当初一个朋友借给我时,我多次犹豫着都不想还他了,可是——
可是我仍然是高兴的,为的是我们都是高兴的。我们都是如此的丰收,以至于我们很快就决定晚上要大大地吃它一顿以示庆祝了。我们都争着要埋单,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埋单呀。但是我仍旧不免要批评某些同志的贪心,因为在我们几乎把那些书翻过三遍之后,还有人不舍得住手。在我们准备去庆祝的时候,他还在打他美丽的小算盘,盘算着如何把这一堆书当作废纸从朋友的单位收走。他的计划很好,书收走后,先让朋友们挑一遍,然后再拿到一个朋友的旧书店里去卖。
呵呵,如果你以为这次淘书之旅到此就为止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对于书虫们来说,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呢。我要怎么消化我的快乐呢?晚上酒足饭饱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丝毫不觉得困,我兴致勃勃地把书一本一本拿出来细细地翻过,分门别类上了架,我甚至还给他们编了书目。但是,天啊,快乐中总也有那么一丝不和谐音,我蓦然发现,我本以为是创刊号的那本《大众文艺》,原来只是一个影印本。我不顾时间已晚,急忙通报给良兄,不久,良兄回复,他那两本也是。
哎呀,空欢喜一场!可是在电话里我们是怎么安慰自己的呢?“不管怎么说,也是1961年的影印本呀,而且只影印了900部。印得又那么好,如果把印有影印说明的那一页撕掉的话,谁会知道它是一个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