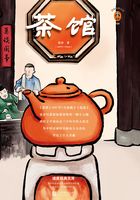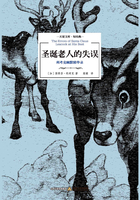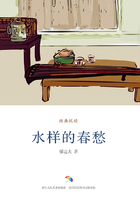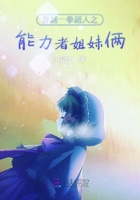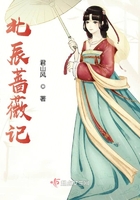多年前,读过达理的一篇小说,名字已经忘了,内容却还记得,讲的是卖书的事。记得看到最后,唏嘘不已。那时我还是学生,还没有几本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书,但是已经开始为身后事发愁了,最发愁的就是这书。相信有我这种心境的藏书家不在少数,历朝历代都有。藏书在中国,历来是一件极其庄重的事,其意义自不必讲,往小了说,怡养性情,往大了说,传承文化。因而在外在形式上也极其在意,有条件的,就建个藏书楼,没条件的,也要设个书房,实在连书房也没有,书架总要有一个两个吧。家里有几本书,就可以称得上是书香人家了。旧时,就连农村,门楣上也总要请人刻上“耕读传家”几个字,我小的时候还经常看到,可见此风之长。
现在藏书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事,但是一般的人,不管家里有没有书,装修房子时也总是要留一间当书房。书房最后往往变成了客房,书架也变成了杂志架,然而说明读书、藏书的遗风总还是有的。爱书人、藏书人买书、搜书时的乐趣自不必讲,现在坊间多有这方面的书,我最关心的还是这些藏书最后的命运。我总认为藏书的命运其实也是藏书者个人命运的一部分,是不能断然割裂的。可惜这方面的书不多,偶尔从一些零散的文章可见一些端倪,但总不能让人满足。所以,突然在书店见到马嘶这本《学人藏书聚散录》,不由一喜,随即毫不犹豫地就买下了。
马嘶所谓学人,多是民国以来的学者、文人,如胡适之流。学者而藏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自然不过了,如钱锤书者,虽学富五车而不藏书,毕竟是个别。藏书而变为学者,也是常有的事。两者可谓是相辅相成。看目录,马嘶关心的那些人,也大多都是我所关心的,如胡适、陈寅恪、钱穆、周越然、阿英等,自然更为兴奋。细数这些人,藏书最后的命运不外乎这么几类:一是生前就毁灭散尽,或毁于战火,或毁于“文革”,如周越然的言言斋藏书;二是生前捐赠,如巴金早在1981年就开始将他的三万多册藏书进行捐赠;三是死后遗赠,如唐弢和阿英这两位藏书大家的藏书即是死后由家人捐赠出来;四是死后散失,如著名学者赵萝蕤教授死后其藏书即被发现流失于潘家园地摊。
人云爱书人“借书是一痴,还书是一痴”,其实更深刻地讲应该是“聚书是一痴,散书又是一痴”。多少藏书人就是在不断地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中度过这漫漫一生的,聚散之间,多少藏书都已灰飞烟灭。有时,甚至让人弄不清楚,这些藏书人藏书究竟是对还是不对,比如郑振铎在他的《失书记》中痛心地记道,他多年来历尽艰苦积聚起来的珍本善本书,在“一·二八”和“八一三”战火中毁于一旦,仅毁于“八一三”战火的,古书就有80多箱,近2000种,一万数千册。相信很多书已随此战火彻底在这个世界上绝迹了。周越然的言言斋藏书也是如此,仅在“一·二八”战火中失去的中文书籍即达160余箱。更让人痛心的莫过于同样毁于两次战火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仅东方图书馆被烧毁的善本书即达五万余册。试想,如果这些书未被聚集在一起,或者并不至于完全毁灭吧?但是,即便它能逃过战火,它又如何躲得过“文革”这场浩劫呢?再说,怪也只能怪那场战争,那个无能的旧政府,又怎么能怪到藏书家头上呢?
读郑振铎《失书记》,感觉真是字字是血。然而藏书人的脾性就是如此,刚刚好了伤疤便忘了痛(其实这痛是永远忘不掉的),一有条件就又开始聚,在1958年郑振铎飞机失事时,他又是一位收藏丰富的藏书家了。1959年其遗藏被家人捐献给国家时,中外图书总数已达两万余种,九万余册了。
收藏丰富的藏书家,为了不至于让辛辛苦苦搜聚起来的藏书分散、散失,最后往往会选择将书捐赠给国家或某些藏书机构,以为如此,藏书就能有个好的归宿。然而,一片“痴心”最后收获的往往是“妄想”。李辉先生就曾著文谈到他在地摊上曾买到从图书馆流落出来的巴金藏书,而阿英捐赠给家乡安徽芜湖图书馆的藏书,据陈平原先生著文讲,至少在他去时还未分类上架,不知今日如何。
不过,此书仍有大遗憾存在,主要表现为资料还不够翔实,有些我真正关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答案。比如谈胡适,就仅谈了胡适流落在大陆的那102箱书,胡适后来在美国及台湾的藏书散书情况就未见提及。又如钱穆,也只写到1937年10月,钱穆踏上漂泊之途后五万册藏书的流失,至于以后,钱穆在海外几十年的聚书散书情况却不见告知。这难免让人感觉不满足。或者是资料缺乏的缘故吧,那么,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作者能有一本增补本出来,好满足一下我们这些饥渴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