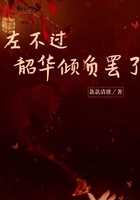凌晨,与一帮许久未见的朋友,在街角一家温暖的餐馆里吃着大排挡。那些腾升而起的热气将窗子渲染得朦胧无比,毫不知外面的世界。一位兴起的朋友站在窗下,一边看着我们大笑,一边写着“今日到此一聚”的字样。透过那些笔画,我们这才清楚地看见此时窗外,俨然已是鹅毛大雪。
端着温热的酒杯,我们丝毫没有察觉到铁门之外的寒冷世界。东一句西一句的调侃之后,终于杯盘狼籍。
当我们臃懒地躺在靠椅上,准备叫唤老板结帐时,一位瘦弱的中年妇女闯入了我们的视线。
褪色的天蓝头巾上,一些灰色的小毛疙瘩纵横交错,夹杂着那些尚未完全溶解的雪花。宽大的绿棉衣将她身体遮了大半,瘦削的脸上挂着些许水珠一类的物质。土黄的皮肤,谦卑而又不自然地微笑。她的打扮在此时这个嘈杂的场合里出现,多少有一些不合。本是嬉笑的我们,忽然沉默了下来。
看着此时横七竖八的我们,她站定了一会,有些紧张,像是在等待检阅。
朋友有些迷惑地问她:“你找谁啊?”
“要柑橘吗?一块钱全部给你们。”她提了提手中那几个用红色小网兜住的柑橘,干瘪而又安静的橙色。
若她不扬起手臂,我们或许都没有发现那提藏在宽大棉衣袖子里的柑橘。停顿了一会,我们互相有些不知所以然。
“放下两个吧,这一块钱你拿走。”最终,还是我开了口。面对她这样的装束,我忍不住同情心泛滥,觉得这样的冬雪天,这样的几个柑橘,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穷苦女人的全部依靠。我自然不忍心在交付一块钱之后,把她所有的依靠统统拿走。
对于我的善意,想她必是要表现得十分欣喜才对。可并没有如我所想,相反她显得更加紧张了,紧张里,多了一些东西在躲闪。
“全部放下,我们全都要了。”在那妇人轻微地放下两个柑橘,正欲转身离开时,我的一位朋友开了口。我知道当时的我们就算是最美味的山珍也难以下咽了,更何况几个柑橘?可朋友硬是要她把所有的柑橘放下,虽然有着满腹的不悦,在当时的场合,我也只能沉默着,看着那个精瘦的妇人尴尬地空手离开。
在回来的路上,我手里握着最后两个干瘪的柑橘,仍旧地难以释怀。
“我知道,你觉得我没有同情心,对不?”朋友在仅有我俩的情况下说出了这句话,我不作声,内心却在责备着他的明知故问。
朋友见我不说话,接着道:“假若我们真的同情她,同情这样的人,就该把我们的善意全部拿走。只有这样,他们才觉得那是一种彼此平等的尊重与交易。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就此离去,回家好好休息。倘若我们为了成全自己的善举,留几个柑橘给她,她必然又要在风雪中为那一块钱继续奔波。而那时,我们的善良究竟帮了她什么?”
话毕,我顿时恍然大悟。
贫富不等的世俗世界里,我们往往在用一颗自我认知为仁慈的心去完成每一次善举。无论大小,我们都尽可能的在给予他们关怀,却从来不知,对于这些真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们来说,完全是一种不经意的伤害。
将我们的善意全部带走,这是一种表面看似冷漠,却在内里温热无比的举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的让他们从社会底层的阴影里面脱离而出,认为这是一种彼此平等的交易,而并非一次对可怜和同情的刻意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