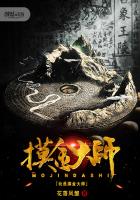“长平九年十月秋收后,恒山郡税得粟米十二万八千石,分别屯于嘉丰两仓,其中嘉仓仓曹掾私吞新粟两万六千石,丰仓仓曹掾私吞粟米一万九千石,贪墨仓粮近三分之一。次年春收稻米八万三千石,嘉仓仓曹掾私扣其中一万四千石,丰仓仓曹掾私扣九千五百石。”
“长平九年十一月,朝廷拨军备款一万两于恒山郡,用于制箭二十万支,其中二百五十两用于实际铸箭,剩下八千两调用为王府扩建,剩余一千七百五十两被库使挪用,至今未还。”
“长平九年十二月,王府扩建,将作掾以虫蠹之木代替承重横椽,以劣瓦充青刚瓦,从中贪墨库银一千两百两。”
“长平十年三月,灵寿县黄碧湖石坝年久失修,出现蚁洞,朝廷特拨款五万两重修石坝。公府水曹掾扣银四万两,其中三万两用于骁卫购马千匹,算是抵折了,剩下一万两中,与库使、将作掾一起,共贪墨银八千两。”
……
容珏越说,在场的几个老板面色越发难看起来。
还不等她说完,库使朱绍便第一个打断道,“公主说这些,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容珏笑道,“自然是想让诸位大人知道,在你们任期内曾发生的贪污纳秽之事啊。”
她话一出口,全部人脸上都没了血色,尤其是刚刚当上将作掾的刘顺昌与水曹掾的陈东升。
陈东升胆小惧怕,当下就直接跪了下来道,“公主啊,这贪墨修坝款项的是上一任的水曹掾啊,跟我没关系?”
容珏道,“在长平九年六月前的水曹掾早调任去赵郡了,你是说他在今年三月时特地从赵郡回来贪墨的这笔款项吗?”
陈东升梗直脖子道,“可我今日才买的官,上半年三月的事情,又跟我有什么关系!”
“任职书上可没有签署时间,只有任职时限。”容珏笑着自位子上走下,一掌拍在陈东升的肩头道,“陈大人,你难道不是去年六月就到任了吗?签字画押的东西,难不成还有假?”
陈东升呼吸一窒,口不择言道,“公主你这是故意给我们设套啊!”
容珏勾着嘴角俯视着他,“陈大人,你不会现在才反应过来吧?这反应该是有多慢啊。”
陈东升闻言身体一软,一屁股往后坐在了地上。
容珏拍了拍手,又回到了主位上,拿起册子道,“剩下还有不少。粮草督运官何大人,校人袁大人,接下来几条主要是跟你们有关的,想听听吗?”
何达、袁逢春忙也跪下,直喊冤枉。
这些人中,还是石康良第一个冷静下来,但他握拳的手也还是忍不住打着颤,“晋国开国初年,国库空虚,皇帝陛下借口诛伐叛乱,将国内十几个富贾商户抄家灭族,以充国库。”
他说着,朝着容珏抱拳道,“公主不愧为陛下的女儿,行事与陛下如出一澈,吾等只得认栽了。”
容珏闻言,眉锋一挑。
先前倒是不知道她父君竟然做过这样的事情,如今初一听到,有些吃惊。
在她心中,父君该是个温柔和善的人,打压商贾充实国库的事可以理解,但平白无故抄人的家,手段未免过激。
若是母皇为帝,必定不会这么做,最多提高商人的赋税,限制利润营收而已,而父君,不仅抄家甚至还灭族……
这么重的戾气,是受了奸党佞臣的谗言蛊惑?还是她的父君,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呢?
容珏压下情绪,笑道,“既然认栽了,那便领罚吧。”
石康良俯首跪拜道,“公主,在这之前,可否容我多说几句。”
“你讲。”
石康良道,“我石家在井陉关经营米店已有百余年,从我高祖父起就扎根在这里,一直兢兢业业,价格公道无欺,这才有了康良米铺现在的规模。这百年间遇过数次洪旱灾害,但祖上从未哄抬过一次粮价。”
“此次冀州水患,是我起了贪心,昧了良心,这才与其他几家米铺老板定下了这百钱一斗的底价,使得城中米粮不足……”
石康良停了一停,再开口时,声音已经颤抖着,昏黄老眼中热泪溢出,“但这都是我一人所为,与我儿无关。他平时只负责米粮的购买与运送,不知道我这离谱的定价,还望公主在抄灭我石家时能放我儿与我孙一条活路。我便是死了,也会在地下谢您的。”
“父亲!”石康良那三十来岁的儿子也跟着跪了下来,求道,“公主!粮价是我定的,与我父亲无关。他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将粮铺的事情都交给了我,这次抬价也是我的主意,他其实是后来才知道的。为了给我脱罪,才故意将事情都拦在自己身上。您要罚就罚我,绕了我父亲吧。”
石家父子这么一闹,其他几对父子也都跟风跪了下来。只不过朱绍的儿子年幼一些,虽跪了下来,却没有替父亲抗罪,只是一直哭喊着自己有多冤枉,好在朱绍爱子心切,倒也没有计较这些。
容珏被一堂十四张嘴闹得烦躁,扶了扶额,道,“安静。”
没人听她,依旧求饶的求饶,哭冤的哭冤。
容珏提了提声音,“安静!”
可声音还是被十四个男人的七嘴八舌所覆盖。
容珏不再多嘴,从位子上站起来,抽了腰间宝剑对着桌角就是一砍,手掌大小的桌角被直接削飞了出去,落在地上时还打了两个转。
大堂内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几个哭的最狠的,连抽噎都给咽了回去。
“知道安静了?”容珏笑道,将剑收回鞘中,眼角扫过桌角,心中非常满意。
上午练了那么久的刀还是有效果的,虽然之前总是差了点手感,可刚刚那一下,角度是真正的好。这要是砍人的话,刚刚削飞出去的就不是桌角,而是一颗脑袋了。
“罚哪些人,要怎么罚,是我定的,你们瞎闹腾什么?”容珏道,重新坐了回去,还故意恶意地反问了一句,“就真这么想被抄家灭族啊?”
吓得地上跪的十四个人连气都不敢出了。
“抄家是不会抄的,灭族也没有,不要太紧张。”容珏笑道。
“不过这罚是一定要罚的,各位回去后都把铺子里的账本给我收拾出来,冀州大水之后赚了多少黑心钱也全给我吐出来,这钱呐国家收了。”
“至于方才买官的粮食与银两,我就暂时不退了。军中正缺粮草,而且黄碧湖那里还得修石坝呢,钱粮都缺,就先征来用一下。利息你们就不要想了,没有的!等恒山郡十月秋收的税粮上来了,再把这笔粮食还给你们。银钱的话,一会儿出去前我给你们打白条,王府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
“放心,恒王就藩至少要到后年六月呢,这期间一定把钱给你们还上,要真拿不出来,我把我弟卖了也给你们凑上。”
众人哆嗦忙道不敢。
容珏却抬手往下一压。
这次大家很有眼力见的立刻噤声了。
“至于之后呢,你们开米铺的,也不能不让你们赚钱。但这米价嘛,每斗赚个一钱半钱的也就够了。我奉劝诸位一句,做人还是要多摸摸良心的,若真掉钱眼里了,就看不到悬在自己头上的刀了,懂吗?”
十四只鹌鹑齐齐点头。
“这不就好了吗?”容珏道。
“等井陉关之围解了,我还是会让人多注意这里的粮价的,若是发现有什么阳奉阴违的事情——就如你们所愿,抄家灭族怎么样?”
鹌鹑们整齐划一的发抖。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了!”除刘东升外的众人齐声应道。
刘东升转了转眼睛,小声问,“公主,那之前买官的任职书……”
话说了一半就被另外的人用眼刀飞的噤了声。
“怎么,还想着做官呢?”容珏笑道,“想做也可以啊,把水曹掾的亏空给我补上就行。”
“不不不不想了。”刘东升结巴道。
容珏最后看了众人一眼,说道,“对于商人,朝廷的确是有所打压,世人对你们也多看不起,但你们也要想想,寒门子弟苦读十年一朝中榜才能为士,农人辛苦耕作一年才得温饱,工人磨炼技艺数年才有吃饭的手艺。而商人呢,不过东买西卖,便能积攒财富,生活富足。得失相伴啊,就不该有所妄念。”
“若是真想入朝为官的话,我给你们两个建议。要么把铺子都卖了,换购土地,与农人一样耕田开地去,要么就去征兵处入伍,拿起刀剑保家卫国。卖官鬻爵这种事情,以后想都不要再想,晋国只要有我在,就绝没有可以用银钱换来的官爵!”
……
目送众人离开,胡广元原封不动地将之前的那几张“任职书”又拿回了大堂。
容珏侧着头,目光落在案桌的恒王印上,听见脚步声,便直接道,“桌角被我削断了,不知要赔镇将府多少钱。”
“让人拿钉子钉一下,再上个漆就行了,还能用。木匠费用大概要个三十钱。”胡广元道。
容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成,老胡你记个账,倒时候从我俸银里扣吧。”
“好,”胡广元道,然后看了看那两张还在桌案上的纸,问道,“没有上钩吗?”
容珏摇了摇头,笑道,“这鱼啊狡猾得很。”
桌案上是“南门校尉”“西门偏将”的两张官职任职书。
胡广元将手里其中一张任职书拿了出来,问道,“这张要记入编制吗?”
容珏看了一眼,正是萧记米店老板萧范之前百两买下的圉师一职。
“先不用了。”容珏道,“但是和军营看马的士兵说一声,若是萧范要去看马的话,就当他是圉师处理。”
“好,”胡广元道,“对了,萧范的情况下午时打听了点出来。”
容珏抬眸:“哦?说说。”
“萧范原是博陵郡的米商,九年前来的晋国,一直在井陉关做米粮生意,与人关系也一直不错。来晋国前没成婚,来后娶了个妻子,只是两人没孩子。”
“燕国来的,娶妻却无子啊。”容珏道。
博陵郡属于燕国,与恒山郡相邻。
胡广元看她一眼,问道,“公主,你觉得他像是燕国的细作吗?”
容珏笑道,“像细作,但不像是燕国的细作。”
“为什么?”
“一是他姓萧,肖萧同音,太刻意了,二是他没有买南门与北门的将领之职。”
“虽说一个商人在战乱之际拍下守城将领之职会非常引人怀疑,但若真是燕人细作,便是冒着这被人怀疑的风险,也是会要试试的,毕竟若城门能自里打开,能省下攻城的不少兵力与时间,而这对燕国细作来说,诱惑太大了。”
“那他是魏国人?”胡广元问道。
“不知道。”容珏摇头道,“也有可能是晋人。不然又怎么会买圉师呢?”
圉师是掌马的官,王府蠹吏这么多,这是唯一一个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就被挖出来的蛀虫,这还得多亏宋君先缴了恒王一千匹河曲马。
而萧范,他别的不买,单单就买了圉师。让人不得不怀疑,到底是巧合呢?还是他知道点什么。
“得空我再去探探他吧。”容珏道。
“公主……公主不好了!”
正这时,林芷儿一边叫着一边跑进院子里,她喘着粗气说道,“燕,燕军……入盆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