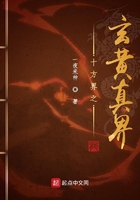那人穿了一件脏兮兮的破衬衫,皮肤黝黑,虎背猿臂,但只有一条胳膊,那只手拿着砖卡子每次抓六块砖头,准准地扔在独轮车上且码得十分整齐,比两只手的人干得还快。
他不敢相信,揉了揉眼睛再看。正好推车装满,那人从砖垛上下来,用独臂把一条拴在推车左侧握把上的绳圈套在脖子上,而后握住另一个握把,歪脖维持平衡飞快地推车就走。
半天儿看清那人的脸,惊叫一声,“栓子!”飞奔过去将车拦住。
栓子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放下推车一把抱住半天儿,“师父你可来了!我想死你了!”
半天儿摸摸栓子身边空荡荡的袖管,鼻子一酸,“兄弟,哥让你受苦了。”
栓子吸吸鼻子,憨厚一笑,“这不赖你,当初是我一心要跟着你的。我妈都说了,我能活着全靠你出的钱。你等我一会儿,我把这车砖推过去就下班了。晚上咱俩找个小店儿整点儿。”说着,他再套上绳子,跑向一个在建的庞大地基。
看着他的背影,半天儿心中百般自责。当初正是刘栓子用手堵住狗皮帽子的枪口才救了他一命,如今他完好无损,栓子却永远失去了左臂。
苍山吞日,古旧的小镇暮色四合。管事的敲铃,工友们欢呼着下工。栓子蹦蹦跶跶地跑回来,搂着半天儿走向工棚。半天儿忽然明白过来,吃惊地问:“是你让赊刀人给我捎的信儿?”
“没有啊,不是你让赊刀人送信喊我来的吗?”栓子也发愣。
“赊刀人也给你送信了?”半天儿更加吃惊。
“啊,是你让送的不啊?”
“不是,”半天儿皱起眉头,一脸狐疑,“这么说是有人故意让咱俩在这碰面?你来多长时间了?”
“一个多月了,那前儿工地刚开工。”
“这一个月里有人找你吗?”
“哪有啊,我就一心朴实等你来呢。你还说不是你。”
“奇怪。你那字条上写的啥?”
“我揣着呢!”栓子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半天儿打开,见上面是同样的笔迹,内容也差不多,唯一第一句地点不同,这张字条上写的是:咸州古城。他随手点燃一支烟,顺便把纸条烧成灰丢掉,叮嘱道:“以后赊刀人的密信看完就要销毁,这是江湖大忌。”
“记住了,”栓子重重点头,“你看出啥来了吗?”
“怪事儿,他应该就在这,为啥不现身呢?”
“谁在这儿?”栓子挠脑袋,明显跟不上半天儿的思路。
“你是到了之后没见着人才进这个工地干活的吧?”
“对呀,我得吃饭呐。”
“这就对了。我的字条上写的是开原县老城工地,你这写的咸州古城。这证明写信人是先让赊刀人找的你,他见你在这安顿下来,才又给我送的信。所以,他肯定就在一个能看着你的地方。”
“师父你这整的我直害怕。”栓子下意识靠近半天儿,眼睛贼溜溜地扫向周围的暗影,似在寻找谁在暗中盯着他。
“甭怕,”半天儿拍拍他肩膀以示安慰,“据我了解,赊刀人行规森严,不接外行人的买卖。江湖上能用这种方式跟我通信的,只有老刘。”
“你那带头大哥?”栓子放松一些。
“见着老刘你得叫师伯,他这人最注重辈分。你要敢说带头大哥,他能踢死你。”
“我叫师爷都行。关键他为啥不出来啊?”
“可能是觉得还不是时候。”半天儿想起最近几年老刘的遭遇,满心惆怅,“老刘这两年不知道惹上什么麻烦,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
“那咱俩现在咋整?”
“既来之则安之,如果真是老刘,迟早会现身,信上不是说约咱寻龙窖吗?指不定这老小子憋着干大买卖呢。”
“那可太好了!”栓子双眼放光,一秒沉入对江湖事业的憧憬。忽地,他又一脸疑问,“哎不对呀师父,他给你送信正常,你俩这么多年交情。可他不应该认识我啊!”
“老刘手眼通天,想知道我身边有你这么个徒弟太容易了。江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那行吧,”栓子有一种得到领导赏识的满足感,“反正找着你我就知足了,你说咋办就咋办。”说着,他跑进工棚,“你等我啊师父,今儿晚上我请。”
“龙窖,老刘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半天儿喃喃自语着走向大门口,语气中的担忧多于疑惑。
等栓子洗漱完毕,二人出工地来到主街上。栓子介绍说这个古镇的人口基本上都迁到城里去了,留下的要么是老弱病残要么是实在不想走的,现在也就剩下千八百人。但政府正在规划一个古城开发的旅游项目,将来这地方肯定能繁华。他劝半天要是有钱就在这买几座民宅,将来肯定能升值。
看着栓子仍然乐观似并没受到断臂影响,并且有了一定生活头脑,半天心中释然一些。可他实在没好意思告诉栓子,他现在兜儿比脸都干净。
俩人来到一家狗肉馆,点一盆狗肉汤,又要了一盘拌狗肉就地开喝。他们先是唠一些分别之后的事儿,半天儿打听栓子父母可好,栓子问到师娘白灵,半天儿满心感慨。接着半天儿问栓子将来有什么打算,栓子说师父干啥他就干啥。
七瓶啤酒下肚,栓子云山雾罩。半天儿喝了同样杯数的白酒,仍脸不红舌头不硬。他问栓子这个工地是干啥的怎么这么老大。栓子回答他说这是古城开发项目的排头兵——东北最大的满族文化展览馆,准备仿太和殿建,预算一个多亿。
两人由此聊到工地上的生活。栓子煞有其事地讲了一件怪事:
工地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开工的,前期主要运输工程设备,做一些地面清理工作,等设备运完开始焊接安全围墙。围墙下面是水泥基础,上面立彩钢板,事儿就出现在彩钢板合围的时候。
那天晚上焊完,工头请工友们每人两瓶啤酒,说这围墙把大伙儿围起来就是一家人,让干活的时候互相照顾着点儿。大伙儿知道就快开始挣钱了,也没吝啬,打平伙买了更多的酒水食物喝得大醉。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工地西南角对着古塔那地方的几块钢板莫名其妙地倒了。
一开始大家也没在意,重新焊好就完了。可过一宿又倒了。工头责怪焊工,派另一个焊工去,那人怕挨骂用两道钢筋加固寻思万无一失,可天亮前儿又倒了。这时候有力工说围墙基础挖到那段时抠出来两罐骨灰,建议工头给烧点纸安慰安慰。结果工头纸也烧了,还摆了供桌供上水果。围墙还是倒。反正就是焊上就倒。
后来有胆儿大的不信邪,合计几个人晚上在那守着看看这玩意儿到底是咋倒的。谁成想那仨小子半夜莫名其妙全睡着了,等第二天起来仨人个个嘴歪眼斜。墙还是倒了。
工头没招儿,亲自到那守了一夜,结果他也睡着了。他醒来后看着彩钢板倒在地上,赶紧派人请了个道士。那道士做法,说那几罐骨灰是日俄战争时候埋在那的俄国军官,因为埋骨他乡化成厉鬼,把那围墙当城墙了,每天晚上用炮轰啊。大师开坛做法,用桃木剑朝围墙劈了三劈,自那以后墙还真就没倒过。
栓子讲完,人精神了一些,盯着半天儿问:“师父,你说邪不邪?”
半天儿听着只管“咯咯”笑,不说话。栓子叹了口气,“我知道你没看着不咋信,我可是亲眼看着的。我试了,就我这力气推一把,钢板都不带扇乎的,你说要不是小鬼儿的炮咋能整倒?”
半天儿还是笑。栓子又灌半杯,“但咋说我也是跟师父你吃过见过的,这点事儿倒不至于让我害怕。可我眼馋呐,那道士鼓捣一会儿就拿走两万块钱,我哭死殆命干四个月才能挣那些钱。”
“那阵儿我是没在,”半天儿忽然也有点眼馋,“我要是在,那两万块钱就是我的。”
栓子一拍桌子,“可不是咋的!师父你就没把你那些手艺都教我。要是教给我,我何必拿脖子拉车挣血汗钱呢?”
“唉……哥对不住你。”
“不是,不是。”栓子自知失言,赶忙辩解,“不是这个意思,我都习惯一个胳膊了,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儿。我原来劲儿就够大的了吧?缺一个胳膊之后劲儿不但没小,反倒更大了。”
“你丫真的假的?”半天儿脸上写满不信。
“你看你还不信。你瞅着。”栓子说着把右臂伸到桌子下面,手掌张开撑住桌面,稍加用力,沉重的柳木桌子和桌面上酒食以及十几个空酒瓶子被轻松举起,又被稳当放下。
“我去……”半天儿瞪大眼睛,一脸惊奇。
“这肯定不能有假呀,我要是没这把力气,哪个工地能要一个残疾?不说这个了,那邪乎事儿还没完呢。刚才不是说道士做法稳住了围墙吗?最近又来邪乎事儿了。就俺们睡觉那工棚子,不知道为啥半夜老听着怪声儿,有时候有脚步,有时候挠铁皮,‘咔咔’的,老吓人了。头几天又有不信邪的晚上守着,结果也不知道看着啥了,吓得人事不省,现在还搁医院躺着说胡话呢。工头又去找那个老道,老道说这片儿工地是清朝时候的刑场,工棚的位置是被扒了的鬼王庙,晚上小鬼把俺们的棚顶当棺材给抬起来了。但这回你猜咋的?他做法没灵!到现在那声儿还有呢,那边儿都不敢住人。”
“这么着吧,栓子。”半天儿怅然一笑,“既然这地方这么信这个,你以后就别在工地干了,咱哥俩装扮装扮给人算去。一来能挣点快钱儿,二来说不定还能打听到点儿老刘的消息。”
“哎妈呀,”栓子一拍大腿,“那可太好了师父。咱俩半年干一单这样的买卖就够吃够喝了。”
未来有了着落,栓子彻底敞开心扉,又喝下三四瓶啤酒,人彻底醉了。临走时,他搂着半天嚎啕大哭,“师父,我胳膊没了,胳膊没了,我他妈现在是个残疾!走到哪别人都用眼神儿看我。以后你别撇下我不管了,就是要饭我也跟你一起要……”
半天儿紧紧攥着拳头,心里暗暗发愿要多挣些钱给栓子弄个像样的假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