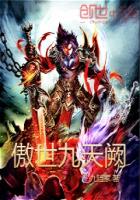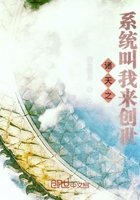一抹潮红在天边升起,黑暗在浩渺的大地上渐渐褪去,在这浩渺大地上沧海一粟的一个地方,一群怀揣梦想,激动兴奋得彻夜难眠的年轻人们聚拢在一个小小的广场上,期待着不同于父辈的人生。
“尽管看过很多届了,可每次看到那些孩子们充斥着兴奋、好奇、激动的眼睛,我感觉自己也是热血沸腾啊。”头发花白的县令在远处观望着那些手足无措的年轻人只感觉自己已经年迈的身体又短暂的充满了勃勃朝气,这种场合下怎么能少了教育司丞,“是啊,这说明咱俩这两把老骨头都是人老心不老啊,只是”老县令立刻扭头看向教育司丞,说实在的他很害怕这位老朋友说话转折,因为他主管教育只要有不好的消息那事肯定小不了。司丞犹豫了一下本来他不想在老朋友高兴的时候报忧的,可是如果不再他高兴的时候说难道还要等他情绪低落的时候说吗?那不就成雪上加霜了吗?他决定还是把最新的情况给县令汇报一下,“咱们县去年进入第二阶段的考生又全军覆没了,没有一个晋级到今年的最终阶段。”老县令一声长叹,又是这个结果,算起来安西县已经有二十年没有人能到省城参加最终选拔了,自己都忘了上次过好年会是什么滋味了。“放心,今年的年会我还跟你一起去,有啥难听的话咱俩一块受着,再忍忍吧,根据历史规律来算就这两三届咱们县肯定能出现新的修炼者,而且昨天咱们这可是刚来了一位麒麟儿啊!”“希望那位新的修炼者别应在这位麒麟儿上,毕竟他只是来这应考而已,跟安西县没有关联的。”
一群士兵小心翼翼的把一面被红布盖住的屏风搬到广场中央,少部分考生本就激动难耐的考生们只觉得心脏就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而大部分考生都按捺下心中的激动,准备以最佳状态迎接考核。领队的士兵长官核对了时间,确定无误后,和朋友一起抖手扯下了屏风上的红布,然后一言不发直接退下。
“开玩笑吧!这就是老爸说的超困难的修炼者选拔考试?我怎么觉得好简单啊。”“连监考官都没有,这是试探我们吧?”等众人看清楚屏风上的问字后,几乎所有考生都怀疑屏风上的信息只是个障眼法,真正的考核不可能像屏风上写的这么简单,只是其中一大半虽然怀疑,但眼见有人老老实实的按照屏风上的要求原地静坐下来后,稍加思虑也跟风坐了下来。剩余的一小部分考生眼见大部分人都按照要求做了,虽然心里仍然抱有怀疑,但抒发了几句牢骚后还是跟着静坐了下来。唯有一两个犟脾气的考生还梗着脖子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他们的认知里修炼者是最厉害的职业,想要成为一位修炼者肯定要经受最残酷的磨练,怎么可能如此简单呢?而且天这么热坐地上屁股的多难受啊?结果一盏茶后,大部分的怀疑者非常庆幸自己没做错选择。
“我不服!我不服!”被士兵们强制带走的两个犟牛,一开始还以为这只是士兵们吓唬吓唬他们的手段而已,谁知道这两位士兵直接把自己的行李打包了,连同他们两个送到了考场外的淘汰考生暂住点。心怀壮志来参加考核,这才刚开始就被不明不白的刷下来,无论如何都要问个明白啊!可是以他们的小身板怎么可能冲击看守考场的魁梧士兵呢?只能在淘汰考生暂住点大声抗议,这种孩子工作人员见多了直接发出了灵魂三问——你小时候学走路是不是先从爬开始?你父母教你认字是不是从最简单的一开始?为什么你现在觉得可以不从最简单的开始?把这两头犟牛说的服服帖帖的,耷拉着脑袋思考自己以后的出路。
而在铁西广场中,大部分考生在看到那两头犟牛的下场后都老实的按照屏风上的要求安静的静坐下来,只是相比屁股下的燥热他们心中更加迷惑,难道第一阶段的考核就是简简单单的每天静坐十个小时就可以了吗?这样真的可以成为修炼者吗?众多的疑问在这些稚嫩的心海间冒着滚滚气泡,把那原本清澈平静的海面搅得波澜不绝。
他们需要有人答疑解惑,可一上午过去了,没有人来给他们说明理由,中午吃饭的时候打饭的大师傅只管分发食物,对他们的任何疑问抱怨一概不予理睬。他们只能抱着满腹疑问继续返回考场应试,下午又是难熬的半天,头顶着大太阳,盘坐在滚烫的地面上,既没有水、也没有扇子、更不能说话不能上厕所。汗水从毛孔中钻出来把他们的衣服打的透湿,透湿的衣服黏在身上让人觉得更加难受,更多的汗水沁出,让衣服变的更加潮湿。有些人受不了了,倒在一边人被士兵们送去了医护室,行李被送去了淘汰生暂住点;看到一个个搬着行李从广场边走过的士兵,有些人只觉得气郁填胸为此向守在一旁的士兵们发出抗议,结果他们就再也没回来;还有的人受不了委屈,低声哭泣结果和抗议的人一起坐在淘汰考生暂住点等待长辈来接自己回去。剩下的人顿时没有了一丝多余的想法,他们只能把委屈和痛苦吞到肚子里无声的忍耐,等待夜幕的降临。
终于到了晚饭时间,被暴晒了一天的孩子们围着水桶贪婪的喝下一杯又一杯冰凉得井水,大师傅们在一旁冷冷观望,并不出声提醒只是暗中提醒医务室的医生们把治疗腹痛的药准备得足足的。灌了一肚子凉水的考生们扶着肚子颤巍巍的挪回宿舍,只是眼前的宿舍和昨日大不一样,很多床位都被清空了,原本就很宽敞的宿舍此刻显得有些空旷,很多人在这里匆匆经过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看着空荡荡的宿舍,原本就一肚子委屈和凉水的考生们大都悲从中来,伤心不已,那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哭泣的孩子和在厕所宿舍不断往返的孩子占了剩余考生的绝大多数。
第二天是第一天的重复,只是走的人少了些,第三天、第四天……,日历被一页页翻过,留下来的人是越来越少,尽管大家当初都是怀着梦想为了改变自己而来,可成长的痛苦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每天都有因为各种原因坚持不下来的人离开。生活区被不断缩小,像老罗叔这样负责接送的长辈们几天就要往返一次县城,给留下来的人送来补给,给各个村里的学堂送去新的学生。每有一辆接送孩子的车从铁西广场出发驶过县城的街道,都会勾起一片唏嘘声,不知道多少的豪情壮志在这里被屡屡证明只是年少无知。
夜幕下的铁西广场已经变成了白皑皑的雪地,打着旋的雪花乘着清冷的月光洒在了那本应洁白无暇的雪地上,把被一行脚印打扰的肃冷修复一新。缩小了十倍有余的生活区早已被统一安置在广场一角,而此刻远在广场另一角,却有一个孤单的身影在雪夜下漫无目的的游荡。
王刚披着前几天老罗叔刚送来的棉大衣,在广场上一圈一圈的压着马路,汗水打湿了他的额头,呼吸变得急促可他好像感不到疲劳仍然不停走着。这样的夜晚本来应该待在暖和的帐篷里,喝着热热的饮料,就着灯光看连环画为明天养精蓄锐才对,可自己为什么要毫无目的在外面游荡呢?他想不明白,就是想做点什么,让自己不要停下来,好像一停下来就会被什么东西抓住他。
在雪地里行走本就耗费体力,再加上寒冷的西风,更是消耗巨大,一个小孩子的体力能有多少?额头沁出的汗水被蒸成一层层热气,而一层层热气又被西风吹走,疲劳终究是抓住了他,他双手扶着膝盖大口的喘息着,喉咙里有一股血腥味不停向上涌来眼前发黑,似乎被谁掐住了喉咙就要窒息而死了,可他的毛孔却是拼命地呼吸着寒冷的空气维持那一点点的生命之火,过了很久很久那被扼住的喉咙才被放开了,他仰着头贪婪的大口大口呼吸着寒冷的空气。看着天空中的月亮,他没来由的抬起扶在腰间的右手把掌心对着那轮皎洁的月亮,双眼直直的看着那穿上月光的手掌,那里不久前刚被什么东西握住过,但是要比月光暖和多了,而且把曾经最重要的东西托付给了他,可最终还是离开了他。良久之后,他才收回了空空的手掌,擦掉了眼角的一滴泪水,一声轻叹,径直转身往生活区走去。
而在远处一直用望远镜密切观察着他的两位哨兵,看他已经往生活区走去,且步伐稳重,没有生病的迹象就把注意力收了回来,继续寻找可能存在的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