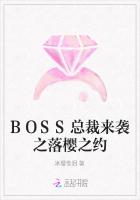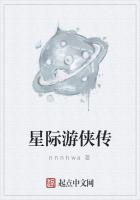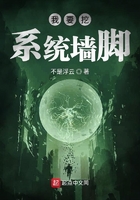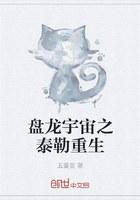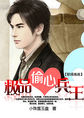在我看来这已成了个不争的事实:每每我俩出现交流障碍、关系瘫痪,这关系也在立时恢复原状,反之亦然,就好像崩坏与重建真的可以融为一体,完美地共存于同一个瞬间。
就这样,正当我们侃着这个、聊着那个,事实上,我们在探讨着哲理抑或希望探讨着哲理——这可能也是当代艺术最核心的活动——卡塞尔夜幕渐落,万物湮灭,缓慢得如同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周二。
乍然,她流露出跳脱的企图,出其不意地为步行唱起又一轮的赞歌,同时推荐我去看看某个声音装置,据称离那儿不远,实际又得走上好一阵子:它位于旧火车总站十号站台尽头。
大战时,她说,那站台主要是用来驱逐犹太人的,而今,苏格兰人苏珊·菲利普斯在那儿安设了她的声音装置“弦乐练习曲”(Study for Strings)。
我婉拒了这一新的提议,称,她还有工作,我不想再麻烦她了,此外,我也得回酒店了,正如早先所说,我开始没力气了。我总觉之前她是没听到,便一再重申了回到黑森兰德客房、尽早搭起我的草堂的迫切需求:都这个点了,我必须掐断任何可能让世俗生活延续下去的苗头。
很自然地,我没跟她说,但我尤其害怕,尤其忌惮她见到我每逢此时便习惯性挂上的惨白脸色;我知道,再过几分钟,我的脸就会阴沉下来,我的性格将变得十分易怒,一切都会难办许多,而这次,我没有科利亚多博士的药片可以救我。
我边向她传达着我的坚持,边想起了罗伯特·瓦尔泽的《散步》。在拖泥带水地描述了一通某位散步者幸福的日间闲游后——整本书里,此人一直在走——我们来到了如树阴般圆满的末页、揭示着主人公心情变换的结语:“我起身准备回家,因为天色已晚,四周一片黑暗。”
瓦尔泽的这个小小颤音打破了整本书的游戏规则,愉快的游荡戛然而止。街道变得漆黑一团。如果说至此那位散步者都感觉十分惬意,无与伦比地快活,沉醉于一路所见的任何风景,转眼他告诉我们,天黑了,一切都变了,连这本书也到达了它的终点,因为主人公想要躲回他的巢里了。
少时之后,我仍在向波士顿述说我的健康问题;就像强行要在我的话后接个“天色已晚”似的,她陡然打断了我,称,要思考大崩溃,“弦乐练习曲”就是最好的地方,没有之一。她道出这话的方式是如此斩钉截铁,我好似陷入了我性情里最绵软的那潭沼地之中,仿佛我爷爷的那两磅稀泥糊在了我的鞋底。我当下就困惑起来:波士顿是否在挽留我,或者只是有意坚持步行,好让我来说不,这样她就不会落下个“不愿陪我”的口实。
我很快发觉,事情正往一个迥然相异的方向推演着,恐怕比我料想的更为阴暗,或许比我预期的更为复杂。我绝对,务必,要去那个站台看看,波士顿又一次亮出了先前惊魂一刻瞪我的那种愤怒眼神。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有谁如此着急忙慌地催我去火车站的。我怯怯地问道,为什么一定得去那儿呢。太阳就快完全落山了,卡塞尔的天空中,云朵逐渐被染成了猩红色。因为我想,波士顿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吐出了她的话语,再走一会儿,我喜欢走路;因为这会儿你也该意识到,你所在的不是个地中海国家,而是个保有着深切悲痛的国度;因为你竟不知道雅利安人的香水瓶与先锋艺术间的关系。她终于道破了对我怒火中烧的原因。
那必定就是我一天中最大的失误:不相信布劳恩的香水也能和先锋艺术产生联系。但这样的话,一个新问题又来了:真有先锋艺术吗?世界各地都有人在谈论一种领先于时代的艺术,可对我来说,它的存在并不清晰。“先锋”一词的含义似乎已经和上世纪初不同了……然而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于紧接着的艰难行走中,我得知,卡塞尔的战后大重建要到1955年才正式开始,当时的市民极有勇气地拣选了一条比他们同胞的决定显得没把握得多的路,在工业发展与文化复兴之间选择了后者,又请建筑师兼教授阿尔诺德·博德负责策划首届文献展。它有着鲜明的修复性:德国在希特勒独裁时期曾将当代艺术定义为“堕落”,并将它的实践者们屠杀驱逐,而如今的它要以一次大展向二三十年代的艺术献礼,用博德的话讲,“它终于让艺术贴近了工人”。
终抵旧火车站的我们缓步朝十号站台尽头走去。到了那儿我才明白——几乎是顿悟——为什么那个声音装置,“弦乐练习曲”,要比任何一处更适合追忆那段纳粹当权的岁月、被波士顿称为大崩溃的时光。
尽管全世界都知道,现时所谓的先锋艺术,大抵都得由一部分视觉元素,以及为了完善前者、解释前者而生的文字组成,但奇怪的是,在“弦乐练习曲”中完全见不到此类情况。苏珊·菲利普斯的这个装置,只需来到十号站台终点便能立刻会意,不再需要任何一本小册子来完成她的叙述。
“弦乐练习曲”是件毫不花哨的作品,直接挖掘着一个人道主义乌托邦终结时的莫大的悲剧。通过设置在卡塞尔火车总站限定区域内的高音喇叭,菲利普斯做到了让所有行至该站台末端的人——战争中,大批犹太家庭就是在这儿等待着将要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的列车——都能收听到那段美妙却又万般悲戚的旋律、死难者的灵歌:“弦乐练习曲”。2012年,卡塞尔文献展播送着它,作为对大屠杀的纪念,因为它的作者,被放逐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捷克音乐家帕维尔·哈斯,正是为集中营的毒气室谱写的这段乐曲;此后不久,他被转移到奥斯威辛,并死在了那里。
我们是站着听的,脸上挂着与所有在场者一样凝重的表情,同时看到,不断有其他听众加入到这场不足半小时的铁道音乐会中;另有内容相同的诸多场次,以短暂的间歇分隔,每天在这悲伤的站台上陆续演出。最终,约有三十人怀着一样的感动听完了这段大小提琴的合奏,曲罢,尽都定在原地,若有所思,不发一语,深受震撼,像是正从所听所忆,所想所演,甚至可以说,所亲身经历的崩溃中慢慢恢复;在那儿,人不难感到脆弱悲戚,有如一名流离失所的被逐者。
那一刻我很想向波士顿坦言,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自己竟没发现,从一开始,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人道主义世界的永恒幻梦,就与艺术探索以及最前沿的艺术密不可分。但我只字未提,因为我打心里还在记恨她;都这个点了我还想不明白,我只不过问了句纳粹香水和先锋艺术,她就可以这么惩罚我,对,惩罚我,逼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行走,或许还一本正经地盘算着,到了某站台的终点,我就能诚心悔改,变得不那么欠考虑。
我很想对她说:我怎么能那么白痴呢!或者反过来指责她,她竟用如此微妙的方式对我施以惩戒。横竖我选择了沉默,静观着在场者共同的心境平复。我在这群极有可能是从各方赶来的陌生人间侦测到了一种极强的内聚力。就好像他们在想——就好像我们在想:这就是时机,这就是地点,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我们的问题。也像是有一缕精气、一阵微风、一股强大的道德气流、一种不可见的力,正将我们推向未来,也将我们这群自发组成的、仿佛忽就拥有了破坏力的人们永远焊在了一起。
这便是那种,我忖度着,我们从不会在电视报道中见到的事:仿佛心照不宣的人们的沉默共谋、随时都在兴起却从未被察觉的无言叛乱、偶然集结的人群、发生在公园中或阴暗角落里的突然集会,让我们时不时还能对人类的未来保持乐观。他们于几分钟内聚拢,而后散去,所有人都加入到了这场对抗道德沦丧的地下斗争中。某日,他们将携空前的愤怒揭竿而起,将一切的一切炸个稀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