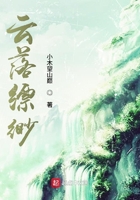但是虞娘不是普通人,她可是斩将罗刹。趁着药劲没上头,神志还清明,虞娘用牙齿在床边啃了一条木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准角度扎进手指里,用疼痛让自己逆着药性保持清醒。同侍女诉苦,请了老爷到房里来看看自己。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情话使老爷动容,等老爷附下身为自己掖被子的时候,一口咬断了他的喉管,鲜血溅了她一脸,连眼睛里都是粘稠的红色。
一人身死,虞娘立时感到力气恢复了一些,用肩膀抵着闻声而来的丫头的喉管,生生撞碎了她的骨头。十三四岁的小姑娘,花一样的娇艳,捂着脖子发出嘶嘶的喘气声,没一会儿就憋死了。
随后电光火石之间便是人间炼狱般的屠杀。
虞娘手上的刀见血是家常便饭,从杀“老爷”开始,她也一直一直告诫自己不过是为了破阵逃生。可是她觉得恶心,恶心的感觉来自哪里呢,是因为空气里挥之不去真实到令人作呕的血腥气,还是因为晚上贪嘴吃多了酸菜炖猪脚?
都不是。
是恶心自己,自己的每一刀的弧度、金属和皮肉摩擦的声音、鲜血喷到脸上的触感都很恶心。
刀有了顾虑就不快了。
她黏腻的手伸向摇篮里的婴儿,孩子冲她笑了,孩子认得自己的母亲。
或许在这个世界里唯一的恶魔就是自己?仗着高出众人的视角屠戮生灵,不论值得与否,不论是非不论因果,只想毁灭此地达到目的。
这是幻境,虞娘默念。手攀上了婴儿幼嫩白皙的短脖子,脖子上挂着一把打得精细的银锁,上书“长命百岁”,银锁被摩挲得发亮,日子过得这样窝囊的母亲也希望孩子平平安安健康终老。
孩子在笑,孩子哭了,孩子没了声息。
或许幻境的前半部分并不是噩梦,屠杀开始才是噩梦真正的开端?
虞娘看了看自己手上的血污,真脏啊。
可是脏又如何,谁不是一身脏污的活着?
出了幻境,虞娘的重剑又回到了手里,槐树沙沙作响,颤抖似的,虞娘的煞气浓的仿佛凝成了实体,待她走近阮北时,看见的是那晚吊在窗外的隐卫正在扒阮北身上的百宝珠披。
“此件鬼衣引人入魔。”这位行为极其惹人遐思的隐卫向虞娘求助。
怎么帮旁人破除迷障,这师父可没有说过。“你有啥办法没有?”虞娘将问题团成团,毫发无损一丝不改地抛了回去。看着隐卫忍了一忍没有忍住:“你这剑哪个师傅打的?吞口真好看,我也想打一把。”镂雕兰草吞口,玉棱来的那夜,客栈窗口外映着月光的影子上,虞娘就盯上了,特别喜欢。
隐卫楞在当场:不愧是“斩将罗刹”,不过是一柄剑便能判定我的来历!但此时不是针锋相对的时候,隐卫急道:“请虞将军费神救救姑娘!”
不用她费神,阮北自己悠悠转醒了。
隐卫瞬间消失在树林里,走的时候一脸震惊,可能以为虞娘会提剑阻止自己来着……
血人虞娘杀性未已,一柄玄铁八棱剑架在了她的领口:“扒了先?”
阮北竟一点惧意也无,低头看了看身上的华服,真是好看,黑夜里也是熠熠闪光:“它救了我。”他们救了我。“玉棱呢?他还好吗?”
玉棱化成原身,白花花的一条大长虫晕在坑里,舌头一如既往地搭在外头,晕着也不见一丝聪明相。由于不知道蛇的脉搏在哪里,虞娘踢了玉棱一脚,至于这一脚的力度是否超出必要,是否有泄私愤的嫌疑另说了啊,玉棱扭动了几下尾巴——活着。
“白白受伤了。”幻境里白白为了唤醒阮北,意图自爆妖丹,这一招非常危险,等同于骑着勃利马往幽都鬼城赶一般的找死,未成年妖精不可以学他。
“要命吗?”虞娘掂量了一下队伍成员目前状况的紧迫性,拾起白蛇盘在肩膀上,同穿得跟花一样的阮北一起下山回城。
“我们都还挺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