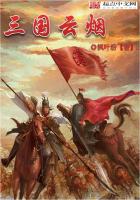就在凛风傻傻的思考这种哲学问题的时候,炽的父亲,夜凛族人的首领,沃卡部的统治者,高亘的四大博济之一,“野狼王”夜弁烺迈着大步朝这边走过来。
每次听到野狼王那如暴风席卷般的脚步,凛风都能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压抑。
“收拾一下,去金帐。”
……
金帐就是汗王居城。
数千年来,草原上的牧民习惯于逐水草而居,但高亘历代汗王并不如此,数百年前,当时的高亘汗王就在高亘河畔建立了坚固的城池。不过高亘人依旧习惯的称之为金帐。
高亘现在的汗王叫做哲鹿汗王。
其实汗王的本名其实是哲归鹿,但通谷关的昆吾人却称其为哲鹿王,或者哲鹿汗。高亘人不知为什么总是按照昆吾人的习惯来称呼。
例如,哲鹿汗的本姓哲弁,鹿是他的名,至于归,按照凛风的理解,应该是来自汗王母亲的姓的第二个字。
高亘的风俗比较特别,习惯于将父母的姓粘合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昆吾人通常会忽略高亘人的母姓而将现在的高亘汗王称为哲鹿汗。
高亘人自己相互间会把父姓的第二个字省略掉,只有凛风这样的下人才会用部族姓氏的第二个字作为姓。是的,凛风没有资格姓夜。
而炽是野狼王的女儿,姓的全称为“夜凛”。炽的母亲是汗王的妹妹,族里人一般通称“哲弁氏”。于是“夜凛”的夜字,以及“哲弁”的弁字,加上“炽”这个名,就成了“夜弁炽”。据说“炽”这个字是汗王所起。
夜弁炽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夜弁煊,今年二十八岁,一个叫夜弁炤,今年刚二十岁。兄妹三人都是一母所生,野狼王是少见的不纳妾的高亘贵族。
总之血统出身在高亘人这里是十分重要的。
……
这次炎夏觐见,野狼王如往常那样没有带上长子夜弁煊。凛风并不会去深究这其中的微妙。他只用关注夜弁炤泰济——高亘人将贵族之子称作泰济——骑着高头大马,欢快的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炤泰济其实并不像他表现的那样纨绔,不仅在容貌上很像父亲,品性也如父亲那样直来直往。煊泰济就有些内敛,很少在脸上显现自己的喜悦与不快。
炽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凛风能感觉到炽今天的心情并不好,是今天早上的羊肉汤做的不好吗?盐放少了?
而炤越是开心,炽的脸就越阴沉。或许炽只是不爽哥哥的趾高气昂吧。
凛风回过头看了眼整支队伍,一百多号人,全部一人三马。和凛风一样,大家都一水的黑披风,披风上还画有白色的狼头。这是野狼王亲卫队的标志,凛风也是今年春天加入亲卫队后才被允许穿上这种披风。
还有十辆大马车,上面大部分是给汗王的贡品,剩下的是来回路上的干粮和一些准备拿到金帐城去兜售的货品。
从沃卡寨——凛风将居住之处称作寨子,因为用木栅栏围成一圈不叫寨子叫啥——到汗王所在的金帐大约有八百里远,野狼王的亲卫队虽然一人三马,打野不敢浪费马力,每天也只走一百五十里。一行人大概要在一些熟悉的地方扎营休息五晚,凛风虽然没有走过这段路,但早就打听的一清二楚了。
凛风的马并不属于他自己,作为一个奴隶,他虽然可以成为沃卡博济的亲卫,但本质还是个奴隶,尤其是得优先保护炽。
炽的马却越走越快,乃至撒开腿跑起来。凛风可不敢怠慢,调整着马步频率尽量跟上,还得注意拉着另外四匹空马。二人不一会就将狼王的大队人马远远的甩在后面。
凛风很喜欢这种在草原上纵马飞驰的感觉,倘若一个现代人是很难体会到的。除非你从小就在呼伦贝尔这样的大草原上,家里有良马成百上千随便骑。
马力也是有极限的,尤其不能长时间快速奔跑。打马飞驰不久,马便渐渐慢了下来,又走了一阵,便来到一处浅浅的水草茂盛的小溪边。马已然不肯多走,两人下得马来便放开缰绳任这些牲畜踩着溪水休息。
……
“阿爸问我哲可定怎么样。”炽突然开口道。
凛风刚把马鞍卸下来放在地上,正准备整理一下包袱想拿点干粮出来吃。炽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让他有点短路。
哲可定?
哲可定是汗王的第七子,年纪好像和炤差不多,也是二十岁不到的样子。
按照古老的习俗,高亘男子二十岁时必须自己建一个帐篷,表示成年。一般结婚也会新建帐篷,这算分家独立。用凛风的话就是成家立业。
“哲可定,定泰济?”他轻声的念叨着,还在揣摩着炽的心思。他不能确定炽说这句话的意思,但他能肯定的是炽想咨询他的意见。只是,凛风并没有见过哲可定。是的,从没有见过。过去这些年里,他只见过汗王两次,但都没有见到汗王的孩子。
“嗯,”炽回头望着远处慢慢靠近的大队人马,哪些人影比地上的蚂蚁还要小,他的脸上一种难以捉摸的神色,“你说哲可定好不好?”
“呃,”凛风嘴里咕噜一下,马上明白了,心中却是一种莫名的失落。炽今年十七岁了,对于高亘人来说,女孩到了十六岁就可以出嫁了,炽也要嫁人了。哲可定可能就是炽未来的丈夫。
不过这一切都是未知,野狼王从来没有提起过炽的婚事。族内虽然对于炽的婚姻有很多议论,但大多数都只是胡乱猜测。
他突然想起去年秋天的事情来。
那是个特别的日子,是炽的生日,也是凛风的生日。高亘人的生日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但凛风每年都给炽过生日,当然也是给自己过生日。
虽然很想念生日蛋糕,可惜他并没办法做出生日蛋糕来,一个是他不知道具体的配方,其次他没有各种材料去尝试。他只能做家乡的长寿面,虽然因为材料的欠缺,味道有很大差距。但炽还是特别喜欢,倒不是这面有多好吃,凛风看得出炽很喜欢这种自我纪念的仪式感。
不过去年的生日,炽没有吃成寿面。
炽离家出走了。一个人走的,连凛风都没有告知,当时的炽正在和面,努力的做着长寿面的准备工作。
快晚上的时候凛风才发现不对劲,他到处找都没有找到炽,于是他去找炤,煊,还有寨子里的其他人。他从野狼王那难看的脸色可以看得出,炽的离家出走与野狼王有关系。当然他也不能问太多,骑了马赶紧出寨去找人了。
茫茫草原上要找一个不愿意被人找到的人真的是很难的。
凛风也没有足够的把握,以他这些年在草原上摔摸滚打的经验,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疑似炽的马的蹄印。但他也不确定,只能赌一下了。这一赌,就找了两天两夜。
第三天的傍晚时分,他在一处荒漠发现炽骑走的马。那马趴在地上奄奄一息,直到凛风拿自己的水囊给马喂水才勉强站起来。
然而天黑了。
这荒原里的夜晚,真个伸手不见五指。凛风也受不了这夜风的刺骨,只能找了个避风的山坳休息,直到下半夜月亮浮出云层时,才循着月光四处探寻。
凭着灵敏的嗅觉——凛风是这么认为的——快天亮的时候,凛风终于在一条干涸的河床里找到昏迷中的炽。
返程的路上,凛风不时的给炽喂水,渐渐能听见炽那含糊不清的声音。但仍然不能分辨清楚。
快到寨子的时候,他听见炽迷迷糊糊的说了一句
“为什么,我不是男人……”
他侧过身,借着月光能清晰地看见炽紧闭的双眼下是两行晶莹的泪水。
……
有时凛风会天马行空的想,炽是不是有那种,嗯,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叫做什么“易性症”的。
想一想炽平日的行为,那就是活脱脱一个男孩子,从早到晚,炽不是拉着凛风到林子里爬树,就是骑着马跟炤比射兔子。说起来,除开凛风,寨子里可能没有任何人的箭术能比得了炽。
除了弯弓射箭,炽用短刀也很熟练。凛风如此评价炽的刀法箭术,倒不是说他自己已经掌握了什么高超的武功,但自从去年秋天他凭着一把弓一柄匕首,一个人杀死十二头狼以后,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自我膨胀的。
是的,十二头狼。凛风有时候回想起这件事就觉得颇为自豪。他自信寨子里,嗯,他不敢说身经百战的野狼王。除了野狼王,其他人他觉得都是随便单挑。即便什么武器都不用。
炽的话,虽然跟他比不了,准确说炽的身手,尤其是射箭,基本就是他教的。炽虽然总是打不赢凛风,但他有个大不了几岁的哥哥炤。于是兄妹俩时不时就来个摔跤比武,虽然多数不分胜负,凛风还是看得出做哥哥的还是手下留情的。毕竟炤的力气真的很大,凛风曾亲眼看见他能扛着一匹马奔跑数里地。
总之,炽从小就是个假小子,如果你称呼她为泰济,她就别提有多高兴了。而你若是称她为塔娜——也就是贵族之女——她可能看都不看你一眼。
……
哎,凛风现在不知道怎么应付炽的话,他干脆装作没听懂的样子继续整理马鞍马镫,顺手又把马鞍给另外两匹马装上。
炽坐在溪边草地上,歪着脖子静静看着凛风,没来由的大笑起来:“我真是个傻瓜,跟你这个大傻瓜说这些。”
凛风也笑了,总算有些释怀,他只好转身匍匐而下,从小溪里掬水而饮。再抬起头时,额角粘上的水珠顺着脸庞而下,用手一抹,也未能擦得干净。他转身看着炽,发现炽还在看着他,只好做个鬼脸。
炽看着凛风滑稽的样子却撇过头装作一本正经起来:“你这种傻瓜又怎么能懂我这样的大人物的想法。”
凛风望着炽,感觉好像就要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人。
他虽然名义上是炽的奴仆,实际上野狼王一家人并没有真正当他是个下人。准确说,高亘人并没有太严格的等级观念。他就像是炽的玩伴,就像是那些读书人的书童一般。而如果炽嫁到外族去的话,那凛风可以肯定自己不会成为所谓的嫁妆。这里没有这个风俗。而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野狼王的亲卫,也许这一次去金帐王城,他和炽就要分开了。
这种伤感让他想起了一些抓不住的记忆,他认为那大约是友情,像是初中高中那些同学分别。
“风,过来下。”
凛风蓦然转过头,却见炽突然凑到他的耳边,露出洁白的牙齿:“风,你能替我做任何事的,对吗?”
凛风向后缩了脖子,感到一丝凉意迎面而来:“这……尽量吧。”
没料这位夜凛族的塔娜,沃卡部的大小姐却猛地转过身朝马跑去。
“为什么我不能是男人!”
看着炽骑上马快步向前跑开,凛风愣在河边好一会也没反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