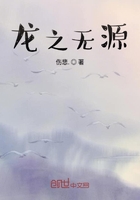穿过游廊是一条白色花岗岩的三曲小石桥,桥下贯穿岑府的活水流淌,甚至还有巴掌长的小鱼嬉戏。
三老太爷身边服侍的胡路站在影壁前迎他们。
“老奴给大爷,三小姐请安!”
“胡叔快免礼!”岑子初抬手扶住胡路,“祖父今日可好?”
“好着呢,正在等大爷和三小姐,就是前几日听闻三小姐得了风寒十分忧心。你们今天要来荣宝堂用晚膳,他还特地吩咐厨房炖了银贝雪梨汤。”
岑子衿心中微痛,“我已经没事了,不过既然是祖父吩咐的,那我今晚就在祖父这里多蹭些好吃的,荣宝堂的厨房可是岑府最精细的!”
她以前其实很少到荣宝堂,印象中岑鹤一直是冷漠寡淡的,现在祖父却特意吩咐厨房照顾给她炖汤……
不是祖父不喜欢她,是她曾经忽略拒绝了。
等进了正堂,岑子衿郑重地跪下给年愈五十四,苍老清瘦的岑鹤磕了个头,“不孝孙女子衿给祖父请安!”
端坐太师椅的岑鹤看着跪在地上脊背挺直的人儿,心中动容。
儿子留下的一对稚儿幼女眨眼间就长大了,如果儿媳妇还在,这孩子又岂会生了病都没个贴身长辈照顾。
说到底是三房子嗣单薄罢了。
“起吧,地上凉。”
岑子初笑着调侃,“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给祖父行这么大礼做什么,害得哥哥站在这里好尴尬!”
“兄长这话可不对,难道我行礼还错了不成?我看啊,是兄长惰懒才是!”
岑鹤看着拌嘴的两人,木然的脸色舒缓。
赵吴氏扶了岑子衿起来,心中感慨,小姐这一病,倒是懂事了不少。
丫鬟进来询问是否可以摆膳,岑子初摸了摸岑子衿的头,和她一左一右搀着岑鹤移到案桌。
岑鹤也曾是前朝满腹才学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当朝天子继位时,长房大老太爷已是内阁保和殿内阁大学士,因大老爷自幼体弱,药不离身,就扶持了刚入仕的岑政和岑敛。
岑家彼时纵然烈火烹油花着锦,但官场沉浮,倾轧不断,也要有所避讳。
岑家已经出了一个阁老,岑鹤便致仕还乡,如他名字般在临安过起了闲云野鹤的日子,直到父母的骨灰从江州送到岑府……
“祖父,这是我从泽芳院带来的桂花糕和云苓糕,您和兄长尝尝味道如何?”岑子衿把带来的食盒打开,取出里面的点心摆在桌上。
“我家小妹也会体贴人了?这可真难得,哥哥可是从来没吃过衿儿做的点心!我先尝尝。”
“食不言寝不语。”
岑鹤面无表情地开口,伺候的胡路眼角一抽,安静地给岑鹤夹了一块桂花糕。
桌子上两兄妹互相看了一眼,默契的低头用膳。
房间里一时间鸦雀无声。
用完晚膳,三人移到抱厦,胡路给岑鹤和岑子衿摆上了棋盘,在岑鹤身边又给岑子衿搬了张加垫子的玫瑰椅。
“不足一月就要开考,准备的如何?”
岑鹤执白子,岑子初执黑子,两人在棋盘上你来我往,但明显岑子初落子速度慢了许多,岑子衿就在旁边观棋添茶。
“孙儿不才,山长今日刚训诫孙儿,稳妥有余,立新不足,恐怕与榜首无缘。”
“嗯,我看过你的文章,秦山长这评价倒也公道。只是各人自有各人文章品性,你本不是投机取巧之子,不必太过在意别人看法。”
“是!不过今日和洛哥儿一道回来,说是三叔父从京都派人送来了闻大人的文章,约我明天去他那。”
“哼,他那个爹倒是会钻营!看看无妨,但切不可过分依赖。”
祖父看不上三叔父汲汲营营,可作为晚辈却不好评价,岑子初落子道,“孙儿明白。”
岑鹤也无意再多说,两人落子声不绝,岑子衿却在想岑子初说的章大人,闻英。
沉思片刻,问道,“兄长,那个闻大人现居何官职?”
正在下棋的岑鹤和岑子初都抬头看突然发问的岑子初。
“翰林院掌院,怎么了?”
“曾任何职?”
“河西巡抚。”
“哪年提调?”
“道清,三十一年初。”
刚回答完,岑子初脸色就有点发白,连岑鹤都放下手中的棋子看向她。
岑子衿还要再张开,他忽然冷哼一声,转头对岑子初说,“天色已经不早了,初哥儿,你先退下,回去好生准备下月秋闱。”
“祖父……”岑子初惊疑看向突然让他退下的祖父,双唇阖阖。
“退下!”
啪的一声,手里的棋子重重压在棋盘上,不容置喙地冷呵。
胡路赶紧上前,“大爷,您听老太爷的,先下去吧,老太爷就是和三小姐说说话。”
岑子初看了一眼祖父,又看了一眼岑子衿,倒退两步跟着胡管家退了出去。
“你跟我来!”
岑鹤瞥了一眼脸色发白的孙女,抬步朝书房走去,岑子衿低头跟在身后,赵吴氏跟了两步,被她停下。
背身站在书桌前好一会儿,岑鹤才冷面如常的转身问岑子衿,“你问你兄长那些做什么?是谁跟你说起这个人的?”
岑子衿自然不能说自己从哪得知,只能编个借口。
但心里却很难过,祖父果然是知道的。
“没谁跟我说什么,我就是关心哥哥这次秋闱才打听了一下闻英罢了,怎么,祖父也知道这个人?”
“放肆!谁教你这么说话的?”
“祖父莫生气,我只是看到祖父听到哥哥提到章大人,下棋的时候好像顿了下,觉得奇怪。祖父已经致仕这么多年,章大人又是外官,您还在任时,这个人都不知道在哪呢,为何会让祖父留意?”
岑鹤看着书桌前的小孙女眼露水光,执着发问,心底有些发凉。
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老了……
“你倒是观察入微”岑鹤冷嘲一声,“罢了,不管你从哪听来的还是自己要打听的,总之这件事不许再提,以后也要烂在肚子里。”
“祖父,有些事不是我们想躲就能躲,想避就避得开的!您当初退让致仕,结果呢?胸中沟壑,腹中乾坤只能配着浊酒吞咽;父亲退让外放,只连累母亲、心腹全部客死他乡,连尸体都有家不能归,只被送回两坛骨灰!您不是心中没有疑虑,可您不敢问,不敢查,但是您不能拦着我!天道不昭,我自己为爹娘求个清白!”
岑子衿双膝落地,凄声恳求。
无权无势无钱,她要走的路何其艰辛,祖父是这岑府她唯一信任又有这能力的长辈,她必须争取。
地上身体发抖的小人儿看的岑鹤眼睛发涩,执着的眼神,真是像极了那福薄的儿媳。
疲惫地闭上眼睛,“你先退下去吧。”
重重地又磕三个头,岑子衿才起身离开。
胡路端了杯茶走进来。
“老太爷,您用茶。”胡路看着岑鹤的脸色,张了张口又沉默下来。
“有什么话就说。”
胡路斟酌了一下开口,“我看三小姐大病一场倒是变了不少。”
茶杯往岑鹤手边推了推,继续说,“这自古至今,哪有孩子不念爹娘的?这是好事儿!如今大爷他们都大了,有些事儿,老奴觉得可以你有什么跟他们说说,免得不领您一片苦心,还要走不少冤枉路不是?”
岑鹤拿着茶碗盖一下下敲着茶杯,嗒嗒声敲击着人的耳朵,让人惊惧。
等到茶水都凉了,胡路正准备下去再给他换一杯时,岑鹤吩咐道,“罢了,你这些日子多看着些。”
“是。”胡路也不再多言,揖手退下。
泽芳院。
岑子衿回来就要沐浴,院子里丫鬟婆子忙碌的进进出出。
等放好热水,青瓷给她挽发脱衣时才惊叫,“呀!小姐你额头!我,我这就去拿药!还有这衣服后背也湿了,可是又招了风?”
岑子衿没做理会,闭目沉思。
她相信祖父也是爱父亲的,但这煊赫威扬的岑府压得他只能选择逃避度日,如今旧事重提,不过只是想在祖父的心中点燃一丝星火之情,只盼将来某日牵扯到岑家时,祖父就算不出手相助,也莫要横加阻拦。
面对祖父的时候她也惶恐不安,但是她不能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