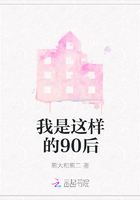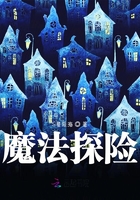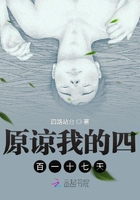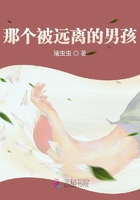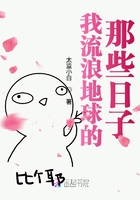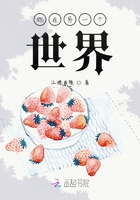孩子们的上课时间是在各种抢答和嚷嚷中度过的,第一节课下课铃声响起,老师说下课的话音未落,陈斌就已经抓起簸箕拿着炉钩子和本小组成员冲出去了。得去挖煤块,当然不是下井挖煤,而是去学校西北角的煤堆那里去找班里要烧的煤,着急是因为全学校六个年级十二个班都在这个煤堆上找煤块,都知道煤块好烧,可这个煤堆里煤块并不多,需要边挖边找。去的越早找到煤块的几率越大。去晚了的只能铲一簸箕煤渣回来了,那会收到全班鄙视的。挖煤还必须去的人多,一组六个男生,一个人用炉钩子刨煤一个人铲一个人拿着簸箕装,剩下的三个则是保护,如果谁敢抢煤那就直接动手。农村,打架很正常,可能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就会动手。不过打的再厉害,也没人去对老师告状,顶多回家被大人发现挨打了,就带着孩子去打人孩子家门口骂几句街,这事也就算了。
今天运气还不错,一会就刨出来了好几块煤。
陈斌正刨的起劲,忽然听到耳边传来他们组员李国印的声音:“你放下,那是我们挖到的煤块。”
“你们挖到的?你们知道这地是我们三2班的地盘吗?所以从我们的地盘挖出来的煤当然是我们的!”
陈斌一听对方这么说就知道坏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只听哎呀一声,三2班说话的人就被踹倒在了煤堆上。“你是不是瞎,也不看看是谁在这挖煤?”说话的是个黑小子,个子不高但是透着一股子狠劲。倒地上那个看了看他,不说话了。因为认出来踹他这个是学校六年级赵瑞强他弟赵瑞刚。
赵瑞刚他哥就是以好勇斗狠闻名整个学校。哥俩最擅长的就是越级战斗,不管你是几年级的,不服就干。如果打不过,那就哥俩一起上。从不胆怯!这边的动静让周围的学生们都停下了手里的狂刨乱铲,起着哄等着看下面的事。结果三年级的怂了。当时农村就这样,谁打架厉害那就怕谁,刚才也说了,孩子间打架,打就打了,并且事后只要不是头破血流那就不会告诉老师和家长。有能力自己把面子再找回来,没能力那就受着。
陈斌说了句:‘瑞刚,行了。赶紧干活吧,该上课了。’赵瑞刚这才继续拿起了簸箕接着装煤。煤堆其实不大,煤块更不多,基本都是煤烟土和小煤渣。都已经被这帮孩子踩的很结实了,可即使这样也还是被孩子们乐此不彼的翻来覆去寻找着。这是他们乐趣的一部分,当有大点的煤块被发现时,肯定大呼大叫,旁边的人就一定会投来羡慕和嫉妒的眼神。
那时的冬天,可以把地冻裂,能让孩子们玩的东西不多。所以天天如此也不觉得乏味。今天战绩不错,陈斌他们装了一簸箕煤块又装了点煤渣,这组人才打道回班。这点煤烧到下午放学是肯定没问题了。
推门一进教室,迎面扑来的是一股子发了霉的味道和酸味。土方子,哪个班有感冒的,那就用班费买点散醋,倒进搪瓷杯子里然后放在炉子盖上面烧。据说这样产生的醋蒸汽能杀菌。不通风的教室本来就充斥着孩子们冬天不洗澡的味道再加上沸腾的醋蒸汽的酸味,真是描绘不出来的酸爽。所以只要一进教室,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样。
上课下课时间过的总是很快,下课后本组的值日女生任务是擦黑板,另外四个男生是去别的教室抬音乐课要用的脚踏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东西算不算钢琴,因为它有钢琴的样子。但是,想弹响它需要用脚踩和手按同时配合。)陈斌则开始做值日生任务中的第二件事,去打饮用水,他拎着已经被喝到底的小水桶,赵瑞刚则拿着抬桶的木棍。两个人前后脚走出了学校大门。
出了学校右转,紧挨着校墙的旁边有条小路,他俩的目的地就是路旁的一口几米深的水井。
“要不是你喊我,我就揍他了。”赵瑞刚把手缩到袖子里,抱着棍哆哆嗦嗦的说道。
陈斌也缩着脖子说:“你打他干嘛?多大点事,打急了又该找你哥了,万一真打坏了,最后回家你爸妈肯定揍你,一块煤的事,没必要这样。”说完,他哆哆嗦嗦的把水桶拴在了辘轳绳头上。然后猛地一转辘轳,伸着头看水桶掉到了井底的水里。俩人一起攥住绳子来回的摇晃,目的是让水桶倾斜可以灌进去水。看着桶里水满后。又合力转动辘轳把水桶摇了上来。
赵瑞刚看了眼桶里的水埋怨道:“又这么多草叶子,这水真混浊”陈斌笑着说:“知足吧,还好是冬天,夏天下完雨,那雨水把路上的马粪都冲进井里了。我看你喝的也挺欢呀?”“那是我渴了!我当时看你也喝的挺开心,靠,你踢我,看我擒拿手!”两个人说闹着把棍子穿过水桶提手,合力抬起来慢慢的往教室走去。进了教室把桶放在讲台旁边。这时的水是没人喝的。因为水质太差了,里面有草和树叶子以及不知道什么物质的东西。水浑浊到几乎看不清小水桶的底。所以这水需要沉淀。上午打来的水,沉淀到下午才会有人喝。
浑浑噩噩的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学了什么也都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及时的忘掉了。老师一说放学。离门近的同学率先跑了出去,其他的人也蜂拥而出。如果那时有无人机在天空俯视拍摄这个小学校就会看到,随着放学铃声响起,由各班里的教室门口就会出现条长蛇一般的人流往校门外跑去,注意是跑,不是走。那情景胜过抢煤块,类似于逃跑,仿佛每个班里都突然出现了一只洪水猛兽一样。
陈斌也随着人群快步往外走,他属于蛇尾的位置。他虽然才10岁但是个子却已经长的很高了,按大小个排的座位自然也就安排在了后面。他们的教室没有后门,只能前门进前门出。他今天是值日生还负责锁门。所以也就没着急往外跑。他走到门口时,理着青年头的班主任跟陈斌说:“快寒假考试了,你得努力,争取再考一个双百!”陈斌很腼腆回答道:“好的,知道了老师!”班主任姓赵,是一名代课老师,年龄20多岁,就是本村的家,那时公家是不会往这种民办小学安排正式老师的,正式工只有校长和大队委是。校长他家也都是这个村的。这个村庄姓氏不多,以赵姓为主,所以叫赵庄。渊源不得而知。因为有人听到过她喊校长叫叔,所以同学们猜测赵老师跟校长肯定有点亲戚关系,才能来学校当的代课老师,那年代有份工作就行了,正式不正式的无所谓。虽然只是代课老师,不过赵老师也很负责。班里这帮孩子,她对陈斌挺好。毕竟这孩子很懂礼貌而且学习成绩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
陈斌背着书包拿着装木柴用的小篮子,站在校门外没有走,他在等住在一个家属院里的孩子们出来,虽然没有他这个年级的,但是后面几年级男女都有。一会儿薛彭勇先出来了,他上四年级,哥俩个,上面有个姐姐,比他大四岁。已经在镇里上初中了。紧接着张晓玉也出来了,她也上四年级了。侯建丽侯建顺这兄妹俩也出来了。这所学校里一共就这几个孩子是一个家属院的,说实话,他们有些被这个村的孩子们孤立,没办法,人之常情。毕竟在同龄人眼里,这几个孩子与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是城市户口,简称:市民户。那个年代市民户好处可很多,国家会按家庭人数每月分配一定量的米、面、油。而农民户那就得自己土里刨食了。种什么吃什么,还得交公粮。所以自己家里基本上都是吃粗粮为主。这就让村里的孩子们看待这些吃细粮孩子,明显有些自卑和嫉妒,也就不怎么爱跟他们接触。好在这几个人年龄也差不了几岁,平时能一起玩,倒没显得有多无聊。
侯建顺年龄最大,上五年级的他个子不高但是很壮,算是这几个孩子的小头目吧,看到人都出来了,他手一挥说:“回家!”这几个人才并排着沿着学校石墙北面的小路,路过了水井继续往东走去,没走多远就到了他们父母工作的单位旁边,这个单位工厂有一圈围墙与村子相隔,墙体全部由红砖砌成,这高墙可比陈斌他们学校的围墙高太多,大约有三米多高。
陈斌他们沿着这个围墙绕到北面再往东走。才走到了陈斌早上来时的那条小路上,路的两边长着两排大杨树,不知道生长了多少年。每棵树都很粗壮,最细的一棵树,陈斌自己的两只小胳膊根本就环抱不过来。树冠也大,夏天满树的绿叶,能把阳光挡在小路的外面,当人走在其中,特别的凉爽。冬天树叶基本上都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被阳光一照,向着天生长的树枝凌乱的泛着惨白的光,显得很难看。
在小路的北面还有一个大院,是另一个单位的厂区,也是个很大的院子,不过他们厂区的家属院可比陈斌住的家属院要小很多,里面的孩子也都上初中或者技校了。所以没什么交集。从小学校到陈斌他们家属院慢走需要十几分钟的路程。进了院门大家说了声再见也就各自散去回了家。
陈斌到了自己家门口,把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拿出来打开锁后,先去把手里的篮子放进了小厢房。又拿出来了一个铁搪瓷盆。
咱们这里先说下陈斌他父亲单位这个大院子的布局。一个占地几十亩的四方形大院子,取中心点一分两半。由一堵红砖高墙隔开分成了工作区和生活办公区。墙西面是工厂,墙东面是生活办公区。办公区最南面是单位办公楼,然后依次往北是食堂、库房、实验室、工人宿舍区,马厩和饲料库。最北面就是家属院了。住家属院的都是已经成家并且在办公室上班的人,这里最少的住户家里也是三口人。按排建的,类似于胡同的格局,比如陈斌家就住在4排4号,(如果在市场上看到写着4排4号的小人书,那就是陈斌的,这是他的习惯,每本书上都写上他的名字和4排4号。)每家一个小院子,有的人家房子后面是别人家的院子,陈斌家的院子南头就是赵媛家房子的后墙。所以家属院里各家的院门呢都是冲东或者冲西开。
陈斌家进院子后,大门靠南有个自建的小厢房,小厢房对面呢有个一米多高的煤棚子。煤棚子北面是一个用铁丝网圈起来的大鸡窝。里面养着十几只鸡。而再往北就是正房了,两间屋,正房当中有个木门,进去后是个一米多宽的过道,直接通向后面的厨房和储藏室。过道东西两边各有一个房间,西面是个大屋,东面是小屋,小屋的北面墙上与储物间有个小窗户相连。
陈斌拿着搪瓷盆打开房子木门,从过道来到储物间,在储物间墙角的袋子里用碗盛出来了两碗麦麸放进搪瓷盆里。在厨房水缸里舀出了点水倒进盆里。然后又去外面大屋窗台下的白菜垛那挑出了一颗比较老的白菜,在菜板上叮叮当当的剁碎。都放进搪瓷盆里与麦麸搅拌均匀。开始了回家的任务,喂鸡。
那时谁家都不用鸡饲料,自家鸡都是纯绿色喂养,冬天吃麦麸白菜,夏天了吃虫子。鸡是个好生灵呀,既能杀了吃肉,又能下蛋。蛋要攒着卖钱,可以用来买本交学费等。所以鸡蛋是轻易不吃的。除非是家里来客人了或者逢年过节时,客人吃剩下了,陈斌才能吃到。香喷喷的炒鸡蛋这个心结,多年以后也是陈斌吃不够的东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