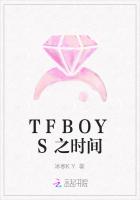他已经很多次在我面前出现了,他总是无助地望着我,希望我能帮助他。他是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孩子,是集团一个分公司的冲压车间的员工。
为了他,我翻了无数次《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我希望能从中找出什么有利于他的条文,为他要求更多的赔偿金,甚至为此私底下请教了熟识的律师。我为他做的这些事情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尤其不能让我的头儿知道。在我的头儿的眼里,我应该站在资方的立场,我们为他购买了保险,他现在出事了,出事就出事,就按照有关规定办了,不违法就行了。我们付了该付的,他已经得了该得的,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我经手办理他的事情,为了他,我跑了无数次医院,陪他一起去评残;去劳动部门,看着他在一些文件上用左手签歪歪扭扭的名字,看着他眼睛里的茫然和无助。他年迈的父亲默不作声地跟在我和他旁边,偶尔叹口气,说:“命啊!”
在整个医疗和评残过程中,我完全放弃了为公司说话,我愿意他能拿到尽可能多的钱来弥补他失去的东西。他的主治医生暗示我说,他可以办理出院了,但是,他本人暗示我他不想出院,说万一伤口发炎了呢?还是要留在医院里。当头儿问到他为什么要在医院治那么久的时候,我答道,他伤口发炎了。
他是为了一种安全感才留在医院里,他以为,若出了院,就不能向公司借钱,赔款又不知何时能拿到,他和他父亲会陷入困境。我想,在此刻他的眼里,世界是冷的。所以,在他父亲每次来公司支钱的时候,我很注意自己的态度,怎么忙也不在他面前露出不耐烦,放下手头的事,把他的事先办了。是的,我觉得他们很可怜,仅仅是可怜,我希望自己能让他们觉得世上还有一点点温暖。
当他领到他应得的赔偿金以后,他还继续来找我,说在报纸上看到,浙江有一家企业的老板,为他这样遭遇的员工,额外给了20万元。他也想做那个幸运的员工,希望我能向我的头儿汇报,让我的头儿向浙江的那个企业主学习。我没有一口拒绝他,虽然我知道他的要求是无法实现的。他用央求的口气对我说:“杨小姐,我知道你是好人……”也许,我真的是个好人,但是,我是好人我也无法改变制度,制度是冰冷的,特别是在钱面前。
我劝他先回去,事情告一段落了,在这里租房耗着会把他的那笔赔偿金用完的。他对我伸出那只断了三个手指的手,说:“杨小姐,我刚出来打工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这点钱够我过一辈子吗?”我知道他刚从家乡出来不久,分到冲压车间做搬运工,他听说冲压工的工资比搬运工高,趁某个冲压工上厕所的时候,擅自开动了机器。他说:“我只想快点学会一门技术。”
刘副总提出“车改”一词后,每遇开会,我们都小心地回避着这个词语,生怕他又突然提起来,当着另两个副总的面,让大家议也不是,不议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