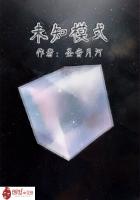“请恕我直言,黛玉群现在不能移防。江阴是长江咽喉,要害之地,是南京水陆屏障;即使日军绕过江阴,我军也可确保封锁长江……”
作战长李卿也上校的回复被打断,安静地听了一会儿电话,接着又继续申诉道:“我早已有言在先,区区一个战斗群的加入不会对南京防务有多大的帮助,然而对江阴来说恰恰相反……什么?”
李卿也挂断电话,摇了摇头,说:“完了,完了。”旁边的同僚们全都看向他,“勿妄而许,勿逆而拒;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这些新军阀,视野狭隘,心胸晦涩,不肯吸纳下级建议,每到紧要关头,总是越级指挥。我们一走,江阴和南京只会被日军各个击破一个不剩!”
“作战长,”黛玉群的参谋长胡笳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地图,“抗命行事,南京失陷,责任在我,又有损与友军之同盟大业;遵命为之,南京失陷,乃是统帅智弱,我等无责。稍加权衡,我部应尽快移防。”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战斗群,不动。”“我们是南线第一支参战的国防军部队!”胡笳的声调突然上升了不少,“执意抗命,坏了抗日统一战线,或许拜你所赐!”
“那你说,去了南京,我军如何克敌制胜!”“去了南京,我军必败。”
“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我的职业操守,不允许我将下属置于险境。”
胡笳想了想,说:“我尝闻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以五音。肉食者尽皆小人,哪管战略之大势,主政者只在乎南京一地之得失,逆之不妥,此为一也。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我等为将者着眼于麾下之周全,误了国家,亦是渎职啊。”
李卿也看向他,许久才说出一句话,愤懑难平:“我虞江铁军,怎就摊上了这等庙堂。”
1937年12月2日,国防军34黛玉战斗群赶到钟山脚下,就是即将成为战场的南京。各部队完成了对空伪装,初步布置了地面防御,与友军取得联系,指挥部门亦建立起来,开始确认开赴战区前的最后命令。
日本陆军携淞沪战胜之威,乘胜追击,来势汹汹,欲一举攻陷中国国都南京。参与此次战略的日军部队有6、9、13、16、18等成建制精锐师团,攻下南京绰绰有余,不论黛玉群参战与否。南京守军成分复杂,素质良莠不齐,但大多是从上海方向撤退下来的残缺不全的部队,元气大伤,难以恢复。
黔系血统的01西施战斗群是淞沪会战中的南线快速反应部队,在阻挡日军主力师团登陆的时候予以敌人重大杀伤,然而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前些日子经过短暂整编,编入了黔系部队的少数老兵,西施群现部署在雨花台,共计320人,只有一个战斗纵队。南京兵籍中心的驻军和滞留南京的虞江籍市民计397人,也编为一个战斗纵队,驻防在水西门,屏护侧翼。
经过一日休整,4日凌晨,进城后在天亮以前分散进入建筑内隐蔽,再次建立指挥部,与南京司令部联系,然而这一等就是一整天,南京战事紧急,却迟迟未能收到司令部的明确的命令。各层指挥官无不心急如焚,只能派人前往司令部直接交涉。
黛玉群的代表是第一纵队的军需官赖云杰少校,出示了证件,卫兵不敢阻挠。南京的司令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外围的保卫战已经打响,隐隐可以听见隆隆炮声。几经请示,他才见到了总参谋部的上校参谋司马小贤。
“黛玉群都到了吗?”“除了野战医院都来了。”
司马小贤点点头,说话的语速像在打机关枪:“好,司令部的意思是我们把库存步枪弹最多的第三军械库的使用权留给你们,具体位置在西华门外的,这里,这是手令。你们的具体防区还没有规划下来,暂时作为预备队休整一下,等待最新的命令。”
“是。”
司马小贤上楼梯回到作战指挥室,由于外围各部队已经与敌人交火,电报雪片似地飞来,忽然蒋昭中校走了进来,报告说:“江阴失守了。”
军官们开始按照情报重新标记沙盘和地图。“不能再等了。”司马小贤自言自语道,于是快走几步到卫戍司令唐生智面前,再次提出:“我军宜展开撤退布置,至少要开始前期准备。外围各军、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切不可集结南京,要向战场外分散,以减轻南京压力。”
唐生智立即否决了他的想法,说:“国防军34战斗群已经抵达南京,协同我军主力,完全足以打一场防御反击。”
“唐司令,战斗群体系有致命缺陷,建制太小,战斗力消耗太快,不可在战役级别冲突中担当主纲……”“司马小贤!”唐生智打断了他的话,“南京之战,关系重大,你莫要动摇军心!”
“那至少允许我先期布置各部队撤退过江事宜。”唐生智挥挥手,司马小贤就离开了。他与副司令罗卓英在战略上的判断是吻合的,因此来到罗卓英的办公室,阐明了自己的想法,罗卓英十分认同,于是派遣他去浦口处理此事。
司马小贤过了长江,在北岸统计了隐蔽在浦口滩头的船只。管理江滩的都是罗卓英麾下的宪兵。“务必保证船只安全,这是我军的生命线。”“是!”
驻守浦口的是黔军102师,师长是柏辉章,遵义人。遵义靠近虞江,历来是虞江的传统势力地盘,军中竟然装备了一门虞江造37毫米战防炮,是部队出征时到虞江软磨硬泡买的。司马小贤立即为他们选定了炮兵阵地,向炮兵和工兵说明如何用简单的工具材料构筑最坚固的工事和阵地,怕他们理会不了,还画了几幅图。司马小贤还帮他们选定了机枪阵地,以防止日军乘小艇巡弋长江,阻碍我军渡江后撤。
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他忽然问柏辉章:“请问您以前是否认识一个遵义人,年轻人,叫做文畅的,应当是官僚家的公子。”
“文畅我不知,但当今遵义令,就姓文。”
“知道了。”
忽然,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竟然在逃难的人群中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挤过去,喊一声:
“胡红?”
胡红转过身来,的确是她,远比当年更是明艳非凡。
“你怎么还在南京?”胡红没有理他,转身就要走,被司马小贤拉到人群以外,说,“你骂我好不好?你打我好不好?我欠你的,一辈子也还不清啊!”
“事到如今,你还想把我怎样?”胡红甩开手臂。
“如果,你当初没有掉下悬崖,也没有战死,你知道你的结局吗?”这是司马小贤唯一一次再见到胡红。
“新疆事变,我听说过。但那样,我胡红是清白的,我的家人,仍会以我为傲,我是他们最心爱的女儿和姐姐,我宁愿落得这个结局!”
“有个人,叫做陈香阁,你应该记得她。她是穿着定制军装出去的,和你一样。在西伯利亚,她的衣服因为是量体裁衣,塞不进报纸棉絮,塞不进毛衣毛裤,她是冻死的。这才是属于你的结局。你至少还活着!活下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如果我不那样说,你无罪释放,你想过吗?抗战半年来,国防军阵亡了一万多人,我们曾经隶属的教导第五师,后来的第一批十个战斗群,都快拼光了,你知道吗?你是职业军人,在战争面前你别无选择。可是我们班,只剩下你我二人,我得保护你,我必须保护你,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和我们一样去送死啊!”
胡红大笑不止,笑到快要断了气。她垂下头,眼泪接连不断地滴落在地毯上。
“你以为,只有你们才可以理所应当地流血牺牲吗?我胡红一样是忠义之士!我喜欢平静的生活,但如果能堂堂正正为国舍命,我同样求之不得!所以你连问,都不曾问过我,就以保护为名,用如此决绝的方式剥夺我为国效力的资格,究竟是为了什么!”
司马小贤强忍住悲愤的眼泪,用颤抖的声音吼出:“我,司马小贤,我是真的,真的担心你啊!军士长!”
目送走了胡红,忽然,一名士兵跑来报告,副官向司马小贤转述说:“电话。”
司马小贤接了电话,唐生智要求他停止当前的工作,立即返回南京处理军务。司马小贤问派谁来接替他的工作,唐生智回答,现阶段不必部署撤退命令,与日军决战才是头等大事。
“三军之帅,岂能朝令夕改?”司马小贤当即强烈反对,“南京不宜大战,而重在善后!到底是谁劝您在南京布置决战,此人可诛!”
“身为军人,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你不想回来,也行。”唐生智就这样挂断了电话。司马小贤只好重新登船,驶向南岸。副官问他上级说了什么,司马小贤回答:
“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主帅如此,我军必败。”副官听得一头雾水,无言以对。
回到南岸,蒋昭在接他。司马小贤问:“是你向唐生智建言决战之策吗?”
“司马小贤,南京战事乃是出于政治考量,统帅自然主战。不用你言,与我何干?身为参谋,不能制定战略方针,便应该退而求其次,以统帅之战略意图制定作战计划,一味推诿牢骚无济于事。你的精力,应当放在正面作战上来,哪怕它并非最优解。明白了吗!”
12月17日,南京城防全线崩溃,唐生智匆忙下达撤退令,司马小贤突然大吼:“不能发!”他随即看向指挥室里的指挥官们,说:“撤退令不能如此下达,必以旅为单位说明沿途可据守之阻击阵地,转移路线,撤退方法以及重新集结的地点,如不说明,整个南京将陷入一片混乱,部队中会造成恐慌,那会是场灾难!”
“事实上,南京已经乱了。我们再不转移,只会为南京陪葬。”蒋昭说。
“住口!”司马小贤暴跳如雷,“南京之今日,多少拜阁下所赐!”
“来不及了。”唐生智说,“我军战至今日,也算是为国家尽责了。我们走。”
司马小贤拔出配枪抵住唐生智的后脑,指挥部里一瞬间鸦雀无声,反应过来后不少人也拔出手枪对准了司马小贤。
“请司令官把指挥权移交给我,唯有如此,大军或许有救。”
唐生智竟然笑了,回答说:“杀了我,丢失南京的罪责,就由你来承担了。”
司马小贤咬紧牙关,听见这话,只得长叹一声,垂下了手臂。
日军早已占据了制空权,夜间渡河显然是更为稳妥的办法,可是战区司令部一行人排在下关等待过江,如此招人耳目的行为又实在不像个话。再加上日军追兵在后,怕是没有条件等待夜幕,惊慌之下,竟然下达了乘多艘小船分散过江的命令。敌机很快就发现了船队,像一群嗜血的苍蝇一样扑了过来。司马小贤与将军们不在一条船上,命令士兵们拼命划船,稍稍远离船队,同时夺过卫兵的步枪,跪在船头向天空瞄准,趁敌机离自己最近的时候开枪,命中了,但是没能造成伤害。
三架日军舰爆肆无忌惮地在天上翻飞着,疯狂扫射。司马小贤拉动枪栓,再次举枪瞄准,再开枪,也依然只是在敌机身上留下一个洞。三架飞机各自进行了几轮攻击,投下了炸弹,就回去了。司马小贤并不清楚船队的伤亡情况,只要求部下尽快划船。离北岸不足四百米的时候,另一波敌机又飞来了,就从司马小贤这一侧低空飞来。他抬起枪口,子弹似乎打中了挡风玻璃,敌机突然一个应激反应向上一拉,几乎要撞到他的僚机。这下子,自己算是通了天大的篓子。机群迅速重整队形,直取司马小贤的乌篷船,他连忙纵身跳入水中,冰冷刺骨的江水一下子刺痛他全身上下。司马小贤尽力向下游,机枪子弹就从他身边打着弧线飞过,拖曳着细长的气泡。极寒和缺氧迫使他浮上水面,又简略地判断更近的江岸的方向,敌机却也调转枪口重新朝他扑来,司马小贤只能重新下潜,尽力使自己远离当初浮起的位置,谁知这一次来袭的竟然是50公斤的炸弹,在他背后砸在水面爆炸,激起高耸的水柱,而在水下,司马小贤的双腿被强烈的冲击波击伤,潜意识地竖起身子,似乎冲击波又重新从相反方向而来,重重打在他的胸口,一瞬间胸中的气体全变成气泡吐了出来。他勉力坚持下来,静静倒在浅浅的江底,窒息的痛苦回忆再次在眼前闪现,而他只能咬紧牙关等待敌机飞走。司马小贤眼前已是一片漆黑,双腿已经开始不能自已地蹬水,要浮上水面,子弹却仍从水面射下,他于是只能将双手深深埋入淤泥,不让自己上浮。大量的江水已经控制不住地灌入他的头颅,剧痛让他心智崩溃,松开双手,终于失去了知觉。
隐隐约约地,他看见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子,在写着什么。
朦朦胧胧,就好像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