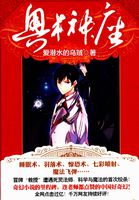陈宣仁今晚喝的茶感觉比他前半生加起来都要多。
当他饮完小茶壶倒入杯里的最后一口茶水,沉吟了会,又对着眼前这个比市井老头还会讨价还价的老人冷声开口:“如若钟离大人没什么别的事,只去纠结在一块尺余的土地上,一味地栽赃嫁祸,那还是请回吧。”
钟离九曲也明白见好就收:“那我也就不再烦扰了,不过今夜我们之间定下的约定,三年无大战,还请大陈皇帝记牢。”
陈宣仁心不在焉,挥了挥手:“知道了,本君有些乏了,就恕不远送,如若想在我大陈赏玩几日,我自然来者不拒,只不过如今陪都这几年都由我儿陈词一手掌管,我会叮嘱他照顾好各位的。”
后面自始至终未曾真正交涉,仿佛是来学习的钟离墨又和兰行止默默嘀咕着:“这大陈皇帝什么态度啊?”
兰行止也不厌其烦:“就照钟离大人这一番交谈,大陈皇帝没立马赶我们走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钟离墨悻悻然。
还是和刚刚一样,流霜仍是没有接他们的话,只是把佩剑从身后正了正,到了方便用手拨出的腰间。
她的声音有如是轻纱遮明月,听了让人有些飘飘欲仙。
却也仅仅惜字如金地说了二字:“有人。”
钟离墨大大咧咧,顺嘴接道:“这么大一个酒楼有人不是很正常嘛?”
兰行止忽然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嘘”了一声。
他语音刚起,这个用来交涉的金屋内就早已经鸦雀无声了。
陈宣仁神情凝重,一双锐厉的眼睛始终注现着窗外如烛火摇曳不定的重重人影。
他这么多年做皇帝的经验,在反刺杀这一行,不谦虚地讲,怕是数一数二。
而太子陈词在相隔不远的包厢中,本来是愉快地聊天,看戏。
而当他把一颗上好的荔枝由下人剥好送入嘴中时,皱眉已久的大陈第一人魏远江就在同时示意屋内所有人噤声。
檀川自然也乖乖照做,心中却不断思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并做着最坏的打算。
而就在此时,整个偌大酒楼坐着的食客酒客也都慢慢静了下来。
伤佛接下来会有一幕重头戏的开场。
舞台上所有乐伎,舞姬好像都受到命令一样有序地退了下去,眨眼之间,处于最中央的舞台上就只剩下了一个婀娜多姿的女子。
戏子摘下脸上遮挡的面纱,亲自为沉寂的众位翩翩起舞,献上了最拿手的一曲。
就连魏远江这么厉害的人,此时也绷紧身体,询问太子陈词:“太子殿下,这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在陈词回答的时候,檀川突然暗自后悔,这种情形傻子也知道要有大事发生啊,他却心存侥幸把山河弓藏在了车厢最隐蔽的地方。
这下好了,真是赤裸裸地被动啊。
他又一回神,刚才陈词说了什么?
没听见。
“……”
随着“吱呀”一声清脆的门响,那个来这巡访的大陈皇帝,今晚这种情形的主心骨不出所料第一个从屋里站了出来。
他却只是嗤笑一声,朗声言道:“有意思吗?都别躲了!想杀我大可明刀明枪地来,往这招呼!”他指了指自己的脖子。
“来啊!”
只听喊声刚落,几十道暗器齐齐飞出,直取陈宣仁的命而去。
身旁侍卫匆忙拔剑大喊“护驾”,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陈词听见打杀声,命令一个待卫去把包厢的门打开,他们三人坐在屏风后,背对着即将打开的门。
突然魏远江动了动耳朵,心神微动,匆匆拉起身旁两位向前急掠出几步,随后飞起一脚踢飞了身后的屏风。
众人还未有所反应就只听“嘭!”的一声,只感觉有重物与沉重大气的屏风毫不避讳地相撞,过了一会声音稍弱,陈词才探头望向那个静止不动的重物。
是那个他命令去开门,但此刻已经没有一丝气息的侍卫。
“太子爷,今天这天罗地网给您父子布下了,太子爷你却没有一丝察觉,这城主可属实当得有些不称职啊。”
陈词退至向下看戏的栏杆旁,看下面大陈酒客会功夫的都早就和刺客们打成了一片,他慢慢道:”是啊,我失职了......”他竟举起手,没有一丝反抗的意思,“不过......在我们几个被杀之前,我还是想求你一件事情........”
对面的蒙面黑衣人问道:“什么事?”
这时的陈词突然狡黠一笑,带着太子爷该有的张狂:”求死!”
黑衣人顿时怒不可遏,不在废话,毫不犹豫疾行提剑杀来,要将那把剑生生刺入这个贫嘴太子说那些糟心话的口中,只见剑尖向陈词面门急速逼进,这一出手便志在一击必杀,一出手便是杀招!
陈词十分平静地望着刺客杀来,剑尖距他十寸,九寸,寸寸递减。
而在令人窒息的区区半息后,剑尖却就那么毫无征兆地折在了三寸。
魏远江甚至没有拔刀,那个刺客就这么被他折断了佩剑,又反过来插进了他的心脏。
大陈杀力第一人,恐怖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