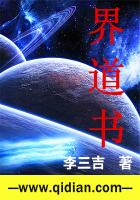朱丽用并不怎么纤细的手指灵活地在键盘上敲动:“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忽冷忽热,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让我多难过?”
正想发出去,手指却在空气中呆住。或许这样的牢骚话会让他觉得自己有点无理取闹,所以最终她还是把打出的字删掉。
深深地无奈地呼吸一下,心里凉凉的。
她多想在人生的路上无论是一帆风顺还是困难重重都有一个人陪着自己,在她开心的时候和她一起笑,在她不开心的时候逗她开心。她不管哪个人是否富贵是否帅气,只要他心里装着她,她便知足了。
但是她爱的唐欣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吗?她不知道。和唐欣在一起快两年了,而相处越久越发感觉自己与他的距离在拉大。这心与心的距离几度让她心情低落却又不想在唐欣面前发牢骚。
“我想你……我只是想你。”朱丽的身影在硕大的房里显得有些落寞,像不得志穷困潦倒的诗人。
时间就在这落寞的空气里流走,已经到了网上填志愿的最后一天。朱丽手执着笔,目光在密密麻麻的专科学校名字中游走,静若水寒似冰的心霎那间就乱了。
前程几茫茫,难思量。此时的她只感到血液升温,头脑一片空白,很想狠狠地扇自己几个巴掌,为自己高中三年没有真正踏实认真而扇,为自己的自以为是而扇。怒归怒,怨归怨,摆在眼前的事儿不能不面对。
爸妈希望她读个专科,选个师范或护理专业,而朱丽知道自己这点分只能选个二专,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很麻烦。唐欣也正为自己的前程而迷茫着,也就不曾给过她一个字的建议。
远处石匠们的嘹亮而狂野的歌声唤醒了朱丽,她努力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干燥的草地上。
一位衣着长衫,古装打扮得六十多岁模样的老太太走了过来,她扶起朱丽,说:“姑娘你总算醒了。你是哪儿的人?怎么睡在这儿?”
朱丽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她想,难道农家乐也有歌舞戏剧表演?
她惊慌失措地张望着四周,不远处有几栋房屋,很多人站在房屋旁伸直了脑袋向这边张望。
房屋后有几个石匠模样却依然身着长衫的人敲打着石头并时不时向这边张望,眼里除了戒备还是戒备。
朱丽把视线收回定格在抚自己的老太太的脸上,那张脸有几分像奶奶又不像。朱丽眼里噙满了泪水,内心充满着恐惧,无助地问:“我这是在哪儿?”
老人拍拍朱丽身上的泥土说:“这是梁子坝,姑娘你是从哪儿来?”
老朱丽努力地回想,老家并没有一个叫梁子坝的地方啊,而且自己好像是在老家的山林里晕了过去,怎么会到这儿?这到底是哪儿?为什么这儿的人着装如此古怪?一系列的问题让朱丽更慌更害怕。
“姑娘,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老人又问了声,朱丽说自己家的所在地叫清楠,老人摇摇头表示不曾听说过这个地方。
见老人对自己很关心便说了自己如何由新家到老家再到晕了的经过,老人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见你衣着奇怪大伙儿都不敢来看看你。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婆子就没想那么多,于是上前来问问你的来路。我看姑娘最近难以找到回家的路,如若不嫌弃就到我这孤老婆子这儿住几天吧。”
朱丽点点头,身在异乡为异客,如今有人愿意收留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当朱丽走近屋子时,站立在屋子旁的人都远远避开却又目不转睛地盯着“着装古怪”的她——头发高束,鼻梁上架着个怪怪的架子,虽也挺好看的但是在他们眼里觉得很别扭。
老人把朱丽带到自己的屋子,朱丽好奇又拘谨地打量着屋子。木镶竹夹的造型很像规范后的农家乐建筑,屋子里的陈设很简单但别有一番雅致,一束绿色的花插在一个咖啡色的瓷瓶里很漂亮,在这暗色调的房间里也显得很耀眼。似乎那雕有仙女舞动图画的柱子,椭圆形的桌子和淡紫的轻纱都成了这束花的陪衬。
整个房间古朴古香,干净雅致。
朱丽又用余光打量着眼前的老人,表面上看起来衣着简单但那衣服的质地却让她吃惊。看起来她年事已高但面容和善举止不俗,让人感到亲切,似乎能看到她年轻时的倾城容颜。
老人铺了铺床,对朱丽说:“姑娘面色苍白,嘴唇发紫,想必是没有休息好,所以你现在就先休息会儿吧。”
朱丽将鞋袜脱下,用老人打来的水洗了下脸脚,她抬头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婆婆。”
老人拎着面盆里的帕子说:“名字不过是代号,叫什么还不都一样?我夫君姓李,你就叫我李婆婆好了。”
朱丽点点头礼貌地叫了声,问:“那怎么没有看见李公公?”
“什么李公公?”老人的脸色顿时转阴,朱丽心里一咯噔,想,难道自己说错了话不成?还是他们夫妻关系不好,忌讳别人说起对方
老人仍然不悦地说:“只有阉人才叫公公呢,姑娘看起来安静娴淑的,不想竟这样无礼!”
朱丽心里暗自后悔自己的言语失当,立即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问你的丈夫。”
“丈夫?”李婆婆一脸的迷惑。
“也就是李爷爷,您的……夫君。”朱丽解释道。心想难不成这儿的人都不把老公叫丈夫,夫君?是什么时候的称呼啊?不会是在拍电影吧?
李婆婆难为人察觉地轻叹了下,并没有回答朱丽的话,朱丽怕自己的言语再次失当也就不敢再问什么了。
李婆婆倚榻而坐,问朱丽:“你叫什么名字?”
朱丽轻声地回答道:“朱丽。”
“你的家乡有什么特别的吗?比如说季节特点,风土人情之类的,你说的越详细越好,我好托人帮你找找或打听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