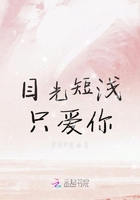那天,千秋的脸红到了耳根,手上的那封花笺也只是急急往书生手上一塞,就逃得飞快。
回去后的千秋连喝了三杯茶水,骂了自己整整一个时辰。
自己怎么这么笨!
第二天,许铭上门了。
他像个大爷一样吩咐千秋家里的丫鬟拖了一张椅子在院子里坐下,一边喝茶一边看千秋扎马步。
许铭,“让你逃课,这下被罚扎马步舒服了?”
“你少在那幸灾乐祸!”千秋瞪了许铭一眼,“你来干什么?看我笑话?”
“笑话?”许铭丝毫不掩饰,不收敛地嘲笑她,“你昨天在街上那样子才真是笑话,我看够了。”
一说起昨天摔倒,千秋又羞又恼,真想跳起来给这个嘲笑自己的混小子一脚。可远处老师又在看着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千秋咬牙,“别笑了!”
许铭哪里听她的,只顾着自己笑,一边笑还一边说,“小千秋还不知道那花笺里面写着什么吧?”
千秋有不祥的预感。
许铭,“里面写着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春天冒绿芽,夏天长绿叶,秋天落入土,冬天死翘翘。”
……
千秋忍不住了,她收了马步,直接一脚踹向了椅子上坐着的欠揍的某人,“就知道你小子没这么好心!”
许铭一只手就抓住了千秋的脚,“你练功不用心,哪里打得过我?”
“混蛋!”
“骂混蛋你还是打不过我。”
“你……”
千秋和许铭总是这样的状态,两人打打闹闹地长大也挺开心。
所以两人的父母其实私底下开始商量两人的婚事,但当事人却是浑然不知。
至于那个一面书生,既然被许铭搅黄了,千秋也不再执着了。
直到某天,千秋在街上闲逛的时候,一群难民自城门处闯了进来,又很快被官兵镇压。
千秋远远地看着这群难民,个个面黄肌瘦,也顾不上仪容仪表,蓬头垢面地呼号着。
最小的难民不过还只是母亲手中襁褓里的婴儿。
此刻也哭得正凶。
这一瞬间,千秋愣在了原地,她看着他们,好像这些人和自己不是一个世界的。
“姑娘觉得他们可怜么?”
千秋听此声有些熟悉,就回过头去看,问她此话的正是那天在小道朗诵的书生。
她看着书生那看得很远的眸子,“他们是什么人?”
书生,“从西边战场逃出来的流民。”
千秋,“现在有地方在打仗么?”
“嗯。”书生有些不忍,“有人苦于战乱,有人安享太平。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可能不久后,这世界上再无太平。”
“应该是阁下多虑了吧,我们朝历来与西面蛮夷征战,这并不是稀奇事了啊,因为战乱有些流民也是正常,你说这是天下打乱了开始……”千秋小声道,“你难道不怕这话被别人听到,说你妖言惑众么?”
书生,“这话仅姑娘一人听到,姑娘不说,就无人知晓。”
千秋戏谑,“那我是不是等于掌握了阁下的一个把柄呀。”
千秋伸出手来,问他讨要了一张纸和一只笔,在上面唰唰写了一首诗,待墨干后折叠起来塞进书生手上,“这才是我的真实水准,还请阁下回去之后,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