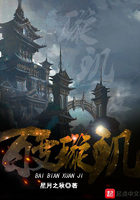桑钺睁开眼,发现自己在舅舅家,心想自己睡觉前不是在家里吗?不过,父亲和舅舅并没有给他提问的机会,因为二人正激动的抱在一起,又是蹦又是跳,搞得像是中举或登科,然后就冲出去,紧接着外面就是噼里啪啦一阵乱响。
不过,他并没有去纠结这些事情,因为一股奇异的感觉突然笼罩住了他,当他闭上眼睛,周遭便似乎有许多东西在围绕着他欢呼雀跃。
桑钺睁开眼,身边居然真的闪烁着红色的光点,红色光点汇聚在一起,宛若一条丝带般绕着他转圈。
当桑父和他舅舅进屋看到后,兴奋的表情里瞬间多了敬畏。虽然,眼前的孩子是他们的后辈,但对于仙师的敬畏早就深深刻在东土百姓的骨子里。
第二天,桑钺的舅舅就命人快马加鞭去了宛郡,因为在地方只有州府和郡城设鸡犬司分司。
就在鸡犬司的仙师来到貳县的当天,貳县县尉在菜市口垒起高台,并且提前几天就张贴了告示说,今日午时要斩妖示众,以儆效尤。所以今日前来观看斩首的吃瓜群众分外多,何况很少有人会见到斩首妖人这样的戏码,要是看一场,都够茶余饭后谈半年。
而菜市口旁的酒肆里,一个说书先生正在那里有形有色的讲着演义,听故事的食客则都听得津津有味,就连没夹到菜的筷子也会往嘴巴里递。
如果桑家镇的人来了这里,定然会认出那个说书先生,他不正是老黄也。兴许大家还会打趣他蹭酒喝都蹭到了县里。
不过今日之他来到此处,并不是为了说书,也不是蹭酒,当然也不是观看斩首妖人。而是为了来见一个人,一个离开很久,终于归来之人。
随着一阵锣响,斩首大戏终于拉开了帷幕。桑圆的囚笼被富有戏剧性的盖上了黑色的布,几个县衙的壮班抬着它,早早的来到了高台。附近赶来围观的百姓在台下指着被盖住的囚笼纷纷议论,似乎大家都在讨论着妖人的模样。有的人说它长了三个脑袋六个手臂,还有人说他身高十丈,不过立马有人说他是个傻子,十丈大的东西,怎么可能塞进这么小的笼子。总之,所有人都像是在看戏,而布盖揭开,妖人斩首就是这幕戏的高潮。
待人群将菜市口围的水泄不通时,县令大人才在县尉、主簿、典史以及一大群吏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现场。
这时,老黄已经不再说书,而是在临街的座位上与一名男子相对而坐。桌上是一壶酒,一对酒杯,一碟茴香豆,一碟炒花生,一碟酱牛肉。
“我以为您再也不会回来了,结果没想到您回来了,更没想到的是您的牵挂居然这么多,竟然还比不得老黄我。”
老黄目不转睛的打量着眼前的男子,似乎想从他的脸上读出这些年岁月带给他的痕迹。
那人神情空泛,眼中映射出的景象像是一副灰白的海景,灰色的海,白色的天,灰色的云。
他看着楼下菜市口这喧嚣的人群,放下酒杯,呢喃自语道,“究竟是有什么不同,让大家如此?”
老黄似乎听力很好,咀嚼完牛肉,也看向楼下,发出“呵”的一声,又继续道:“人妖殊途,仙妖殊途,仙人殊途,您不是早知道,也早就经历过的啊?我们改变不了的,当年没改成,现在也改不成。”
说到这,老黄又给自己斟满酒,一饮而尽,然后重重的放下杯子。
“总能改变的。”
说罢,二人突然安静,不再说话。因为囚笼的布盖被揭开了。
“怎么是这小子!”老黄见到那妖人的面庞,立即就想起了自己讲故事时每次都来凑热闹的桑圆,毕竟那群小孩每次都喜欢问这问那,老是打断他,害得他好几次险些忘记讲到哪里。
“故人?”那男子盯着桑圆,问道。
“非也,只是认识。”
“蛊雕妖人,还是孩子,真可怜。”那男子站起来。
“您要出手?”
“嗯,你先去阳都见我三弟,这一次真的要麻烦你了。”说罢,他就带上了斗笠,蒙上面。索性他们位置偏僻,没人看见。然后,他走下楼梯。
老黄从二楼窗户往下看着那男子即将融入人群的背影,心里感叹现在真是不知道男子到底在想啥了。然后提起酒壶豪饮,喝完酒水,准备离去。
刚走下楼,店小二就笑迎上来,“先生可是吃好喝好了?”
老黄点点头,“你家酒水滋味着实不错。”
“先生故事也讲的很好!”
“凑活,走了啊。”
“先生,您不能走?”
老黄一愣,旋即又笑道,“下次有机会再来你这里说书,我真有事,走了。”
“不是,先生,你酒钱没结。”
老黄一个趔趄,心里开始骂那男子,正事还没开始,就给自己添堵,自己这么多年靠“街头卖艺”为生,能有几个钱,哪次喝酒不是蹭人家店家,现在倒好,你堂堂一公子哥一回来就要我请客,还要我给你跑腿,没天理,没天理!
最终,老黄软磨硬泡,让酒钱便宜了些许。
一出酒肆,老黄摸着干瘪的钱囊,扭头看了一眼菜市口,便消失在街道上。并且还下定决心再也不跟那男子下馆子了。
老黄走了没多久,县太爷终于下令斩首。只见那挺着大肚腩的刽子手朝手上吐了口唾沫,然后在众人围观下依旧镇定自若,屏息凝神,准备行刑。
有些胆儿小的,在刀起时赶忙捂住眼睛,应当是怕见到血腥的画面,不过嘴巴里却在那里叫好,叫嚣着让妖邪知道知道我们人族的厉害!
不过,当那些人睁开眼的时候,却发现刀起却未刀落。因为,一条粗壮的藤蔓从斩首台的木板上生出,然后沿着刽子手的腿,一直爬到他的手臂,刽子手被紧紧束缚,就连嘴巴里都塞满了藤蔓,令他只能发出“呜呜”的哀嚎。
“啊!妖人的同伙来了,大家快跑啊!”不知谁喊了这么一句,瞬间,围观的人们便作鸟兽散。
在乱糟糟一片的环境里,没有了男人和女人,以及老人和小孩之分,有的是心里只想自己和家人安全逃离的百姓们。不论是老人在人群摔跤,还是孩子在人群里跌倒,都没办法停止这脚步踩踏的洪流。
有人劫法场吓了县令他们一跳,他们虽然在意,但最终也不会被深究,甚至在貳县这一亩三分地,他们还可以串联和平息这事端。
但百姓被踩死,那可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县令看着台下乱哄哄一片,心里有些后悔,自己怎么就只考虑了功绩却忽视了隐患。这要是被传成好大喜功,那他今年考评可就得不到甲了。
当县令悔恨交加,担忧考评时,摔倒哭泣的孩子,跌倒无助的老人,真的就只能看着那人群和脚底板向他踩踏过来,一切不过电光石火,来不及反应。
他们闭上眼,准备接受这场惨痛的无妄之灾。过了会儿,睁开眼却发现这里不是黄泉彼岸,依旧是那个嘈杂的菜市口。茫然的孩子和老人环顾四周,才发现身后树起了一块坚实的木墙,木墙阻挡住了那些犹如黑白无常的腿脚和汹涌人潮。
“得救了?是仙师救了我们吗!”
老人只犹豫了瞬间,然后立马跪在木墙前磕头感谢。
就在这时,台上恼怒的县尉终于看见了逆人潮行走的斗笠蒙面男子。在县尉眼里,男子诡异,人流居然冲不倒他。再加上他来救妖人,便马上给他也打上妖人标签。
“孽畜,竟然敢闯刑场,来人啊,将他拿下。”
县兵待百姓散尽,就立马将男子围住。
可男子面对数十名县兵,只是抬起手,轻轻一握,县兵脚下的地面上便瞬间长出一颗巨大的树,树枝将周围士兵全都困住。士兵们自然不会束手就擒,各自剧烈的挣扎,但就在这时,树上结出许多鲜艳的花朵,花朵里飘出一阵甜甜的香气,士兵一闻便纷纷失去了意识。
台上的县官吏员皆大吃一惊,虽然他们都知道县兵不堪,但平均武力值也大多比三班的人要强不少,现在居然一触即溃。
再看看那参天大树,所有台上的县中大佬都想骂一句,“这不是仙师手段吗?仙师救个什么妖人啊!”
不过这样,反倒让大佬们觉得事情变得更好解决,毕竟出啥事,都有仙师大人顶着,何况这仙师手段这么高,定然不会是只燕雀。
“仙师大人,不知为何要来扰我刑场?”
县令拱手作揖,想了想,才想出这样一个称呼,毕竟不知道对方官居何职,但仙师基本都是七品以上,而即便没有为官,那必然也是某个大家族的客卿供奉之类,总之不好得罪。
“不为何,只是因为他还是个孩子。”
说罢,他意念微动,一根细细的藤蔓就钻到枷锁的缝隙间,然后陡然膨胀,将枷锁撑裂破坏。
也不再理会貳县要员们,只是低着头,看着受惊瑟缩的桑圆,然后问了一句,“要跟我走吗?如果不想也可以,我会送你出城的。”
男子带着斗笠,蒙着面,眼神空泛,眉有风霜,顿时让桑圆想起来老黄故事里的那些风尘中客。
“我跟你走。”
桑圆用手臂上的羽毛擦干眼泪,跟着男子扎入风尘。
只留下县中那些要员在哪里大吼大叫干捉急,没有武力的后盾,面对斗笠客这样的大仙师,他们着实不敢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