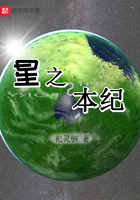老头儿也说得不错,他真没什么大志,也就是什么远大的志向,其实就是一滩心安理得地躺在沼泽里的烂泥或者朽木,心安理得地一辈子呆在这座村子里种地,过着每天一模一样,起早摸黑的农作生活。
当然,有时候,他也会苦恼,为什么自己不是二蛋,为什么自己不是啊强,出生就是大户人家的孩子,逢年过节家里都是挤满了人,不像自己家那间破瓦房,也不用一定要等到过节的时候才会有肉吃。
打小爹娘就一直教他怎么才能当好一个的农民,怎么插秧,怎么犁地,怎么割禾...
林林总总的粗活儿,他都会干,也都按照吩咐地去做,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去做,一定要去当这个农民,一定继承家里的那半亩的田地。
没有人告诉过他,除了做一个平庸的农民之外,他还能做些什么。
每当他看见村里的小孩聚在那里画画,在学堂里朗诵诗文,在鼓捣一些二胡啊,琵琶啊之类的乐器,他都会跑过去问他的爹娘,为什么他不能也像别的小孩那样学学这个,学学那个?
而爹娘给他的答复永远都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家里穷。
穷人的孩子要早当家,就算学好琴学好书学好画,又有什么用,那都是些大户人家才玩得起的玩意儿,那个圈子里头全是他们的人,我们农民天生就比他们低人一等,再怎么努力也挤不进的,倒不如好好种地,好好开荒,囤积点粮食,留着过冬。
那我们跟狗熊有什么区别?
大春又会问。
区别可大着了,你见过有狗熊会拿起锄头去耕地的么?它们怎么能跟咱们比,那可都是些喜欢不劳而获的畜生!
那二蛋和阿强家就是狗熊咯?他们也不种地,但是他们却很有钱。
嘘嘘!你小子再说些什么浑话呢,小声点,别叫人听见了!那不一样,狗熊是畜生,他们是人,到底是不一样的。二蛋和小强他们家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们家的长辈聪明,跟城里的那些人也有关系,一代一代地积攒下来,才会有钱的。
那我们家的祖上呢?
咱家祖上没钱,跟爹娘一样,都是农民,每年的冬天能熬过去,就已经算不错咯,哪还能积攒点啥呢?
那么我的孩子也会这样么?我孩子的孩子都会这样么?
....是啊,会是这样的,世道如此,穷的人只会越来越穷,富的人只会越来越富,世道就是这样的。
大春,死了那条心吧,活着就是活着,什么都一样,人这一生最后尾还是要回归黄土的,不要在意太多,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到最后,我们都是一样的。
爹,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了。
儿啊,听到爹说这种话,是不是会觉得很难过?
嗯,是有点难过。
没关系的,忍忍就会过去的。
...
几年后,来了一场漫长的隆冬,那一年地里的收成不好,每家每户囤积的口粮很快就吃完了,村民们只能眼巴巴地坐在家里,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可那年的春天仿佛失约一样,来得特别晚,无论村民们怎么盼望,严酷的冰寒却没有出现半分衰退的迹象。
眼看着弹尽粮绝的时刻马上要到了,村里几户农家的男人聚在一起,商议要不要进山里一趟,打些猎物回来,接济一下生活。
但因为山里有狗熊,很多男人在自家女人的劝诫下退缩了,到出发的那一天,仅剩下五个如约而至的男人,其中一个就是大春的老爹。
临行前,他们每个人都喝了一口烧得温热的烈酒壮行,然后就一鼓作气地挺进大山里,很快就消失在山林的深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有人说,他们可能是掉到坑里了,被山石活埋了。
也有人说,他们是被狗熊吃了,那畜生邪乎得很,一旦碰上了,就跑不掉的。
还有人说,他们是在山里挖到财宝了,搞到了一生一世也花不完的钱,跑去外头的花花世界里面潇洒去了,永远也不会回来这个破烂的村子里。
记忆里,那个冬天过得格外的凄苦,老爹走了以后,老娘整天守在门口,整天巴望着他们进山的那一条路,期待着老爹会从那里出来,一路走下去,最后回到家里来。
但她每天都会失望,失望的时候就哭,哭出来的泪水把她的脸冻得红通通的,就像是一个令人心碎的老苹果。
如果真是苹果,那该多好,因为苹果是不怕冻的,可以整天整夜都呆在门口外面巴望着那条山路,整天整夜都不会闭眼。
但是,人是会怕冻的。
接着,一个星期过去了,山路上还是没有出现人影,老娘的病加重了,病怏怏地躺在床上,每天就靠两口稀的像是开水那样的白粥维持生息。
渐渐地,村里的人也不再抱有希望了,二蛋和阿强也眼看着瘦了下来,大春这时候才知道,原来有钱人也是会怕冷的,有钱人也是会没肉吃,有钱人也是会变瘦的。
就像老爹所说的,他们除了有钱,跟自己是没什么不一样的。
就像老爹所说的,大家都会死,到最后,大家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他自己倒真被狗熊吃了,在不久以前的那阵子,他还很瞧不起人家狗熊来着。
再后来,在春雷打响前的一个夜晚,老娘也跟着走了,大春捧着一碗白开水那样的米粥,守在老娘的身边,想把她从黑白无常的手里抢回来,但还是没能成功。
他用力地抓住她的手,那一双瘦削得只剩下一层皮抱着白骨的手,想用手中的热汗温暖她的肌肤,但她的手还是慢慢地冷下去了,慢慢地失去了最后那点力气。
就像...此时此刻那一只垂落在他眼前的手那样。
只不过,老娘当时走得很平静,没受那么多的罪,也没流那么多的血。
葬下了爹娘的时候,枯树上的枝干已经抽出了绿芽。
他选在那座大山的边缘,草草地挖了一个深坑,把老娘埋在里面,然后立了一块木质的碑,用借来的毛笔,在墓碑写上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啊大,一个叫啊春。
大是大山的大,春是春天的春。
他看着那两个名字发呆,心里涌现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一种既是自由又是悲伤的感觉,也从没有觉得过...原来那两个人的名字拼在一起是那样的美好。
春风拂过大山,微雨落在草坪,那一刻,他不再是什么农民,不是什么有缘人,也不是谁谁的孩子...从此以后,他就是独自一人了,孤独地一个人,继续生活在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世界里。
他就是大春,大大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