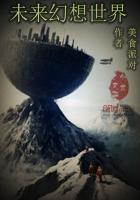忽如其来的,脑子里闪过那一片黑色的海,那个孤独的男孩站在海的水面上,激流的水底下,有一条苍白的巨龙冲破乱流,对着他发狂地咆哮。
天空下着无边无际的雨,那个孤独的男孩站在雨的中央,大声地哭,大喊着不要,可却没有人回应他,也没有人来接走他。
痛,好痛好痛,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痛,好像失去了些什么,好像被夺走了些什么...又好像已经是一无所有了。
心脏被那条龙狠狠地抓住那样,心里猛地抽搐,小白陡然睁大双眼,看着天上越下越大的雨,悠长的风里仿佛具备某种重量,沉重地令他无法呼吸。
那种感觉又来了,就像是三年前,他站在小镇的牌坊下,跟着镇民们一起目送那九位结队的神师们离去,慢慢消失在茫茫无边的雪原里。
那一天,苍茫的天空同样下着很大的雪,那个名字叫做‘雪’的女孩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依然穿着那一件驼色的长衣,在呼啸的北风中沉默地走着。
她还有他们,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再也没回过头,他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塞满了无可救药的悲戚,难过到哭了出来。
从此以后,那种悲伤仿佛根植在他的心里,再也难以去除。
“那条龙把什么东西塞进了我的身体里,”大海缓缓地说,“那东西好像毒瘤,寄存在我的灵魂里,蚕食我的人性,就像是把那种东西...当成是它的养分。”
“原来龙是不需要人性的。”他悲哀地叹了口气。
“那它会不会把你吃掉了...”小白声音发怵地说。
“不会,”大海摇摇头,“但我能感觉得到,它是想要将我同化,令我变得越来越暴戾,越来越残忍,直到丧失所有人性,变成一头纯粹的龙。”
“那样的话,就等于现在这个我已经死了,替换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我,”大海说,“那个我将不再是我,而是作为一条龙,怀揣着无比的痛恨留存于世。”
“为什么?它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小白眼神空白地看着他。
虚无里,那片黑色大海的水平面似乎正在缓缓上升。
无边无际...无边无际....梦境里的黑水仿佛在现实中泛起,沿着冰冷的风啸,无边无际地往外扩散。
他躺在水平面的中央,就像一艘孤独的小船,孤零零地飘零在平静开阔的海面上,四面八方都是黑暗的虚无。
无边无际...无边无际...
他如同死亡一样躺在木舟上,望不到灯塔,也找不到可以停泊的港湾。
“我也不知道,”大海说,“可能是为了报复人类吧,也可能是为了传承,继承龙的...意志。”
“反正到了最后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什么是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小白脸色苍白地看着他,讷讷地说。
平乏无力的声音就像是回放到三年前那场大雪,他强忍着,死憋着不要让自己哭出来,不要让姐姐看到自己的难过。
可是...到底他还是哭了出来,对着消失在雪原深处的人们大喊,对着漫天呼啸的北风大叫。
他声嘶力歇地大喊,他歇斯底里地大叫,“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想要....求求你们,不要再带走他们了,不要再...不要再有人...再有人离开我了...”
“放心,这只是个猜测而已,也可能不会发生呢,”大海温和地笑,伸手摸摸他的脑袋,“说不定呢,说不定你哥的命就是比那条龙的命硬,就是战胜了它,就是活了下来呢。”
小白不说话,默默地看着他,只是眼圈渐渐泛红,噙着的泪水就像海潮拍击着堤坝。
“呀,小白,不要哭啦,对不住啦,”大海忽然又说,“其实每个人生下来都患有一种病,就是会死的病,每个人都会死掉的,不过是迟或者早的问题,真正的男子汉是不怕死的,更不会因此而哭鼻子的。”
“因为那是迟早要面临的结果,对于这个结果,我们无法改变,那还不如想想怎么才能让自己活得开心,怎样才能让自己变得快乐,然后在那结果到来之前,在最后可以像个男子汉那样说一句牛逼的话。”
“就是...我已无悔这一生。”他笑笑,“这几年,在梦里,我还是会遇见她,跟她说话,假装她还活着的样子。”
“我想,她应该真的是累了,才选择的离开,这是她心甘情愿的,没有人逼她,她也从没有后悔过。”
潮湿的冷风又一次吹起,天上的浮云慢慢散去,展露出幽冷的星光,小白忽然坐起来,抱住身边这个大男孩。
他们相互依偎在一起,在这清冷的夜里,就像两条破落的败狗。
隔着大海的肩膀,他眺望着水洗过后的天空,眸子里倒映着清澈的光芒,犹如悬挂在穹顶之上的点点繁星。
...
淌满积水的阴暗小道里,形单影只的少年被一群醉酒的混混无理地推搡着,踉跄地后退几步,最后摔倒在泥泞般的路面上。
“喂喂喂,我没认错人吧?这不是老崔烤鱼那家黑店的死剩种么?”其中一个混混显然是认出他来了,挑挑眉,口气轻佻地说。
“喂,乡下来的小杂种,知不知道为什么整一条街,其他店不烧,光烧你一家么?”还有一个混混拿着酒瓶,蹲下来,拍拍少年的脸,嬉皮笑脸地说。
“一群欺软怕硬的垃圾。”少年抹掉嘴角的污泥,冷冷地凝视着微弱灯光下的那几个吊儿郎当的身影。
“垃圾?大哥,这杂种说我们是垃圾!”有一个喝着酒的混混忽然乐了,转过头对着为首的那个混混说。
他也跟着蹲下身,看看少年沾满泥垢的脸,嘶嘶地笑着,“如果我们是垃圾,那你又算什么啊?”
“算你爹,干你妈的...”少年冷冷地说,“你爹。”
“哟,还挺嘴硬的嘛,不怕死么?”混混戏谑地笑。
少年不说话,依旧倔强地抬起头,冷漠地逼视着那个混混。
凄迷的冷风嗖嗖地吹过,那个混混忽然瞪大了眼,对着他大吼,“杂种!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说着,他不由分说地拿起了手里的酒瓶,墨绿色的酒瓶扬起坠落,飞错在水银色的灯光下,猛地砸在少年的头上,分化成千百片断裂的碎片,犹如残梦一般砰然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