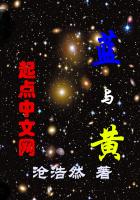夜深人静,时间的流逝总是不予人提醒,宛若贼眉鼠眼的游鱼,见缝插针地穿梭在世界侧漏的风声中。
时间一直在走,明天终究会变成今天,未来终究会变成过去,不存在所谓的永恒,即便是轮回也会有其开始的那一刻,亦有其终止的那一刹那。
创造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光华,所有的一切在背后,终会导向毁灭,就像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会走向死亡。
无可逃避的命运,以及无可逃避的死亡,最后的最后注定还是会孤身一人。
便如头顶的天空,眨眨眼,它就黑了,又眨眨眼,它就又要亮了,好像永远都会这样循环下去。
但终是会有那么一天,那么一刻,它既不会黑,也不会亮了。
....
小白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昨晚过夜的天台上,身上盖着一件破旧的衣衫,还有一件崭新的礼服。
夜里的风很冷,但因为身上有被子盖着,所以他一点也不冷。
隔着几条街外的闹市似乎已经收市了,漫长的夜幕下,这座陌生的城市显得寂静而又深邃,他担忧地看着坐在围栏上的那道单薄的身影,生来第一次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这个最熟悉的人说出一句话。
只是一句话而已,再简单不过,可以是‘我醒了’,可以是‘大海哥’,可以是‘大饭桶’,也可以是‘臭色鬼’...
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种方式跟那道孤寂的身影交流,但是他却硬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个人的背影,喉咙里仿佛被风堵住那样干涩。
持续进行的沉默里,时间不知再一次流走了多少,清冷的月光下,水银色的路灯就像浮游在空气里的水母,轻易地笼罩着一条条穿插分岔的街道。
零星的路人行走在苍白的道路上,投影在地上的影子忽短忽长,很快就消失在某一个灯光照不到的转角里。
空气里荡漾着雨的气息,月亮渐渐被乌云盖住,月光消弭,黑暗随之越发的深重,厚实的云层不知不觉又下起了细雨。
凉飕飕的雨丝纷乱地下坠,被风吹散,涣散着一种难以承受的悲伤,无声地逸散向四周,仿佛银针那般,扎在人的灵魂上。
除了水银色的路灯外,远处没有半点光亮,房屋里最后的那几盏灯火就像是被细雨浇湿了那样,黯淡地熄灭。
此时此刻,无月的天空下,昏沉的街区占据着城市绝大部分的位置,犹如凝固般伫立在原地,沉默着,匍匐着,宛若一头正在消食的巨兽。
小白忽然觉得,坐在围栏的那道身影就像一座熄火的灯塔,被封锁在那一片坚硬的黑暗里,如同爬满藤蔓的墓碑那样慢慢腐朽,慢慢地变得不再有什么意义,不再有什么价值,也不会照亮什么黑暗,就像是慢慢地死去那样。
还不做点什么么?还不肯开口喊醒他么?天气这么冷,他把所有的衣物都给你,连同灵魂都要被冷风冻僵了...
再不跟他说点什么,好像就要来不及了,再不冲去拉住他,好像就要掉下去了,这里那么高,摔下去一定很疼很疼,会折断骨头的。
风一直在吹,小白缩了缩脑袋,收回视线,定定地凝视着眼前遮雨的搭棚,仿佛是在犹豫,又仿佛是在逃避。
没有来由地害怕,心里忽然填满了没来由的不自信,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只怕一开口...迎面而来的一句,是那冷漠的...你是谁?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这里?
为什么要用这种目光看着我?
我认识你么?
我们以前见过么?
有一起吃过饭么?
有一起说过笑么?
....
这一刻,他开始想念老白了,如果老白在这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如果有老白在这里,就是大海哥再怎么犯浑,他也能用一嘴巴子抽醒他。
但是,老白不在这里,在铁轨摇摇指向的北方,在他和大海的家乡,这里不是他们的家乡,这里没有白色的雪花,也没有吹个不停的西北风,只有雨,好像永远永远也下不完的雨,慢慢变大,慢慢将这座陌生的城市笼罩。
千丝万缕的念想发散在雨水的帘幕里,风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那个背对着他的少年忽然转过身,湿漉漉的额发下睁大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
眼睛凝实而又深刻,透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急切和关怀,还是记忆里的那番模样。
“醒啦?”大海定定地看着雨中的搭棚,轻轻声地说。
“嗯。”小白坐起来,看着他,点点头。
大海当即跳下围栏,跑到他身边,弓下身,把手平放在他的额头上,闭着眼睛思索,同时感受着手面依附的体温。
“现在感觉有没有好点,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他沉默了片刻,睁开眼睛,念念叨叨地说,“喉咙痒不痒,呼气吸气的时候,有没有障碍...”
他的语速很快,三两个字跳跃般地说话,浑身淋满冷雨,就像一条离家出走的落水狗,冒着大雨回到曾经的家门前,湿漉漉的脸上浸满不安与紧张。
他的手上落满了雨水,抹在小白的额头上,冷冰冰的,很快又被体温加热,变得暖乎乎的,像是在发烧,又像是从噩梦里醒来,重新回到了温暖的被窝。
“还好啦,就是做了一个噩梦,很可怕的噩梦,”小白虚弱地笑,“现在梦醒来,就没事了,大海哥不用担心,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可以一口吃完三大碗米饭!”
“吃吃吃,就知道吃,吃个屁的米饭,没好起来之前,你都得给我乖乖地喝粥!”大海的手仍然放在他的额上,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好起来以后,想吃啥,哥就给你买啥,但还是得先养好病再说,知道么?”
“又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做个噩梦而已嘛,”小白嘟哝着说,“大海哥真没事的,只是小问题而已,有啥好大惊小怪的…”
大海没有回答他,忽然沉默了很久,风萧萧地掠过潮湿的大地,空气冰冷而寂清,仿佛回荡着丧钟的悲鸣。
他久久地凝视着小白的脸,低声说,“不,这不是梦,这确实是病。”
那个代表着生命的沙漏似乎出现了裂缝,细微的声音在黑暗中隐隐不安。
他放下了手,声音低垂,苦涩地笑着说,“好像挺严重的,具体什么情况说不清,我也不知道还剩多少时间,那个加速过的倒计时,原来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