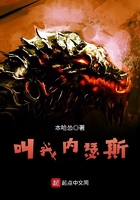铅灰色的沉云笼罩在天空,遮挡了冷月的光华。
银色的雷闪一划而过,男人收刀回身,再度摆正姿势。
他竖刀在身前,风飒飒地吹过他的衣衫,他在冷冽的寒风中睁开眼,横眉立目地凝视着眼前的巨兽。
“雷刀,”他沉声低喝,浓墨般的眼瞳深处,仿佛藏有无数蜿蜒的雷蛇在闪烁。
“居合...”他一字一句地说。
“十字天斩!”他猛地怒吼一声,浓云中暗雷涌动,似乎在遥遥地响应他的号召。
他举起长刀,雷霆滚滚直下,就像一条从空中逐渐裂开的清晰裂缝。
刀锋凛然,不可抑制地切过眼前的虚空,简练的刀轨引导着天上的奔雷。
他猛地攥紧手里的长刀,势要用这一刀,将眼前这个世界...一分为二!
炽白色的高压电流击穿大气,仿佛恶鬼急于跃出深渊般,自穹顶直降而下,笔直地冲向巨兽的头顶,宛若神灵降下的天罚。
无尽的紧迫感随之施压下来,似乎下一刻就会轰落大地,洞穿那道蜷缩在巨兽体内的软弱灵魂。
噗通的心跳声在狂跳不止。
少年的灵魂在战栗着。
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是要被那一道惊雷硬生生地轰死了。
死亡的气氛显露在眼前,他却茫然若失,不知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这场轰轰烈烈的死亡。
然后,他做了一个梦,一个很平常但又很离奇的梦。
梦里,他路过了一个塞满火药的木桶,木桶上牵引着一条细长的火线。
火线的末端被不知谁人点燃了,暗红色的火星在人们注意不到的阴影里嘶嘶作响。
他看到了那点火星,但他没有出声,没有走过去踩灭它,也没有去警告那些站在木桶旁边的那些浑然不知的人。
他别过头,装作没看见,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脚步不急也不徐,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在逃离还是在等死。
木桶在他离开后没多久就爆炸了,当场炸死了很多个站在附近的人,就连一台停驻在路边的燃油机车都被热浪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掀翻了,烧焦地侧过了身躯。
现场死伤惨重。
人们纷纷惊慌地尖叫,匆忙地逃跑,天上的太阳有点儿刺眼。
他抬起头看了眼太阳,那融化一切的白色仿佛夺走了世界所有的颜色。
他把目光从太阳上移开之后,霎那间,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黑白两色的了。
混乱中,人们虚张着口型,猛按着报警的喇叭,但却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
耳膜似乎在爆炸声中破裂了,他的双耳失聪,耳边留下了黑色的血迹,耳蜗好像已经完全不会运转了。
但他却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只是默默地转头看着陷入暴乱中的人们,看着那一场越烧越烈的大火,就像是与这些人这些事隔开了整整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他就像是站在影子的里面,默默地眺望影子之外的那个与他无关的世界。
忽然间,有个女人冲出了人群,径直地来到他的身前,一把将他搂住。
她是搂得那样的用力,就像是要将他塞进自己的身体里,差点就令到他无法呼吸。
莫名其妙的一个深拥,女人身上散发的味道,有些让人熟悉,又有些让人陌生,陌生得有点让他心悸。
五味陈杂,心里有什么坚冰一样的东西,在这一刻裂开了。
不知为何,忽然间鼻子酸了起来,他跟着抽抽噎噎地吸着鼻子,最后站在原地不动地大哭,任由鼻涕和眼泪混在一起,像是浆糊那样,糊满他的脸庞。
他伸手擦走脸上的这些黏糊糊的分泌物,但很快,它们又再次从泪腺和鼻腔蜂涌而出,再一次牢固了那一张悲伤的脸。
这就像是一个堵了很多年忽然泄开的水闸,极深的流水顷刻间泛滥成河,在他的脸上肆无忌惮地狂流不止。
天上的阳光就像即将起航的轮船汽笛一样响亮,无声无息,又无时无刻地照耀着这个黑白分明的世界。
不知不觉,道别的时候又要到了,伤感荡漾在午后的阳光里。
女人的身体一直在颤抖,她同样也在哭,只是在哭一些他不太知道的事,哭一些他还不太理解的悲伤。
“不要死...”女人凑到他的耳边说。
苍白的阳光下,她注视着他的眼睛,眸子深处的苍白,就像是大火烧过后的白色灰烬,沉降着漫长的缄默。
过了许久,她声音嘶哑地又说,低下头,仿佛转述一个卑微的请求。
“要一直一直活下去。”
然后,她就走了,穿过混乱的人海,一直走到海岸那里去了。
在他的遥望中,她登上了那一艘停靠在海港里的轮船。
轮船上的烟囱喷薄出浓密的烟雾,不用听也知道,它在呜呜地拉响着悠长的汽笛,看起来,就像是一曲道别的挽歌。
他目送着她的背影,心里悲伤不已,好像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只把他一个人留在了这里。
如果连他也死了的话,那么,她在这个世界上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下了。
就像是从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一样。
接着,一个男人走出了人群,拉起他的手,带着他开始往前走。
许久以后,他们穿过人流不断的大街,走过青石板铺设的小巷,最后驻足在一家火热的店铺外面。
那应该是一家火锅店,他们不懂规矩地站在店的门口,什么也不做,就那样看着那些进出店门的食客们,看着他们神情各异的脸庞,默数着他们的那些价值不菲的衣饰。
忽然,男人笑了,对他说,“这会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如果我们盘下这里,一定可以赚很多的钱。”
男人的口型同样虚张,分明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可他就是能听懂他的话。
仿佛那张空洞的嘴里流淌出来的不是声音,而是文字。
他不解地看着男人,声音微弱地问他,“为什么要赚钱?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男人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深吸了一口气,眼光未定地看着那一家火锅店的店面很久,然后,他低声嘶哑地说,“因为钱是一样好东西,可以麻痹人的神经,让人忘掉很多的不快。”
“其实,”男人说,“我们都是时间的奴隶,战战兢兢地缩在自以为温暖的泥沟里,终日惶惶不安地看着天外,一边苟延残喘地活着,一边又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爱只是短暂的,那段短暂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永无止境的空虚和痛苦。”
男人面容沉静地说完这一段话,或者说是用嘴巴写完这一段文字,然后,松开了他的手,一步走进了那一家热火朝天的店里。
走得很坚决,走得很无情,仿佛下狠了决心...就这样,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了黑白色的大街上。
他站在阳光普照的地方,就像是热烈的光线下最后一块顽固的阴影,如同污迹一样难以去除。
他抬起头,仰望天空,发现午后的阳光,很是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