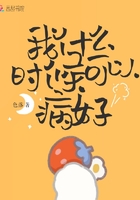第一眼,并未觉得这个男人有何特别。
第一次在王府里见到他,朔王府真正的主人。由于半低着头行礼,又被拉着退到一旁,恍惚和紧张中,阿淼并未看清楚他的五官,不过好像也没如传说中那般,三头六臂,只觉得这是个身材很魁梧很高大的男人,脊背很是挺拔,彼时战袍都未能及时脱下,身后拖着长长的黑色披风,走路的步伐稳健有力,经过阿淼身边的时候,带起一阵劲风几乎要把单薄瘦小的她刮倒。
郑氏走过的时候,微微侧目,似乎不经意地看了看阿淼,又转过头去。而那个男人,甚至连目光都未曾往这个方向流转,好像并没有她这个人存在。
赫赫亲王,为何会纡尊将目光停驻在她身上,就算一秒,一刻也好,都不会。
阿淼很容易地就说服自己接受了这个事实,谦恭地默默低着头,眼珠子却偷偷地随着那个身影而去,走远了,突然,他又远远地回望过来,好像看到了什么如梦初醒一般,在回过身的那一瞬间又迅速地忘记了。
该死,分明看到了什么,可是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朔王瑞谚,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朝堂,都目光如炬,他深信自己经过千锤百炼的直觉,刚才,肯定是看到了,什么让他觉得似曾相识却总也回忆不起来的,人或是什么事物?
王妃郑氏也回头看着,轻声道:“王爷此番刚班师回朝,妾身在前厅吩咐了一桌酒菜为王爷洗尘。”
瑞谚道:“本王尚有公务处理,稍后叶大人和杨大人会过府议事,多准备两副碗筷。”
郑氏道:“那妾身先告退。”说完,稍稍欠身行礼,止步于书房台阶下,等到瑞谚进了书房,她方才转身朝阿淼这边走了过来。
阿淼很是规矩地低着头,甚至于脖子已经开始有些酸痛,看看旁边的方嬷嬷,后者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不适,阿淼吞咽着喉头的唾液,这样久久地盯着地面,如果目光真的有杀伤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这青石地面已经被烧出洞了。
郑氏走到方嬷嬷面前:“嬷嬷,今日王府设宴款待叶陈两位大人,素尘不在,璃翠身体不适,前厅人手不够,让阿淼过去帮忙吧。”
听到素尘的名字,阿淼心下一动,抬头就迎上郑氏的目光,阿淼忽然觉得这看似和蔼的目光此时竟然显得如此深不可测。郑氏在说到素尘的时候,那种云淡风轻的态度,就好像在闲聊中顺带提起一下般稀松平常,仿佛关在柴房那个素尘,并不是和她平常如影随形的那个人。
朔王和朔王妃,两个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时,郑氏停下脚步,也不回头,道:“阿淼,你过来。”
阿淼一怔,确定在叫自己之后,慌忙小跑过去,跑到郑氏面前的时候,甚至还微微喘着气。
郑氏微笑着:“你这孩子,就这么点距离还用跑的,姑娘家家的,一点也不矜持。”
“娘娘……”
郑氏示意落英拿手帕给阿淼擦擦汗,道:“看你走得太慢,还心不在焉的,这园子太大,让你到前面来跟着落英走,仔细着别走丢了。”
阿淼有点不好意思地小声啊了一声,还没想好如何回答,就听得郑氏凑在自己耳朵边柔柔地说了一句话,让阿淼顿时起了一脊背的鸡皮疙瘩。
你,很关心素尘啊。
算上今天,刚好是阿淼到王府整整四个月。
四个月,从严冬到仲春,阿淼本以为自己会很难以适应这种被人使唤,小心伺候的生活,结果发现在朔王府这种角色的转换似乎很顺理成章,只是今天,阿淼隐隐感觉有些不一样。
王妃娘娘在两个时辰之前跟她说的那句话,让她一直心虚到现在,临近傍晚的时候,那根始终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慢慢地松了一点,她以为郑氏会找她,也许她会和素尘一样被关起来,方嬷嬷说过主子们是最不待见下人们嘴碎管闲事,曾经还有家丁多嘴说了不该说的话惹恼了王爷被打了几十棍,还赶出了王府,云云。
就这样胡思乱想了两三个时辰,临近晚膳时分,宴席都准备好了,却一直没有人来找阿淼说王妃娘娘找她过去。
阿淼心里还有那么一丢丢失落,其实就算把她和素尘一样关进柴房,也好过现在一头雾水,还因为郑氏下午在耳边说的那句话失魂落魄,就像临上刑场的死囚一样,最恐惧的不是死去,是知道即将死去却不知道何时死去,怎么样死去。
晚膳开始的时候,郑氏还坐在后堂喝茶,落英提醒了她几次前堂马上开席,郑氏却并不急着起身,只道:“王爷和两位大人定是有朝政大事商议,我还是先不过去了。”
落英不解,觉得王妃今天和往常不大一样,郑氏身为将门忠烈之后,当今太后的义女,被封为郡主赐婚给朔王为正妃,虽说不上对朔王有多少助力,这么多年来也算是一位贤良淑德,颇有德行的王妃,因此也能多少参与一些政见,并且深得朔王敬重,今天,却为何突然避起了嫌?
郑氏放下茶杯,看着外面,对落英道:“你去前堂告诉阿淼,留下侍酒。”
落英是了一声便掀帘出去了,郑氏重新端起茶杯,自语道:“王爷应该会喜欢这茶吧。”
事实上,阿淼侍酒进行得有些胆战心惊。
开席的时候,从门廊远远地看到瑞谚走过来,他已经脱下了战甲,换上了一身宽松轻便的白色袍子,腰间依然是标示着他战将身份的束甲,旁边还有两位穿着正式朝服的人,年龄稍大,大概就是他今天设宴款待的叶大人和杨大人了吧,阿淼知道他们,一个是脾气比酒量还差的耿直兵部尚书,一个是人称“笑面虎”的刑部侍郎,再加上一个朔王,总之,都不是省油的灯。
阿淼不知道郑氏为何会让她特地留下来侍酒,这种场合,本不是她一个小小的丫鬟能在场的,不过,这也许意味着,她不用再回去下等房没日没夜地做杂役丫鬟了。
席间,觥筹交错,很快酒过三巡。
阿淼很尽职地做着一名侍酒丫鬟的本分,提着酒壶给宴席上的每个酒杯添满酒,然后恭敬地退后两步,等着下一轮添酒。
他们在商讨着什么,阿淼并不能完全听懂。
叶大人本就臭着一张脸,喝了几杯酒之后,说话更加急躁,甚至有些歇斯底里。
杨大人倒总是笑着,一边安抚一样地劝着叶大人,一边慢条斯理地和瑞谚说话。
瑞谚话不多,多数时候只是听着两人的话,脸却总是阴郁地沉着,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北边匈戎,东边狄夷,联合兴兵来犯,朝廷匆忙把修筑堤坝的银子挪去作了军费,导致黄河堤坝修了一半便搁置了,而淮东灾荒即将蔓延至黄河,汛期将至,一旦黄河决堤,祸及黄河周边郡县,对于目前的国家现状那就是雪上加霜,但偏偏这个时候,市面上却出现了物价飞涨,不少大户商家囤积居奇的情况,都在无耻地等着大发国难财,丝毫不在乎百姓生计,更加不顾及大宁朝已濒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阿淼听着,心里五味杂陈,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酒壶上镶嵌着的一颗珍珠,好像工匠偷了懒,珍珠打磨得并不光滑,甚至还带有粗糙的毛刺感,而阿淼依稀记得很久之前,似乎也是这样一尊酒壶,上面镶嵌的是极其珍贵的寒山玉,一颗的价值就足够寻常人家五口人两年的口粮了,而那尊酒壶里装的酒,饮起来似乎也并不比这种酒壶装的酒更加香醇。
寒山玉!
阿淼脑子里突然划过一道光,不错,那个笔洗,也是寒山玉,她想起来了,可是为什么瑞谚要把寒山玉笔洗伪装成青花瓷的样子?本来一下子想通了的,这时却又冒出了新的疑惑,想到这,她不由自主地看向坐在不远的正对面,仅仅一桌之隔的瑞谚。
不知道是否因为此时坏脾气的叶大人早已不胜酒力醉倒了,不再胡言乱语的缘故,瑞谚此刻脸色比刚才稍有缓和,但依然正襟危坐,左手捏着一只酒杯,不经意地在手指间晃动着,不时地看看杯中随着杯子晃动的酒,这种稍带金色的透明液体,就是现在正在大宁关边烧杀抢掠的帝夷进贡的。
那个时候,这个强盗还在俯首称臣。
弱则称臣,强则掠夺,这国与国之间的所谓情谊,不过是利益和权宜而已。
瑞谚打心眼里不想理会这些事,他只是个将才,只在朝廷一声令下上战场御敌而已。
席间不曾多言的杨大人突然开口道:“王爷,朝上都在议论皇上这回派您去淮东赈灾,看来,这次您是没法再独善其身了。”
瑞谚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本王这次不仅是没法独善其身,能否全身而退都尚未知……”
这时早已醉倒的叶大人忽地又抬起头来,指着瑞谚道:“朔..朔王殿下,先帝在世时,在诸多皇子中最为赞许的就是...就是你,但为何现在...你只知行军打仗,不理...朝廷大事,宋相已经不...不在朝,就连陆准那个迂腐老儿也...赔上了自个儿满门,殿下你...你这样袖手旁观?为何?!难道仅仅为明哲保身这...这四个字?”
阿淼的心一紧,好似冥冥中有只手在心上狠狠地捏了一把,痛得她几乎窒息。
“好了好了,醉了醉了...”杨大人笑呵呵地把叶大人按下去,然后端起自己的酒杯。摸着下巴上的胡须道:“这么好的酒,咱们大宁却酿不出来,可惜了。”
瑞谚对叶大人的醉言并未在意,倒是听到杨大人说的看似无关的话轻蔑的笑了笑,看着桌上的空酒杯道:“如若有幸,本王下次必将狄夷这酒窖搬来靖天,杨大人你这酒瘾当可得缓解?”
阿淼上前准备给瑞谚添酒,却被他扬手制止,一时间,竟让她进退不得。
这一次,终于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她却显得有些局促,手足无措。
阿淼暗自骂了自己一句没出息,定了定神,稍稍侧脸偷偷地打量着瑞谚。
她终于看清楚了这个传说中神一样的男人。
长期征战沙场的他,虽说是个尊贵的亲王,整个人却完全就是个糙汉子的模样,今日方才归来换装时匆忙挽起的发髻,耳边还散乱着一两绺碎发,边关的风给了他黝黑的皮肤,也给了他五官分明,轮廓坚毅的脸庞。
正打量得出神,被打量的那个男人这时似乎也发觉了侧边的异样,转过头去,正迎上身后明晃晃的目光。
阿淼被他突如其来的注视一个哆嗦,忙低下头快速后退了两步。
瑞谚皱了皱眉,又仔细看了看这个有些眼生的侍酒丫鬟,心想,真是太长时间没有在王府了,下人并不多,但是居然都记不住这是谁了。
突然,瑞谚又好像想起什么,再次回头看向阿淼。
瑞谚充满疑问的眼神让阿淼感到十分不自在,忙垂下头,盯着手中的酒壶,那目光如一道利刃,就这么直勾勾地向她刺来,此时瑞谚确信自己的确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这个少女很普通,身材纤细,穿着王府给丫鬟配备的统一的衣裙,梳着很普通的发髻,可刚才她看着自己的时候,眼神为何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那双眼睛好像在告诉他:我认识你已经很久了。
瑞谚眉头紧锁,将手中的酒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说了一声:“来人,送叶大人到厢房安歇。”
一直待到送走杨大人的轿子,瑞谚才依稀想起几个月前成霖好似提过一嘴,说王妃娘娘在大雪天救了个庆水逃难来的女子,约莫十五六岁,然后收留在了王府。当时听成霖说起的时候,他正为和狄夷和谈的事烦心,也是左耳进右耳出,府里又多了个丫鬟这种细微末节的事,一如平日很快就抛诸脑后。
这天晚上安歇的时候,瑞谚向郑氏问起了那个捡来的丫鬟的事。
郑氏正在为瑞谚整理脱下来的衣袍,听到这话后露出讶异的神色:“王爷是说阿淼?她说她姓姚,家乡灾荒,逃难来靖天又和亲人失散了,也没有好的去处,着实可怜,妾身看她像是个本分人,便留她在府里做个杂役。”
“哦?她是叫阿淼?是这样....”瑞谚点点头自言自语道,“那派她今天去侍酒也是你的安排?”
“其实今天本来侍酒安排的是璃翠,但是这丫头咋咋呼呼的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前厅又人手不够,我看阿淼还算大方得体,就临时让她去顶上了,不过王爷您一向不过问府里下人的事,难道是她今天有什么失礼的地方吗?还是觉得妾身没有问过王爷就收留她这样有何不妥?”
“那倒不是,本王知道你做事一向稳重。”瑞谚抿抿嘴,“没事了,安歇吧。”
郑氏温柔一笑,道了声是,转身灭了蜡烛,自家的糙汉王爷,居然也有如是心细的时候。
倒也不枉她,一番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