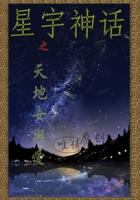“他又去美国了,他是去和慕尼斯脑科神经专家讨论我的病情,应该不会有新的进展,我是不该抱有任何希望的。
我恨他,他夺走了我原本安静沉稳的生活,我可以去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富家小姐,现在这恨淡了些,因为我不想带着仇恨死去。
他走时对我说过,他不会让我死的。我从来不信他的,现在我能感觉到越来越嗜睡,今早背着柏渊照镜子时,镜子里的人眼睛开始有些下陷,浑浊的眼睛也不再灵动。
我没有哭也没用闹,我安静的收拾这坏情绪等待这死亡,那何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解脱。可在死之前,我会失明,陷入无尽的黑暗,我无法记住每一个人的面孔,可闭了眼,首先映入脑海挥之不去的是他温乔川,那笑起来春风十里都不及的俊儿郎。
失明过后,我便会像个植物人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我会在沉重冗长的睡眠中死去。内心世界再丰富多彩,却再也不会张口说话表达汹涌复杂的情感了。
只希望他温乔川早日回头是岸,别再为这份偏执无果畸形的爱将错就错了。”
——来自棠雅沐日记
夏秋之际,多暴雨。上一秒是万里晴空,下一秒阴雨密布,厚厚的云层使大气消弱作用强,温暖干燥的阳光透不进来,残余的余晖也消散得快。成团的阴雨已密集在云层里,待凝结和饱和时,大风骤起,倾盆大雨。
苏柏渊把庭院里的落叶扫完,一阵凉风袭过,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像走完一生的濒临死亡的老人落叶归根,棠雅沐扶着门框走了过来,看到这萧条景色,眼睛里的光亮又暗淡了些。
“棠小姐,进去吧!外面风大。”苏柏渊见她弱不禁风,还不听话跑出来吹冷风,他在放下扫帚,两步并一步赶紧过来搀扶她,她身体微微颤抖,泛白的嘴唇像一扇生了锈的铁门缓慢的吐出十几字。
“再给我看看吧。看一次少一次。”
苏柏渊不敢强硬逼迫她,独自进了卧室拿了件雪白厚毛绒的披风,从她身后给她披上。棠雅沐自从患病以来,性格愈加孤僻,王俊凯给她请的保姆服务她一一不待见,唯独对苏柏渊言她听计从。
苏柏渊是从小和温乔川一起长大的,王俊凯对他为人处事都比较欣赏和放心,所以每次只要是关于治疗棠雅沐疾病的国际会议他都亲自参加,这段时间都是交给苏柏渊照料的,往日都是温乔川亲力亲为。
“相信他,他得了所有人都治不了的不治之症,最后不也是痊愈了吗?这辈子人总得经历些什么,对你而言,可能只是生与死的临门一脚,而对于他是痛苦绝望的深渊。”
苏柏渊扶她坐上庭院的摇椅,耐心劝告她说。这八年多里,他作为温乔川的贤内助好兄弟,一直都是鼓励他的。他的确是有个家庭优越的环境,可先天性的疾病迫使他无法让正常人一样生活,所以他选择学医,想尽一切办法自己救自己。
“我从不信他的,他将我绑起来数不尽的冲击和发泄时,就再也不可能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