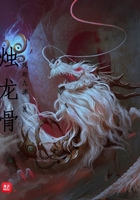青雀从衣柜里翻出郦妃口中说的那件鹤氅,捧在手上。
郦妃伸手摸了摸那鹤氅,里面用狐白一块块拼凑起来的里面儿,摸在手上,手感顺滑,比上一般的裘衣不知要好上多少,只这一件便要价值千金。
青雀捧着那白狐狸鹤氅,跟在郦妃之后,两人到了太和桥时,果然看到宇文斐与云景正往这边走来。
郦妃从青雀手中接过那鹤氅,笑盈盈的走上前去,“斐儿,如今天都这么冷了,你怎还穿的这样单薄。”
宇文斐远远的便看到郦妃二人,冲云景摆了摆手,站在原地。
郦妃见宇文斐也不回应自己,脸上的笑容一僵,随即又是灿然绽开,将手上的鹤氅抖开,亲手披在宇文斐的身上。
“这鹤氅里面都是用的白狐狸腋下的皮毛缝制成的,狐狸毛只有那里才真的是柔顺保暖。”
宇文斐冷眼看着她亲手将那鹤氅给自己披上,又将系带系上,“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冷冰的语气中丝毫不见母子的情分。
郦妃手上一顿,轻笑了声,手上用劲儿将系带系紧后,往后退了一步笑道,“我早上见你穿的单薄,心疼自己的儿子,来给你送件衣服,怎么?还有错了?”
宇文斐冷哼了声,“你会这么好心?”
郦妃叹了声气,“再怎么样,我终究是你的母妃。”
宇文斐听她那落寞的语气,闪了闪眸,别过脸看向那茫茫白色中矗立在远处的勤政殿,“说吧,何事?”
郦妃愣了愣神,自嘲的笑了一声,转身吩咐身后的青雀退后。
青雀收到吩咐,向后退了几步,躬身守在两人身后。
宇文斐见状也令云景退后。
郦妃拢了拢身上的衣服,将两只手缩回袖中,看着宇文斐笑道,“你刚从大理寺那边回来,要去御书房向你父皇回禀事情的吧。”
宇文斐冷冷不做声,郦妃只好又接着道,“一起去吧。”
母子二人静静的在前面走着,茫茫的大雪,身边也不要一个打伞的,就那样在这雪色天地中任雪飘零。
二人的身后是两串长长的脚印,一大一小,却相隔甚远。
“昨日发生的天雷劈人的事情里,出现了‘玄鸟陨卵’的玉佩?”
郦妃眼睛看着前面唇角微动,低声问道。
“是。”
宇文斐也直接回道,只是一双眼略有深意的看着郦妃,“母妃怎么对这事有兴趣了?”
“只是好奇,问问。”
“好奇?”宇文斐冷哼了一声,“母妃好奇的东西可真特别。”
之前北凌线人进京都,郦妃便借此机会竟将蓝翎接到了宫里,欲图与北凌搭线,中间若不是宇文斐中途将人劫走,只怕凭郦妃的手段,还斗不过濮昕那只老狐狸。
如今北凌的事情刚过,她又对前朝遗物有了兴趣,莫非?
宇文斐顿了顿脚步,一瞬不瞬的盯着郦妃,低声道,“母妃最好还是安安生生在宫里好好做你的宠妃,有些事情还是不要好奇的好。”
郦妃身体轻颤了颤,回身看他,口中仍是说道,“只是好奇,怎么?问上一声都不能了?”
“那是前朝余孽!”
“我知道。”
郦妃满不在意的眨了眨眼,转过身,继续往前走着。
“你若是就这样不想活命,当年为何要将我接回?是非让我陪着你一起死不成?”
宇文斐看着她满不在乎甚至有些冷漠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阴郁,一步上前,狠狠的问道。
郦妃脚步不停,却是默了半晌,忽然悠悠叹道,“有哪位母亲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去死的?”
宇文斐心中一颤,脸上也慢慢恢复,仍旧是平时那个潇洒浪荡的七皇子的模样。
“那人如何了?”
郦妃又问道。
宇文斐白了一眼,知道就算自己不说,他面前的这位母妃也会自己派人去查,倒时她若是出了什么事,又要连累自己不说,还要自己给她善后,还不如自己直接告诉她。
“那人死了。”
“死了?!”
郦妃突然转身,高声问道。
宇文斐随意的点了点头,“被那道天雷劈死了,尸体就倒在巷子里,当时没人发现。”
他一字一句的说着,可郦妃却是身子忍不住的轻颤。
宇文斐眯了眯眼,郦妃这个反应有些不对。
“你认识那人?”宇文斐厉声逼问道。
郦妃被宇文斐这样一问,神志马上清醒了过来,连忙摇了摇头,有些勉强的笑着,“我如何能认识那人。”
宇文斐却是不信,“这玉佩的事,是不是你搞出来的?!”
“你怎能这样说!”
涉及前朝那可是滔天的大罪,郦妃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当即就冷下了脸,一瞬不瞬的看着宇文斐,“不是。”
宇文斐仔细打量了半天,看郦妃那样子,也不像是有假,但心里还是存了疑虑。
两人边走边停,足足走了两刻钟才到了御书房。
御书房内,苏太师早已和宇文珏商谈结束,宇文珏体谅苏太师年迈,便吩咐人备了轿子一路抬至宫门口。
这边送苏太师的轿子刚走,宇文斐和郦妃便来到了御书房。
宇文珏抬头看到他们母子二人同来,眼中有些惊异。
“你怎么也来了?”宇文珏看向郦妃问道。
郦妃柔柔地笑了笑,将身上的披风解了交给青雀,自己上前接过李常德手中的茶水为宇文珏添上,楚楚道,“早日见斐儿这样大雪的天气,竟穿的那样单薄,不免有些担心,便亲自送了衣裳给他。”
宇文珏抚了抚郦妃的手,看向宇文斐,一眼便认出了他身上穿的正是价值千金的白狐狸裘衣。
他又看了看青雀手中郦妃刚刚脱下的披风,口中微有责怪之意,“朕赏你的,你倒没穿,却给这个混小子了,他是不冷了,你却又穿的那样单薄。”
郦妃淡淡地笑了笑,“那披风也是早先圣上赏的,比起那些寻常的,不知道要好上多少,臣妾穿着那些也就够了。”
宇文珏冷哼了一声,松开她的手,让她在一旁坐下,转身看向宇文斐,又是连连叹息。
宇文斐看着二人情意浓浓的样子,翻了个白眼,将身上的鹤氅解开随手往椅上一丢,懒懒道,“既然这鹤氅是父皇赏给母妃的,那便还给母妃。”
“宇文斐!”
宇文珏知道从宇文斐从鹿鸣山上回来之后,对郦妃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但不知在他面前他也竟如此放肆,丝毫不加掩饰,不禁有些怒道,“她是你的母妃,她疼爱你,怕你受寒,自己舍不得穿,巴巴的送与你,你却不领情,反倒这副样子像什么话!”
宇文斐白了白眼,一屁股坐下,只当耳边的声音不存在。
宇文珏不禁气怒,拍案而起厉声喝道,“往日你最是乖巧懂事,可是自从去了鹿鸣山,脾气便越来越怪,也不知那东篱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如今连自己的母妃都敢顶撞!若不是朕亲眼看着你长大,怕是都要怀疑你是不是冒名顶替,有人故意派人气朕的!”
郦妃心里一惊,兀地从凳上站起,急忙走上前,帮宇文珏顺了顺气,温声道,“这孩子从小也是皮的,只是臣妾怕皇上不喜,便整日偷偷打骂,硬生生让他做出一副和顺的样子,想来是臣妾早日责打太过了,孩子也压的狠了,这才对臣妾心有怨恨。”
说着,郦妃鼻头一酸,哽咽起来,“可是臣妾有什么法子,臣妾没有家室庞大的母家傍身,只凭着圣上的宠爱走到今日,宫里那一个不是等着看臣妾出错,好惩治臣妾?!这孩子跟着臣妾也是命苦,不能随自己的性情任意的活着,只能被臣妾整日责打,委屈的压着自己的性子,装作一副温文和顺的样子。”
“臣妾又能力有限,总免不了他在宫里受人欺负,但臣妾总是让他忍着受着,后来若不是发生了梅妃那样的事情,让这孩子差点丢了性命,臣妾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跟圣上提起这孩子平日所受的委屈。”
宇文斐听着郦妃那句句肺腑,只是冷笑。
宇文珏却是看着她的样子,打心底里心疼,但也是无奈地叹着。
郦妃抽了抽鼻子,从袖中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的泪,低声道,“如今这孩子,跟了东篱那么久,远离了这宫里的是是非非,好不容易能依着自己的性子任意活上一遭,便随他去吧。”
宇文珏瞪了瘫在椅上,仿佛都要化成饼一样的宇文斐一眼,也是无奈的叹了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