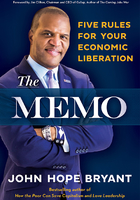三月的柳絮盛季,随着干冷的春风吹撒的到处都是。
拂宁一早就坐上马车进京了,通州接邻京州,不过半日的路程,进了京便一路向宫里去。
慈宁宫里太皇太后早早起了身,尚膳房进茶点进来,司膳的宫女接了大提盒,由祥嬷嬷揭了黄云龙套。宫女们摆上炕桌茶几,祥嬷嬷捧了牛骨髓茶汤到太皇太后面前,花梨木的茶几上铺排开各种点心,太皇太后旁的未动,只接了香茶抿一口。
管事的宫女秋荣猫着步子进来,“徐姑娘来了”
祥嬷嬷望了眼太皇太后,笑道:“听说一早去了御花园替您折花去了,虽说如今开了春,可晨间露气重,倒难为徐姑娘了”
太皇太后闷笑了一声,“你倒肯替她说话”
祥嬷嬷陪笑了一声,“老奴哪是替徐姑娘说话,是心疼老祖宗,难得有个知冷知热的姑娘在身边孝顺着”
按说徐善慈是大长公主的女儿,该是眼高于顶的人物,可偏偏却不同,人很是温和守礼,也不拿自己当主子看,和慈宁宫的宫女也常在一处说话。
祥嬷嬷说不上是想替徐善慈在太皇太后跟前说话,她这一辈子效忠的人只有太皇太后,可总是来侍奉的贵女,性子也不差,提拔两句还是应该的。
“叫进来吧”
秋荣屈膝道是,出身招呼着徐善慈进屋。
廊庑下侯着个身着白底粉花宫装的女子,一双如剪秋般的眸子,笑盈盈地望着秋荣,“烦请姐姐通传了”
秋荣一笑,“哪里当的上姑娘一句姐姐,快进来吧,老祖宗等着了”
徐善慈撂了帘子跟在秋荣身后进了屋,心下有些忐忑,从前在家里讨好母亲用的手段都使不上劲。
“给老祖宗请安”
太皇太后慈善地笑着:“这些日子在宫里可习惯?你身边也没带个伺候的人,若需要什么就来说,别委屈自己”
“在老祖宗身边伺候已是我的福分,慈宁宫的姑姑们和善,在这儿和家中没什么两样”
太皇太后静静地看了会儿徐善慈,突然有点想念她娘那般的性子了,当年静和皇贵妃身份尊崇,乐安又是静和最小的女儿,在宫里是呼风唤雨,跋扈任性,怎么她教出来的女儿说话这般谨小慎微,就跟这宫里的人一样,不新鲜。
太皇太后看了眼她怀里的梅花,浅浅一笑:“这时候还能寻来梅花,你费心了,哀家记得库房里有个白瓷的瓶子,寻来插上吧”
徐善慈一喜,乖巧地说道:“我跟着寻来替老祖宗插上”
太皇太后点点头,望着徐善慈出去的身影。
祥嬷嬷是跟在太皇太后身边五十余年的老人了,太皇太后一眼她就能猜到七八分,“徐姑娘是次女,听说在家中不受重视,难免性子小心了些,姑娘家也难得有这样稳重的性子”
“这宫里这样性子的人太多了”
“听说翟姑娘在家中很是受宠”
太皇太后难得笑出了声,“她老子是个痴情种子,当年为了她娘远离家族,听说这些年也只守着她兄妹二人,这样的情深不寿,哀家活了一辈子也才见了这么一个人”
太皇太后这辈子什么都有了,可从前还是淑妃的时候,听人说起翟家混小子的事迹时,竟对那传闻中的扬州瘦马羡慕得很。
在宫里浮浮沉沉久了,这才明白能得到颗这样的真心是多么难得可贵。
祥嬷嬷在旁附和着。
当年京中翟万山也是有名的公子哥,哪里想着竟看上个扬州瘦马,不惜和家族闹翻也要娶进门,后来更是去了福建参军,远离京都。
太皇太后想起了往事,低声呢喃道:“这样的人,要不大忠要不大奸”
当年翟万山在京里闹的这一出,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人满身的逆骨和一腔魄力,这样的人在如今手握重兵,太皇太后不得不防。
先帝爷说过,翟万山这样的人,便是大忠,他忠的从来也都不是宇文皇族,而是天下百姓,是他自己心里的信念。
太皇太后期盼着先帝爷没看错人,忠于百姓便是忠于宇文氏,只要他是个忠臣,那她孙儿的南疆便没有后顾之忧,可只怕看错了人。
如今的朝堂一点风雨都经不住,她老了,沈辅也老了,朝堂上的人马虎视眈眈,宗室动荡,皇帝根基不稳,若要整顿朝纲,还要三年。
这三年,一点可能都不能有。
“到底是南方来的姑娘,怕是会不习惯北边的气候,你着人留意着,家里身娇肉贵养着的,进了宫也不是真叫伺候来着的,一丁点闪失都是容不得的”
祥嬷嬷心下知道,翟姑娘有闪失不打紧,可她这一闪失,背后动荡的是翟万山和翟家军。
秋荣又打外头走了进来,弯腰在旁说道:“曹公公回来了”
太皇太后微一沉吟,“人来了就带进来吧”
岁心的配剑被缴了,宫门口冷面侍卫毫不留情地将那把配剑与一众废铁之类的物件搁在一处,岁心一步三回头,那模样怕是与亲儿子分别也不过如此。
曹喜依旧是雷打不动的弥勒佛模样。
拂宁看的心疼。
这配剑是岁心十一岁的时候翟万山寻来给她的,她一向视若珍宝,如今也为了拂宁舍了。
迎着拂宁担忧的目光,岁心没心没肺地笑了声,她爹是翟家军中一名校尉,战死沙场后她便成了孤儿,若非翟将军收留她在府中陪着小姐,她哪有这么多年的锦衣玉食。
翟家待她极好,故而在得知小姐要进京的时候,她便决定要跟随左右。
曹喜皮笑肉不笑地看了眼咧着嘴的岁心,咳嗽了一声,“岁心姑娘,笑不露齿,这是规矩”
听了这话,不仅岁心的脸僵住了,就连拂宁的笑意都半露不露地在脸上,很是怪异。
曹公公换上监服后,越发阴气森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