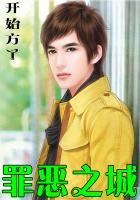“还没有吗?”
还不等家侍木高走近,木缈就急切问他:“这个地方的茶社,也没有哥哥的信息吗?”
木高摇了摇头,十分警惕地四下瞥了瞥街道周围,“小姐,今日天色晚了不适合再赶路,咱们就在这城里的客栈休息,明日一早我再去问问,如果二爷有消息...”他话还没说完,突然冲出一个人直直往木缈身上撞,木高反应迅速,一脚将来人踢出去老远,眨眼间就将剑搭上其脖子上,怒道:“什么人!干什么!”
突如其来的一记重击让路人蒙圈,躺在地上哎呦哎呦直叫唤,再睁眼一看时立马吓破了胆,“大侠饶命,我就是个过路的,刚才有狗追我,顾着逃命冲撞了大侠,还请饶命啊!!”
紧接着巷子里又冲出来一条狗,躺地上的人一听狗声浑身直打哆嗦,证明着所说非假,木缈将神情紧张的木高拉开,给地上的人赔了不是,二人这才进了客栈,“不要这么紧张,刚才只是个路人。”
木高不敢松懈,他的直觉再告诉他,自出花都之后,一直有人在暗地里盯着他们,“小姐,茶社寻不到二爷留的信息,实在是太反常了,咱们每过一个城地都要送一封信,却次次如石沉大海,下一个城地是浮岩城,因为生了疫情控制出入,不能再往前走了,两国的战场就在浮岩城外,若是让老爷知道我送你来这里,非得扒了我的皮不可,小姐,你既然不肯回去,那就在这里等二爷的信息,我明日再去打探一下。”
木缈没有反驳也没有同意,心里默默想着可能性,这一路走来,反常的事可不止收不到消息一件,譬如三番四次遇到蒙面人拦路,仿佛要下了狠手除她,在双方差距悬殊之时又有人暗地出手帮她,这两个不明势力纠缠斗了一路直跟着她二人到现在,不仅木高精神紧绷下意识将无辜路人当做歹人,她也很不安。
若是她的信根本就没送到二哥和杨叔子手里,那她不管等多久都是徒劳,浮岩城近在眼前,她的父亲和大哥就在城外,她不想被动的等,便对木高说道:“大约明日也没什么消息吧,不必再等哥哥回信了,我们今晚歇一歇,明日出发去找父亲。”
“可浮岩城瘟疫肆虐,因此出入戒严,怕是进不去。”
这一路上木缈也听了些许闲谈,朝堂对浮岩城瘟疫重视不已,亲自派了二位王爷前来探看管制,这其中一位便是她想躲的人,若是进了边境小城,指不定就遇上了,此番戒严甚得她心,于是回道:“不必进城,我们绕路。”
等见到父亲得了他的同意,那之后,就再无瓜葛了。
————
司默坐在紫檀木椅上微低着头,一只手握成拳抵在嘴边抑制着汹涌的咳嗽,等到胸腔里的冲动散去,他才抬头,目光又停在桌子上散开的一大堆信上,重新拿起看到一半的信件仔仔细细读了起来。
等到看完,他才问身边的许攸:“这信上所言的方法,那些异士们有几分把握?”
“回王爷,有八成把握。”
司默闻言不语,习惯性食指敲着桌子,闭眼想着八成把握,他到底要不要试一试。
八成把握,已经是很大的成功概率了,且那些结论都是名声在外的修士得出来的,他命许攸将他们全困在一起,威胁他们的言辞也都很致命,这种情况下得出的八成,是真金白银的八成!
可即使这样,事关能不能让他的小木重新苏醒,即使有一点点的不确定他都不想贸贸然行动,那修士的信上所推测的结果,木缈的突然觉醒只是暂时,觉醒原因很有可能在于人,若想让其彻底消失,让那副躯体彻底为清绝一人所用,那就得除掉支撑着木缈觉醒的人。
他不确定这个人是谁,是木将军和二位兄长?还是那个季涯?或者以防万一,全部除掉?
他要不要下杀心?
这又是一次赌博,赌错的后果无法挽回,他在心中举棋不定,出神的时间也长了。
“王爷,”许攸站在一旁提醒:“属下刚才得到消息,夫人一行已经出了安平城,往浮岩的方向来了。”
司默点了点头,吩咐道:“继续派人跟着,照她的性子,很有可能越过城直接去段安营寻将军,最近路上不太平,多派点人手保障安全。”
二人的谈话还未完,房门却匆匆打开,司昭面上似有怒,手上拿着召纸,急匆匆走到司默身边,依旧激动地说道:“那帮大臣都是干什么吃的,由着父王下这样的旨意!”
“怎么了?”
“父王要用虫囊对付战乱,那三国再怎么难缠也是小喽啰,父王竟用虫囊对付!那可是虫囊啊!三国才多少的人?!这样下去死伤无数,要是因此又给了岐国话头借由此事开战,那天下的百姓又要开始受苦了!”
司默知道五哥心善,可有些时候心善反会导致不好的结果,便劝说道:“那敌军怪异顽固不堪,将士仿佛不死之身,加上我军又受疫情影响士气受挫,速战速决也是常情。”
“可我都跟父王上书过了,我们押了不死将士,可以尽快查明缘由,这其中必然有什么阴谋,如果不查清楚就动用虫囊实在是下下策,况且疫情控制住了,父王为何这么着急?不仅要虫囊,竟然突然间就让星儿去和亲,那召国太子可还是个小儿,他怎么能如此顽固?”
这句和亲,让静立在侧的许攸身体一僵猛然间眉峰紧皱,下意识蹦出一句:“王爷!”
之后求证的话被他狠狠压在心里,在两人看过来的瞬间重新整理好表情,“王爷,属下先告退。”
出了门他都未发现,自己用力紧握着双拳,脸上神色吓人,脑子里回荡的,全是出发前夜时那句,许攸,你亲亲我吧。
他怎么这么迟钝这么愚笨!明明知道她的不对劲了,为什么就没有主动问问她?
为什么不问她!
房内的司昭依旧十分激动:“老七,芙凌演算过,这场瘟疫来的极诡异,那个被压住的敌军身上有邪纹,明显是被人试验练出来的,偏偏出现在比邻的三国,你觉得会是什么目的。”
“为了虫囊!”
“对,这么锲而不舍一再挑衅,很有可能是故意想激我们放虫囊,那些士兵虽然古怪,却并非刀枪不入的不死之身,或许背后的人就是要让他们做牺牲品,以此来测测这些试验品是否抵挡的住炎国的虫囊,若是抵挡得住,那他们的目标就是炎国了。这太显而易见,分明就是岐国的计谋,父王怎么还能中计呢?!事不宜迟,我得回去亲自阻止父王,所以浮岩城交给你了,芙凌知道制药一事,让她留在城里帮你,你们等着我回来。”
司默知道五哥决定的事情无法改变,也没再多做劝说,只接了管疫一事,打点了回程的准备,亲自将五哥送出了城。
一连十日都一如往常,却在第十日夜里,三国的敌军不约而同发了狠夜袭,攻击一波比一波生猛,等到暂时性压制住袭击时,双方都受了很大的创伤。
木缈到营的时机实在是不好,她拿着木府的印进了营门,却见营门一战车一战车往回拉着或战死或受伤的将士,每一个营兵脸上,都带着彻夜厮杀之后的疲惫,没人往她这里看,没人注意到她。
木高站在她身边,瞅准时间拉住路过的一个胳膊受伤的小兵,连忙问道:“这位兄弟,请问将军现在何处?可否带我们去见他”
突然而来的拉扯让小兵一个激灵,戒备的眼神打量了又打量,才摇了摇头,“将军正忙,不见外人。”
“我们不是...”木高剩下的话被木缈止住,眼神示意不要打扰对方,等放了那小兵离去之后,她扫视一圈周围的伤员,略微叹了口气,卷起身上的衣袖,加入了救治的队伍中。
木缈幼时跟着父亲常居在战地前线,学了营地大夫救伤的技能,并且帮着大夫救治,直到战后回了花都,如今此番情况下,她便自然而然去帮伤员治疗。
行医的大夫见她是个熟手,也没有过多疑虑就让她跟着,时间倏然而逝,等到伤员几乎安顿的差不多时,她才微微喘息歇息,远视的目光不小心瞥进了死人堆,正欲移开眼时,却被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揪住了眼睛。
木缈的心猛然间敲起了惊慌失措的鼓,她盯着那个人堆里被层层压住只露出的半截手臂,紧张到下意识干咽了一下口水,随即缓缓起身向死人堆走去。
越来越近,心中的害怕也越来越浓,终于走到了眼前,她的手颤抖着要去触碰那半截手臂,那手臂衣服上的纹理她再熟悉不过,那是她家的鹰爪家纹。
这个手臂的主人....是谁?
就在她快要触到的同时,身后响起一声讶异的询问:“小缈?”
这声音让木缈瞬间清醒,转头去看,竟是斐济。
“斐大哥,”
斐济脸上的疑虑变成惊喜,却又转瞬即逝,他快步走上前,同样看见了吸引木缈的东西,便不着痕迹上前挡在木缈与那死人堆之间,“你怎么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这里刚打了仗太危险,你来干什么?”
“我来找父亲.”
“走,我带你去见将军。”
这简单的一句话将木缈从害怕中拉扯出来,她听到父亲无恙一颗心也落了地,跟着斐济进了主帐,穿过一堆将首,看到心心念念的父亲坐在桌前,正仔细看着桌上的地图。
“将军,小缈来了。”
木将军闻言抬头,这久别之后的一眼竟又让木缈心惊胆战,她的父亲,怎么能如此苍老?
布满沟壑的脸上毫无血色,鬓角的头发灰白,面上裂开的两三个小口子虽然涂着药,却让他更显脆弱和不堪一击,木缈一瞬间睁大了泪眼,这怎么能是她记忆里永不倒下的父亲?
“爹爹,”她的声音控制不住地发抖。
将军越过桌子上前,一把抱住了她,又是激动又是担忧:“缈儿,你怎么来了?!”
等到大帐内只剩了久未见面的父女两,木缈来时打算说的话已经不忍说出口了,只想尽可能的安慰父亲:“七...殿下他奉命来浮岩城管制瘟疫,我也跟着来了,想到浮岩城离得父亲近,我想念担忧父亲,所以私自跑来看看。父亲脸上的伤是怎么弄得?”她心疼地用手去触摸,却被将军避开,“缈儿别动,这是瘟疫之症,虽然有药止了传播,还是不动最好。”
木缈暗自使劲压抑着自己,却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木将军只得反过来安慰:“为父好好的哭什么,不要哭,花了脸就不好看了。”
“大哥呢?怎么不见他?”她只得扯出一个笑脸,来转换自己的情绪,没想到木将军脸色一沉,握着木缈的手微微发抖,嘴角动了动,半晌才说道:“晨儿他,战死了....”
木缈都忘了自己是怎么从段安营出来的,那句大哥战死的话让她失魂落魄,抱着父亲哭的几乎晕过去,直到载她的马车往浮岩城驶去时她都在浑浑噩噩。
大哥木晨大她十岁,所谓长兄如父,那些父亲远在边关的日子里都是他给了木缈父爱,兄妹关系如胶似漆,直到得了官职接了父亲的职责,他说木家他来当责,让二哥与她随心所欲生活。
然后他真的为他们撑起了任性的天,却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一晃三四年未见,再见时,却只得到了他战死的消息...
往日的美好通通涌入木缈心头,让她在车内嚎哭不止,却不知道外面,那伙跟了一路的黑衣人又缠了上来。
马车突兀一个急转,接着就冲向阴沟,木缈还没来得及确认发生了什么,一阵巨大的震荡传来,撞得她直晕了过去。
“阿缈...”
“阿缈...”
谁,谁在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