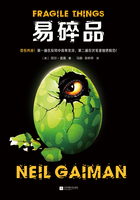一
当付文强和林晓晴躲在树荫底下讲故事时,宣传委员赵红芳正满世界找他。
其实,她找付文强也只不过是为了告诉他,刘老师叫他尽快把纪律保证金收上来。按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况且付文强早就知道了也说不定,然而赵红芳就是这样的人,哪怕是针眼那么大的一点事儿,她也会一五一十地认真对待。
对于二班头付文强,赵红芳是真正很佩服的。虽然他常常不声不响的,却从不把工作丢在一边;虽然他常常是人群中的一员,却从不随波逐流;虽然他常常会带着些忧郁,却从不故作深沉地说“我想我是海”。
曹菲虽然身为班长,但除了学习之外却再没有什么关心的事,也许老师们会觉得她好学,但赵红芳却觉得那叫不负责任。
相比之下,付文强就要好上千百倍了,虽然他没有曹菲的成绩好,却知道来这里的任务并不只是学习,身为一名学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也还有许多事要做。
所以每次改选班干部时,赵红芳第一个要选的不是曹菲,而是付文强,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同学们,也对得起她自己的那张选票。
对于付文强的工作,她自然也是尽最大努力去支持。
这次也是一样,找不到付文强,那她就先帮他收了。本来,这事是不应由副班长来做的,当然也不应由她这个宣传委员来做,可班上就是这种情况,班干部很多,真正肯做事的却没有几个,久而久之,班里就多了一堆摆设。
正当她准备向教室走去的时候,却见谭华急匆匆地跑出来了。
“气死我了。”谭华看到她过来了,就抱怨说。经过星期天下午那次短暂的接触后,谭华见到她比从前亲热了许多。
“谁呀?”她心里知道可还是这样问。
“还有谁?”谭华说,“张国豪那个大混蛋呗,说别人哪能对得起他呀!”
赵红芳每个星期都走离谭华家不远的那个路口,所以对于她和张国豪的事也知道不少。
星期天下午,赵红芳看见谭华脸上带着些生过气的痕迹一个人在那里等车,就已经猜到是和张国豪闹矛盾了。不过这种近乎无聊的事,谭华不说,她也不问。
说实在的,赵红芳对他们俩都是有些看法的。谭华一个劲地赶时髦,把自己打扮得没一点儿学生样,而张国豪仗着家里有钱,整天大手大脚地摆阔,纯粹就是一个败家子,有一次学校停水了,他竟然用矿泉水洗衣服!
然而有看法归有看法,赵红芳并不会因此就故意疏远了他们。谭华回不了学校时,她依然会带上她,谭华开口跟她说话时,她也依然热情地回应。
“互相体谅一下呗,”赵红芳很笨拙地劝解道,“很多事忍一忍就过去了,顶两句说不定就会闹个天翻地覆……没准张国豪也有他自己的难处呢。”
“他会有什么难处?老爸是大款,老妈是太后,自己却是骑在爸妈头上的小皇帝,走到哪里都有一帮狐朋狗友跟着,我看他就是吃饱了撑的!”
为什么不管什么样的男男女女,走到一起后就都会闹个没完没了呢?莫非自从亚当和夏娃走进伊甸园的那一刻起,人类就注定会有这么一种苦难吗?赵红芳百思不得其解。
“你说,像咱们这么大就去说‘喜欢一个人’……到底应不应该呢?”赵红芳静静地沉默了片刻,终于开口问道。
谭华一听忍不住笑起来,在她眼里,昔日的赵红芳又重新出现了。
“你问的可真有意思,这要是让别人听了,不笑掉大牙才怪呢!”她说。
二
谭华跑出教室,都是让张国豪给气的。
课外活动时间,教室里人不多,有学习的也有玩的。
上一节是英语听力课,英语老师因为有事耽误了,下课时还没听完。她就把录音机放在了教室里,准备晚自习时接着听。
张国豪觉得谭华真是生气了,都已经有两天不理他了。他坐在谭华后边,上课下课不管怎么逗她,她都不吭声。
每次搬起石头砸在自己脚上之后,张国豪都要拉下他大男子汉的脸,低声下气向谭华赔不是,而每次赔不是,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回该怎么个“赔”法呢?
请她吃饭?恐怕除了满汉全席之外也快吃得差不多了;请她看电影?她肯定会找出一百个理由来拒绝的;继续送东西?那又该送什么好呢?
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就难以牢牢地抓住爱情,这是张国豪一路“赔”下来的最大心得。
想来想去,想得张国豪头都大了,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一时心烦,张国豪见英语老师的录音机还在讲桌上放着,就从书包里掏出盘磁带来问同学们:“哎,这个,你们听不听啊?”
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少年,正处在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让他们整天埋头在死气沉沉的教室里的确有些残忍,所以很难找出几个不喜欢听流行歌曲、不喜欢追星的。
张国豪放上磁带,刚听了没半首歌,冷不丁发现谭华正在瞅他,于是马上跟着录音机里唱了起来:你知道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你的态度我不能平衡……
他对着谭华唱了半天,把谭华气得一扔课本,起身跑了出去。
好几天来,谭华总算对他有了一点表示,尽管只是瞅了他一眼,那也总比不理不睬强。张国豪顿时心花怒放,正要跑出去追,刘老师就迈步进来了。他一听到教室里的歌声就把脸沉了下来。
刘老师心中的流行歌曲是《十五的月亮》,是《小白杨》,是《我的家乡沂蒙山》,而对于时下满街满巷都在传唱的流行歌曲却从来都看不上眼,因而,他也很讨厌学生们听这种格调不高的东西,这叫作“恨屋及乌”。再说了,刘老师一直都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尤其还是高中的学生,正处于考大学的关键时期,只要不是在学习,干什么都叫“不务正业”。
刘老师在讲台上威风凛凛地站了会儿,也没人理睬他。他又居高临下环视了一圈,然后问:“这是谁放的歌?”
同学们各自静静地坐在位子上,谁也没有搭腔。张国豪抬头看了刘老师一眼,没搭腔。
“谁放的?”他又问了一遍,声音大而带着怒气。
张国豪这才说:“我放的。”说这话时,人也未站起来。他是不会怕刘老师的,他知道刘老师也就有点吆喝两声的本事。
“我还当是它自己响的呢!”刘老师有些厌恶地看着他,“这么多同学都在学习,你放这种玩意儿多打扰他们?”
“什么叫‘这种玩意儿’啊?”张国豪不服气地说,“现在又不是上课时间,听听歌怎么了?”
“我说过多少遍了,这里是教室,不是歌厅!”刘老师的火气很大,里边带着一股浓烈的火药味,“教室是学习的地方,你想听歌我管不着,可只要别在教室里,别打扰了别人,你爱去哪儿听去哪儿听!”
“又不是光我一个人想听,干吗非要找我的麻烦?”张国豪指了指教室里的同学,“不信你问问他们,有谁不爱听了?”
“胡说!”刘老师的话里明显地带有一些激动的色彩,“你见有几个能一边听歌一边学习的?他们不愿说你你还不知好歹。再听听这些流行歌曲里唱的什么?今天你爱上我明天我抛弃你,全都是些低俗下流的东西!”
“你懂什么!”张国豪不屑一顾地说。
“我不懂你懂,”刘老师不愿跟他再纠缠下去,多说无益还惹一肚子气没必要,就说,“我没工夫跟你扯淡,你给我赶紧把磁带拿出来!”
张国豪背靠着后边的桌子,双手抱在胸前,不急不忙地说:“不拿。”
刘老师又问了一遍:“你到底拿不拿?”
“不拿!”张国豪依旧说。
“好,你不拿是吧?你不拿我拿!”
刘老师对于录音机知之甚少,连按哪个键可以停下都弄不清。没办法他就挨个按,费了半天工夫才拿出来,可估计那盘带子也被绞得差不多坏了。
刘老师拿出磁带来二话没说,气冲冲地甩门而去。
教室里的同学似乎都被吓住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一个个不声不响的,而这时张国豪却又重新放上一盘磁带说:“不让听我偏听,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有几个同学看不过去就劝说:“他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又是班主任,你就别跟他斗了。”
“你们怕他,我可不怕他,他年纪大怎么了?是班主任又怎么了?凭什么就可以不讲理!”
当然更多的人是替他说话的,这让张国豪的劲头更足了。然而新放上的磁带刚听了没两分钟,刘老师又进来了。
“还听!”他这一喊,把几个胆小的同学都吓了一大跳。
“这不是流行歌曲,这是世界名曲!”
“世界名曲有的是,你要是都听,咱这课还上不上了?”
“现在是课外活动时间!”
“课外活动时间也不能听!”
“谁说的?”
“我说的!在高二·一班,我说不能听就是不能听,不服气你可以到别的班去!”
就在刘老师提走录音机的那一瞬间,张国豪已经把手中单放机的音量开到震天响了。
三
江新也是高二·一班的一员,然而连他自己都觉得在这个班里是多余的。人们都倾向于把自己融入一个集体当中,说如果集体是一幢楼房,那么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块砖头;如果集体是一段道路,那么自己就是其中的一颗铺路石。可在这个集体当中,江新总感觉自己既不是砖头,也不是铺路石,甚至连粒沙子都不是。
上课回答问题时,怎么也叫不着他;每次要想从成绩单上找他的名字,最好的办法是从后往前找。平日里的各项活动,他也没有一样能拿得出手的。让他去打篮球,别人从他手中把球抢过去,然后投进篮筐了他还没反应过来;让他去踢足球他更不敢,一上场不让人把他当球踢了才怪呢;让他去唱歌,其结果顶多也是花很大的力气制造出一串噪音罢了。
在班里,哪怕是最没爱好的同学也会去交两个笔友,相互谈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可江新连交友信里要写些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硬要说他还有点儿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可以供大家逗笑了。
有一次刘咏波问他猪八戒的老祖宗是怎么死的,他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还是说不知道,周围的同学就哈哈大笑着告诉他是笨死的。
没分科之前,他和刘咏波就是一个班的,对于他的底细,刘咏波掌握地一清二楚。来到这个班以后,刘咏波也老爱拿一些有关他的糗事,不厌其烦地讲给同学们听,恨得他牙根疼。
就算到了现在的班里,他也依然会闹出一些不可收拾的笑话来。
刚开学的时候,天气还有点热,还有些蚊子,同学们都在宿舍里挂了蚊帐。全宿舍挂的都是白蚊帐,就长得特别胖的沈童一个人挂了红色的。江新看着看着就不由自主地哼起那首儿歌来: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睡着个白胖子。
正躺在里边午休的沈童听了立刻爬起来问:“你说谁?”
他说:“我说花生。”
沈童一听气得不得了,又问:“江新,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他说:“我一看到你这样就想起了花生,可我真的不是在说你。”
闹到最后,沈童差点儿气死,而周围的同学却差点笑死。
江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笨,他想他一定是还没有发育完全就被生出来了,明明是一句很正常的话,可一旦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完全走了样。如此时间一长,也就没有几个同学肯理会他了,吃尽了祸从口出的苦头以后,他也不敢再与别人主动搭话了。
上课的时候他一动不动地趴在桌上,老师讲半天课,他未必能听懂一句,就算听懂了也未必能记住。下课的时候还是一动不动地趴在桌子上,别人怎么玩都不会想到他,他也不敢自告奋勇去参加。他整天都什么事也没有,在学校里唯一的任务就是熬时间。
从小就有些智力缺陷的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们眼中的“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没办法,父母就让他上学,只要有一丝机会就绝不放过,说是在学校里总比在外边好一些,说不定将来还好歹能考上一所大学呢!
但是江新并不喜欢待在学校里,这里与他朝夕相处的只有冷落和无聊。刚一开始,为了打发时间,他就在桌子上转笔玩。心里盘算着,如果前头指向他,那他就是“蛋白质”,如果后头指向他,那他就不是“蛋白质”,可转来转去,总是前头指向他的时候多。他也总是生气,生那支笔的气,也生自己的气,渐渐地他就不再转笔玩了。
后来他又开始画画,用不到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去画一些小猫小狗小鸡小鸭之类的弱小动物。有时画着画着冷不丁被人从背后抢了过去,于是又会拿他取笑一番。
再后来他也不这样画了,干脆就拿着笔往课本插图上画,给男的涂上口红,给女的画上胡子,把人改成猴子,再把猴子改成人。
然而就在刚才,他却又因如此乱涂乱画被同桌臭骂了一顿。因为正当他画得起劲时,同桌怒气冲冲地过来一把把课本夺在了手中,他这才看清楚,那本书上面写的是同桌的名字。
四
月上柳梢头。
到中旬了,月亮也将近全圆了。明亮的月辉轻轻吻着大地,垂柳的疏影在风中微微摆动。熄灯铃打响一会儿了,沸腾的角角落落已经渐渐安静下来。
夜好静谧,宛如一潭微风轻拂下的春水。
张国豪又把谭华“请”到了老地方,操场北边第三棵柳树下面。
明朗月光下的谭华,即使是生着气,也依然楚楚动人。惹得张国豪又不禁想入非非,道歉之心也更加坚定了一些。
“找我干吗?”谭华嘟着嘴,明知故问。“给你赔不是嘛,每次都在这儿的。”
谭华“啧啧”了两声说:“谁敢让你张大少爷赔不是啊?你可别把本姑娘的阳寿一下子给折没了。”
张国豪不顾谭华的挖苦,说:“那天是我一时糊涂说错了话,我当时只是想跟你闹着玩的,其实在我眼里……”
“你爱夸谁夸谁,关我什么事!”
“当着你的面夸别人,这是我的不对,我也知道你想让我……”
“想让你去死!”谭华说完,转身就摆出一副要走的架势。
张国豪赶忙拉住她,说:“先别走啊,还有东西要给你呢!”
谭华一甩手说:“我不要,要不起!”
张国豪变魔术般从背后拿出一个精美的音乐盒,举在谭华面前,然后轻轻地打开,美妙的音乐顿时就荡漾开了。
音乐盒的中间是个可爱的芭比娃娃,随着音乐的响起,芭比娃娃缓缓转动着。在娃娃的四周,还有一圈七彩小灯,月光之下,一闪一闪的,煞是好看。
谭华一看到这音乐盒,就惊喜地叫起来:“哎呀,芭比娃娃!是不是金园礼品城里那个啊?”
“当然是了。”张国豪说。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啊?”谭华捧在手里,爱不释手,“全县城可就那一个地方有卖的!”
“我是谁呀!”张国豪得意地说,“怎么能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呢?”
谭华白了他一眼,说:“德行!”
张国豪在冥思苦想了好几天之后,终于想起来谭华曾经跟他提过芭比娃娃的事,于是他就发动自己的狐朋狗友全城搜索,最后才在金园礼品城找到这个。依蒙县不是时尚大都会,能搞到这个音乐盒,着实花了他不少力气。
不过看到谭华这么喜欢,张国豪心里也就满意了,于是赶忙趁热打铁说:“这回不生我气了吧?”
“谁说我气了?你配让我生气吗?”谭华一歪头反问道。
“那你为什么好几天都不和我说话?”
“不和你说话又怎么了,我就是讨厌你不行啊?”谭华说,“我问你,今天下午干吗跟班主任发那么大脾气?”
“心里烦嘛,你都不理我了,我哪还有什么好心情?”
“心情再怎么不好也不能跟一个老头子吵架啊,你以为你是谁?”
“遵命!以后再也不敢了。”张国豪嬉皮笑脸地答道。
谭华抓住他的脸狠狠地拧了一把,“你少在这耍贫嘴,赶紧回去睡觉了!”
五
月色很好,刘老师也睡不着。
想来今天的事也怪自己,不就是听听歌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无论如何也不至于那么大动干戈。或许换了别人也就过去了,可他就是看不惯张国豪那副纨绔子弟的样子,这种坏学生,如果不好好教训教训,迟早是个害人精。
经过这么多年的计划生育宣传,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子女少的好处了,再加上国家的严格控制,即使是农村,也大都超不过两个孩子了。孩子一少自然就都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加倍地宠着爱着。这样固然让孩子得到了更多的关爱与呵护,可同时也惯出了一大批小皇帝、小太岁。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到底是爱还是害呢?
刘老师在气愤之余,也感到了自己的不对,和张国豪闹翻事小,可作为班主任,在班里失去了人心则是事大了,他觉得今日之举有点得不偿失。
夜里睡不着,他想去男生宿舍外边听一听他们都在说什么。
男生宿舍外边静悄悄的,可里边却早已乱作一团,夜夜都是如此。
刘老师今天固然让人觉得生气,然而对于谈论他,同学们大都是没有兴趣的,在他们眼里,明星永远比刘老师受欢迎。
他们一会儿研究某明星做没做整容手术,一会儿又讨论某明星拍的三级片,翻来覆去都是一些无聊至极的话题,刘老师实在搞不懂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张国豪回到宿舍时,被刘老师撞了个正着。一想到白天的事,他就有气,不过自己终究是个老师。
“干什么去了?到现在才回来。”刘老师按下性子问道。
“去厕所了,我拉肚子。”
刘老师知道再问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就说:“赶紧回去睡觉吧。”
张国豪一进宿舍,床位在门口的刘咏波便问:“哟,又去会佳人了?”
张国豪给了他一拳说:“别说话,狼来了,就在门外边站着呢。”
一群说话的舍友听到这,便都不作声了,各自在心里头迅速地过滤,想想自己这一晚上说过多少“犯戒”的话,以便事先有所准备,免得到时候批评起来无言以对。
刘老师这时已经进来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睡觉,到明天谁要是在课堂上打盹儿,就给我小心着点!”
他的话刚一说完,宿舍里就响起了一连串的呼噜声。
“装什么洋蒜,不愿睡滚出去!”刘老师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
好半天,直到没声音了他才往外走,可这时的刘咏波却又说:“老师,帮帮忙把门带上吧,我没拖鞋。”
“没脱鞋还让我带门干什么?”
刘咏波裹着被子嘿嘿笑了两声,然后一本正经地解释说:“老师你弄错了,我是说没‘拖’鞋,不是说没‘脱’鞋。”
刘老师听完一甩手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