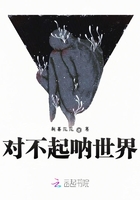“何止是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这次我们还必须要大把大把的花钱呢。所以我说这是一场比财力、比势力、最后还要比武力的一场灾祸啊!”
“爹!照您这一说,我们的命运岂不是要被县长来掌握着,我听说这县长是新来的,他真的敢判我们输官司吗?”
夏振东的神情似乎有些紧张,在他心里老天爷排第一、他排第二,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有被别人宰掉的危险。
“我料他不敢,这家伙如今上任已经快半个月了,可他一次照面还没有给我打,如果不是发生了这档子事,我非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夏啸天咬牙切齿的说道。
夏啸天这话还真不是吹牛,在紫云县他夏啸天是跺一脚紫云也要抖三抖的人物。他身为本地虎,多年经营的庞大势力无处不在,黑白两道翻手覆云,紫云商业经济命脉被他一手垄断,乡、镇士绅听他掌控,所以历任县长第一站都要来拜访他,如果惹上了他,他稍微使个绊子,可就够这县长喝上一壶了。
“大哥!我在县上听人家说这个新来的蔺同春县长是“东救会”的成员啊!恐怕会对咱们不利呀。”
“什么东救西救的,怎样对咱们不利?啸江,你说清楚点。”夏霸婆着急的问道。
“据说这个蔺同春是东北人,他所加入的东救会全称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这个组织里面有很多的共产党人,所以这人与共产党来往密切啊!”
“共产党?你说的可是当年成立农会要分我们土地和家产的那个红毛党,哎呀!啸天,这可怎么办啊,他们可是与我们有深仇大恨的呀!”夏霸婆急的捣着拐杖跺着脚说到。
五弟的一番话令夏啸天心里猛然的一惊,但是,他看到家人们脸上紧张的表情,他立刻平静了下来。
“他加入什么会的都无所谓,只要他是国民政府的官员他就不敢用红毛匪的那一套,另外他不会不掂量掂量咱们夏家是什么声望,到时候只要咱们再把他喂的饱一些,我就不相信他是一只不吃腥的猫。”夏啸天用自信的口吻说道。
此时的夏啸天突然意识到,自己必须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必胜的信心来,决不能让家人们失去信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我不隐瞒的告诉你们,我现在已经有百分之八十的胜算在心里面了。”夏啸天满怀自豪的说道。
“真的吗?”一家人听他这样一说顿时间喜形于色。
“快给娘说说孩子,这是为什么啊?你说了娘今晚可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咱们的仇人现在靠的就是驻军的保护,可是咱们知道现在的驻军是一支被打残的军队,差一点在前线就全军覆没了,无奈之下才撤到咱们这里休整,可现在他们已经恢复了元气,眼下战事越来越紧,鬼子们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还能在这里长呆吗,我料定过不了多久,也许是明天他们就有可能卷铺盖走人,哼哼!到了那个时候……。”
“对!这话说的太对了!”
“是啊!是这个理。”
夏啸天的话音未落就赢得了满堂喝彩,一家人顿时满脸的兴奋,压抑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
“哼!到时间他龙家失去了保护伞,他想跑我也绝不会让他跑掉,咱们给他来个关门打狗,当年他龙得水砍掉了我一只耳朵,现在我可要好好的“伺候伺候”他了。”
“儿子!听你这样一说,娘又可以看到刨腹挖心的好戏了。”
“对呀!娘…”
“O(∩_∩)O哈哈~……。”满屋子的人开心大笑起来……。
∽∽∽∽∽∽∽∽∽∽∽∽∽∽∽∽∽∽∽∽∽∽∽∽
“耗子!耗子,别睡了,快起来吧,龙家在发粮食呢,你去领回来。”
莲西村村东的一户人家里,一个女人正使劲的摇晃着床上睡着懒觉的男人。
而这个被叫做耗子的男人一声不应,呼的一下抓起被子蒙头又睡了起来。
女人急了,张口大骂道:“睡你妈那*呀!整天就是睡、睡,睡死你个赖种!家里都没吃的了,你也不管。”
女人越骂越来气,伸手哗的一下拽扔了盖在男人身上的被子,露出这男人的白屁股,这男人是裸睡。
床边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他手里边拿着一根小棍子,男孩用棍子朝男人的光屁股上打着,嘴里面学着母亲骂道:“打死你个赖种。”
“我日你八辈!老子睡会也不让睡安稳。”耗子急了,呼的一下子坐了起来骂道。
耗子原名姓江,叫啥名字没人知道,人们只管叫他江耗子。他活脱脱是一个老鼠精托生来到人间,这不但是因为他长着两个长长的老鼠牙,更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贼。
莲西村甚至整个莲花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贼。四十出头的他常年领着他的两个徒弟——哈巴狗朱宝瓶、癞皮狗石斛子,三个人勾搭成帮流窜在外,能偷就偷不能偷就抢,干尽了坏事。
喊他起床的这个女人是她的老婆小灵红。小灵红长的漂亮,白皮肤、大胸、细腰、大屁股。她原是县城怀月楼的头牌风尘女子。那一年耗子在外干了一桩“大买卖”。手里有了钱回来就包了小灵红。小灵红把他伺候的舒服似神仙。这耗子便就有了想法了,自己四十多岁了,也得娶个老婆生孩子留个种啊,死了有个哭丧的。
正好小灵红也有想法,自己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已经快过了吃“青春饭”的年龄了。这男人有钱,以后跟着他不会吃苦受罪,再说了也脱离了“万人骑”的苦海了。
两人的好想法一拍即合,这耗子掏钱给小灵红赎了身,她便跟着耗子来到了莲西村耗子的老鼠窝成了家。
被老婆掀被子叫骂的耗子眼看也难以睡成懒觉,便骂骂咧咧的起了床。
“晌午给老子烙些葱花油饼吃,天天给老子吃些啥呀,想害死老子你再找一个小白脸是吧。”耗子走出门的时候骂道。
“姑奶奶还想吃烧鸡卤肉呢,你给姑奶奶拿钱来,整天你鳖孙不在家……。”
∽∽∽∽∽∽∽∽∽∽∽∽∽∽∽∽∽∽∽∽∽∽∽∽∽∽
耗子来到村子的大路上,村里的人都来去匆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兴奋的表情,路旁的一片空地上,几台大火炉里燃着熊熊大火,铁匠们光着膀子满头大汗,黑红的脊背油光光汗闪闪,叮叮当当打造着大刀长矛。
一群手拿大刀红缨枪的巡逻队从跟前走过,虽然这群人衣服破烂,五颜六色的烂布条一缕缕露着肉,但他们精神饱满,神情庄严。更令人惊奇的是队伍里还有几个青壮年人。
自从那一天夏霸天引来抓丁的把村里搅个底朝天后,村里青壮年都跑光了,哪还敢呆在村子里,可后来龙召男一行来到了莲西村,从随行的任庆伟副官那里,乡亲们才知道了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壮丁征招计划,人们顿时明白了夏霸天的阴谋诡计,流着泪把他祖宗十八代骂了个底朝天。这几天一些胆大的年轻人才敢回到了村子里。
“老大!”
“大哥!俺两个就是去找你呢,真巧了。”
随着声音耗子看到两个贼徒弟哈巴狗和癞皮狗,他二人正朝自己走来。二个人手里面也拿着一个大口袋,也是要去龙家领粮食去。
大徒弟朱宝瓶长的是小个、小头、黑脸皮,特别是尖脑袋、大嘴巴、宽下巴,嘴脸看上去和狗一模一样。所以人送绰号哈巴狗。这二徒弟石斛子也长着狗一样的脸,只不过他头上长了一头赖疮流着脓水,所以人送绰号癞皮狗。
三个人相遇嘻嘻哈哈一通后,便一起去领免费的粮食。
早些日子大栓兄弟的武艺班在外打把势卖艺,就在班子回到村子里的第三天。这三个贼也从外地回到了村子。
三人看到了村路口的那棵大槐树都激动的流了泪。倒不是因为几个月来想念家乡而流泪,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不可能活着回来了。
就在今年过年前,三人流窜在冀州干了一件大案,杀了一家金店掌柜的全家,没想到失手被逮进了大狱。眼看着就要等到秋天行刑砍头,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日本人打了过来,监狱的看守跑了个一干二净,三个家伙就这样捡了条命。
一路上三人嘴里面不停的念叨着,感谢着日本鬼子八辈祖宗,同时还不忘重操旧业,持枪抢了一群逃鬼子兵的商人家眷。
“到家了大哥,你回家可以大干嫂子了。”两个徒弟嘻嘻哈哈开着玩笑。
“干个毬,谁知道是不是又跑回老地方浪去了。”
耗子一边骂着一边又说道:“咱们在家待一阵子避避风头,等过一阵子咱们再出去大干一场,趁现在世道乱正是咱们大显身手的时候。”
人家大栓弟兄们每逢回村的时候,乡亲们看见了大老远便围了上来,流着泪拉着手问候着,一大群男女老幼一直跟到家里面,这时候李老太全家人烧水倒茶,院子里总是围的满满的,乡亲们听着大栓兄弟讲着外面的所见所闻,欢快的笑声如同潮水般阵阵响起,一派派情深深意切切温馨浓厚。
这三个贼回了村没人搭理,村里人见了老远躲着走,实在躲不开只好硬着头皮走来。
“抽烟!抽烟。”耗子拿出哈德门香烟,满脸堆着假笑上前让着烟。
“哎哟!不行,我戒了,咳嗽。”
或者说:“不了,我只抽这个。”人家拿出旱烟袋杆。然后赶紧扭头走过去。
要是实在抹不面子手里接了烟卷,看着他三个人走远了便骂道:“抽,抽个你娘的屁,一股子血腥味。”
然后便把烟揉碎扔的远远的。
∽∽∽∽∽∽∽∽∽∽∽∽∽∽∽∽∽∽∽∽∽
莲西村的地势两边高中间低,三十年前夏霸天炸开山洪道,山洪水夹杂着泥浆滚石奔涌而下,这可苦了村子中间的住户,全村受害的七十三户人家,基本上都住在这里,龙得水的家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是从龙得水老院旧址向南望去,寸草不生的山洪道痕迹依旧清晰可见,乱石黄泥斩木摧房威力无比,许多人家满门遇难尸骨难寻。
此刻,龙得水老院旧址旁黑压压人头攒动,人山人海熙熙攘攘。莲西村的男男女女以及莲花镇闻讯而来的乡亲们把这里围的是水泄不通。
“招魂台”奠基仪式隆重开始。
伴随着“噼噼啪啪”鞭炮炸响,十四班国乐队哀乐齐奏,十八铳招魂炮震耳欲聋。霎时间,莲西村众乡亲齐刷刷跪倒在地,香烛腾烟纸钱灰飞四扬,哭亲人悲声震天痛断肝肠。惊天地泣鬼神招亲魂回归故里。
“今造招魂台,招魂回故乡。亲人野孤魂,从此能安祥……。”老秀才叶殿卿苍凉悲壮的声音响起,如泣如诉。
众乡亲泪雨纷飞,哀哭啼号声中黄土飞落,基石入土。
“济深啊!你听到了吗!为妻在呼唤你啊!几十年来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济深!你转身就走,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给为妻留下啊!……你知道我有多么后悔吗济深……,你的冤魂在那里啊济深!你可以回来了呀!你看看为妻吧……。”
李老太放声痛哭着,几次都昏厥过去。
“娘!…”
“姥姥!…”
秀芝和两个孩子拉着她的左右手臂心痛的哭喊着。一家人悲痛欲绝。
几十年来,每每想起那个那个凄惨的夜晚,李老太的耳边顿时就会响起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声,她的心立刻间就会被一道道的闪电撕的粉碎……。
“咚、咚、咚…”屋外瓢泼大雨中传来一阵剧烈的敲门声。
“济深叔!济深叔……。”有人在急促的呼喊着。
她看到丈夫忽地从床上坐起。“济深!”她的心猛然一紧,伸手紧紧抓住丈夫的手臂。
“我去看看。”
丈夫骨碌从床上下去,抓起衣服披在身上,“吱呀”一声屋门被打开。随即一股凉风夹杂着雨水扑进屋里。
“济深!”未及她递过蓑衣,丈夫已经消失在瓢泼大雨之中。
一道闪电划过,随即惊雷炸起,她看到大门口丈夫正和一个人焦急的说着什么。一股不祥的预兆顿时涌上她的心头……。
“济深!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望着紧张披着蓑衣的丈夫,她连声的问道。
“没事!不要担心,得水的父亲病重了,我过去看看,很快就回来了。”
突然间,即将出门的李济深回过头来说到:“孩子他娘,你先不要睡,照顾好孩子们。注意听外面的动静……。”
那时的李老太做梦都想不到,这将是她和丈夫最后的一次话语!
“济深!……”她担心的呼喊着丈夫,可她听到的只有那震耳的雷鸣和瓢泼的大雨声……。
而那个时候,焦急行走在雨中的李济深万万没有料到,这将是他今生最后一次踏出大门。
就在刚才,龙得水惊慌的告诉他,为了给病重的父亲抓药,他深夜从城里里回来的时候看到夏霸天领着一群家丁上了山。倾盆大雨的黑夜他们上山一定有什么阴谋,但是他们二个人万万没有料到,这里面竟然是罪恶滔天的阴谋。
“得水!你在山下守着,我上山看看,万一有什么意外,你赶快通知乡亲们。”
“嗯!济深叔!您…保重啊!”
……李老太永远不会忘记,当那划破雨夜的枪声从山上传来的时候,她顿时惊呆了,她发疯似的冲出屋去,紧接着那急促的报警钟声冲击着她的耳膜。
“济—深—”……。
她惊恐的呼喊着丈夫的名字,夜幕中,她的声音被****淹没……。
∽∽∽∽∽∽∽∽∽∽∽∽∽∽∽∽∽∽∽∽∽∽
“父老乡亲们!”刚刚痛哭后的龙召男嗓音嘶哑沉痛的说道。
“遵照我父亲的意愿,今天我们在这里建造招魂台,沉痛追忆我们的亲人。当年他们惨死在夏霸天的毒手之下,几十年来,亲人们尸骨难寻,孤魂野鬼四处游荡。怎不令我们心肠揉碎。苦难岁月恶人横行,善良人的生命就如同草木般的薄脆。但是从此以后,这座招魂台就是我们莲西无辜亲人的灵位,上面将会铭刻着他们的名字,我们每年都会在这里祭拜他们,他们的在天亡灵将得以告慰!”
“诸位父老乡亲!”召男突然间提高声音大声宣布道:“我龙家已经决定,择吉日在此重建我龙家新居,我们龙家将会和乡亲们朝夕相伴,生死一起。不报这血海深仇,我龙家誓不归去!”
“为—亲—人—报—仇—雪—恨—!”随着一声铿锵有力的呼喊声响起,霎时间,排山倒海、山崩地裂般的高呼声响彻云霄……。
“我的娘啊,看这劲头夏啸天这回可是要完蛋啊。”远远站在人群之后的耗子低声说道。
“是啊,我好兴奋啊,想不到咱们这次回来还能赶上一场好戏看。”徒弟哈巴狗说到。
“太好了,到时间趁乱咱们就可以到夏霸天家搞些好东西了,那家伙可是富得流油,够咱们吃喝一辈子了。”徒弟癞皮狗一边说着一边摩拳擦掌,似乎现在就要大干一场。
“哎!先别说话,看,他们在干嘛呢?”耗子摆着手说到。
他看到人们都争先恐后向前边挤着,纷纷咬着手指头。
“啊!靠!他们在咬手指摁血手印呢,今天这粮食咱们可不是白领的。”哈巴狗惊叫着说道。
“我晕了,我可不咬手指,多疼啊!”癞皮狗吓的翻着白眼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