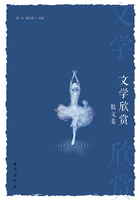答长沙《晨报周刊》孙魁您在《读好书的时间》这篇文章中说:“我会看到无穷无尽的小说,我每天都要扔掉若干本小说,我倾向于保留那些完美、接近于完美,或者至少表现出达到完美的志向的小说。”抛开批评家的身份不谈,单纯作为一个热爱小说的读者,迄今为止,大量的阅读小说的经验给您带来了什么?那些值得您保留的小说中,所谓“完美”或“完美的志向”指的是什么?很长时间里,读小说对我来说就是工作,包括读大量很烂的小说。无论是作为编辑还是作为批评家,在阅读时都是要负责任的。当我作为批评家或编辑说这是一部好作品时,意味着我做出了某种公共判断,期待着共鸣和回应。所以,我很喜欢你的这个说法,“单纯的热爱小说的读者”,或者换一个说法,任性的、享乐主义的读者。我承认,在工作之外,我就是这样一个读者。而且我不得不说,这样的读者其实不像我在那篇文章里讲的那样总是拿着尺子考量完美不完美,那还是一个批评家的话,在私下里,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喜欢什么样的书,所以,这就是隐私。在隐私中,你悄悄地扩张自己的经验,体验你真正感兴趣的可能的生活。
有一个作家是我个人很喜欢的,美国的帕拉尼克,他关于小说说过这样一些话:“电影,或是音乐,或是电视,都必须有某种节制才能播放给广大的观众和听众。其余的大众传播形式制作成本又太高,不能冒险只提供给有限的对象。但是一本书印刷和装订都很便宜,一本书就像性爱一样私密而你情我愿,书本需要花时间和力气去吸收——也给读者各种中途罢手的机会。事实上,只为肯花心力去看书的读者,少到很难把书本称为‘大众传播媒体’的地步,可是在忽视中带来的是只有书本才有的自由。如果一个说故事的人决定写一本小说而不是电影剧本的话,那你就要好好开发利用这种自由。否则,不如去写电影剧本,去写电视剧本,那些才能赚大钱。可是,如果你希望能有去到任何地方,谈论任何事情的自由,那就写书吧。”
这个家伙说得真好,我不能比他说得更好了。您在题为《为小说申辩》的讲演中阐述了读小说的理由,比如小说“提供的不是对世界的一般正解,而是个别的理解和看法”;小说提供了“理解他人的真理”;小说“在死亡的终极视野中考验和追究生命”。这里的“小说”也包含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学么?说那些话时,我心目中想的其实只是通常所说的“纯文学”,所以我很高兴你提醒我小说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学。我必须承认,类型小说也是我们理解自我、世界和他人的重要途径。比如很多人会用金庸某本小说里的人物形容自己或别人,也就是说,他读了这本小说,然后他借助小说的意象自我表达。但是,正如“类型”这个词所指的,不管一本类型小说的情节多么复杂,它的内在逻辑其实是简单和清晰的,是对世界和人的一种简化的分类,它让我们简单地明了地想象世界和人,当然,我们喜欢这种简单,不累,但是你知道,你不能真的按照武侠或言情小说去安排生活,那你就成了堂·吉诃德了,那部小说正是对骑士游侠小说的嘲讽,正如《包法利夫人》是对言情小说的嘲讽。《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这样的小说,志向不在于简化,而在于让我们更为贴切、真实地感受生命。长久以来,读者被灌输一种理念:纯文学才是文学,纯文学才是值得尊敬的。而其他的类型或作家,比如安妮宝贝、郭敬明,他们在市场上是成功的,但他们的作品,在批评家甚至读者心中,也仅仅具有市场所赋予的价值而已。但您曾说:纯文学是一种建构,它并非自然之物,它是中国现代以来一系列争执、权衡、机遇和选择的结果,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全景中它是一种罕见的例外。“纯文学”神话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文学的常态应该是什么样?类型文学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或者说类型文学孵育了什么?我相信,文学的常态是,所谓的纯文学总是少数。至于纯文学是否值得尊敬,那么,至少自现代以来,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比如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时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很火,读者比鲁迅多得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他挣的钱大概远超郭敬明,据说一本书就可以在北平买一座王府。但是,我们现在很少记起张恨水,可你还记得并尊敬鲁迅,这两个作家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我所说的“罕见的例外”是,我们曾经完全取消了类型文学,以至于在很多人眼里,类型文学是无可置疑的新事物,其实只是对他们来说是新的而已,类型文学旧得很,比纯文学旧得多、古老得多,或者你也可以说,类型文学更深地植根于某些基本人性,而纯文学,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的产物。就世界文学而言,在很多地方,大众阅读的主流是类型文学,但纯文学通常有更高的文化地位,因为人们意识到,纯文学所体现的志向不能被消费和市场这单一的价值取代,它关乎我们的存在,关乎我们作为现代人的一系列内在疑难。当然,纯文学和类型文学的区分在我们这里常常是很随意的,常常不过是门户之见,比如安妮宝贝,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把她算作类型或通俗文学,她比很多所谓纯文学作家更具内在性。
过去是纯文学霸权主义,把类型小说全部剿灭,现在又有网络文学或类型文学霸权主义,认为纯文学应该完蛋。我想,文学又不是打仗,不是非得谁灭了谁取代谁,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价值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一条街上开湘菜馆也开粤菜馆,这不是很正常吗?您如何看待官场小说?现在的官场小说越来越有一种技术化的倾向,有的官场小说干脆打出这样的广告语:当官是一门技术活。您认为官场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如何才能走得更深更远?我根本不认为它能走深走远,走深走远了就不是官场小说了。官场小说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晚清时就有黑幕小说,但现在的官场小说比黑幕小说还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它们至少还认为那是怪现状,需要揭露使之现形。而现在的官场小说,常常是对怪现状习以为常,津津乐道,那不仅是“技术化”,而且是完全抽去了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当然,很多人爱看,他们本来也没把这种书当小说,而是当成人生教科书,那就祝他们好运吧。让我们来说说读者吧。有了微博之后,你很容易就可以查到人们的阅读状况。我认为值得信赖的普通读者(他们不是作家、书评人、批评家或出版人,但又能够保持对小说的长期、大量的阅读并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寥寥无几。就您的观察而言,是不是也存在这种状况?您心目中小说天然的读者是拒绝承认生命和生活只有一条路、一种表达的人,不愿让精神僵化的人,这种天然的读者是否是稀缺的?这是否也是中国文学所遭遇的困境之一?有一个词叫“理想读者”,就是我说的那些人。这样的读者在哪儿都不多。但正是这些不多的读者维持着一种文化、一个文明的敏感和活力。这样的读者需要培养,包括通过学校教育去培养。但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恐怕是无助于阅读的。在欧洲,一个中学生毕业时已经读了很多本国文学的基本经典,他的感受力得到了充分的培育,而我们的中学生大概顾不上这个。读者也是需要成长的是么,从小时候热衷的武侠、冒险、爱情小说慢慢过渡到一些更具有精神特质的小说,也可以说是阅读起来更有难度的小说?很多人可能一直不成长,到老他对世界和人生的想象力都限于武侠或言情。当然,这也没什么,他一样可以过得很好。但我想,到你三十岁、四十岁、五六十岁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认为,这个世界比你预想的丰富和复杂,并对此好奇,于是你就面临“难度”。关于小说,我的一个热爱小说的朋友的建议是,读经典就可以了。她的意思是读那些公认的、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作品,这样不至于浪费时间。对于这样的建议,您怎么看?呵呵,这是个好建议。我很想知道这位朋友在读什么书。经典也是不断生成、不断变化的:马尔克斯还活着,他的书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经典了。而有些所谓的经典,除非做学问或找罪受,谁也不会去读。就我个人来说,我宁愿去发现我自己的经典。说到底,读小说不是吃饭,不是任务,是一种活跃的、充满好奇和热情的心智活动,是一种精神的探索,这使我们注定对新作品怀有兴趣。
20世纪80年代,是很多作家心目中的黄金时代。他们的作品被广泛传播,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你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阅读氛围?那时很多人读书,现在人不读了,因为有更多的事可忙。那时很多人认为,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价值值得追求,现在可能大多数人认为只有一种价值,就是成功。就阅读而言,我们大概不可能回到80年代了,那时随便一个大学生都会买一堆海德格尔或尼采,那也是异数。但是从80年代到现在,阅读人口和阅读习惯的衰退还是惊人的,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比不上很多国家。这关乎中国文化的长远气运,不可等闲视之。微博时代,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直接面向作者发表自己的评论。而且网络时代的阅读也自有其特性,比如碎片化,比如阅读介质的变化,电子书日渐流行。这会对文学的未来产生什么影响?未来怎样,我不知道。我们会预测未来天气不好,比如多雨。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准备雨伞,不是非得淋雨感冒得肺炎才是顺应未来。港台与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作品在大陆出版的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的语言与大陆的语言是有差异的,大陆一些作家和读者对台湾作家骆以军和马华文学代表李永平提出批评,认为他们最基本的语言关都没有过。您如何看待这种争论?这些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汉语是分途发展的。也就是说,港台海外也在各自的条件下发展着汉语,这使得不同地方的汉语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我编杂志时,编辑常常忍不住要修改港台作家的稿子,因为很多表达不合我们的习惯。我说,不要改,把人家改得和我们一个口音了还有什么意思?庞大的、人口众多、地域分布广泛的语种都有这个问题,印度人的英语能把英国人气死。这种差异也是一种语言的宝贵财富,其中包含着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你是否喜欢这种差异,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也可以想想:我们只剩下普通话,把方言都取消会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语言都会失去一些很宝贵的东西。所以,关于这个“语言关”,我看还是慎重一点好,别轻易把自己当成把关的人。汉语属于所有说汉语的人,人家要那么说那么写,怎么就不可以?就你是正宗,说得好说得对?大家都说得太好太对,这个语言也就没有活力了。莫言获得诺奖真的是“中文的胜利”么?要知道,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依据的是经过翻译后的莫言,这是不是只能说明“中国故事的胜利”?您觉得莫言得诺奖最终会对中国文学产生什么影响呢?如果不是用中文,莫言大概也不会这么讲中国故事吧?各种文化和语言通过翻译对话和交流是文明的常态,我们也应该以平常心看待它。至于莫言获奖的影响,大家已经说了很多,这种对影响的预测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的愿望,那么,我最大的愿望是有更多的中国人爱读书、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