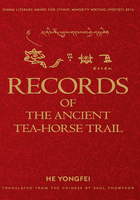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您宽容地认为这个时代的语言(比如一些流行语)生产是民主、平等的,但在另一篇报道里,也隐约说起当下公共语言和价值维度的荒凉。您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应的,文学的位置和意义又获得了怎样的变化?我并不奢望一个语言的“理想国”。就汉语而言,我们可能要长期承受某种巴别塔状态,语言不抵达理解,而是造成分裂。这很痛苦,但也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简单的办法难免要强制,一种声音覆盖所有的声音。
语言有一个困境,它用于交往,发自或大或小的“我”,这使它成为一个政治场所,区分你我他,诉诸权力、意志、暴力,看谁的声音更大、更高。在一个世界公认说话嗓门特别大的国度,一种宽容、理性的声音是非常困难的。但文学的语言是特殊的,它主要是说给自己,你看《诗经》里的那些诗,特别是《国风》中,大多是旷野无人、深夜无人时唱给自己听的。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自省的语言,内倾的而不是外向的,有内心深度,力图准确表达自身经验。文学的语言不依靠权力。相反,为了杜绝作者或说者的骄横,它甚至要约定虚构:那些话不是我说的,属于人物,作者有一种深刻的谦逊。
这样一种语言,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少,它谦逊、低调,但它捍卫着人类的精神生活。
所以,就文学来说,语言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民主、是否平等。那种试图在文学中把个人的声音与大众拉平的努力,是一种可怕的、不顾常识的文化民粹主义。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我们都需要自我交谈、自我倾听、自我认识的语言。我从来不认为文学语言的第一要义是美,当然不是,而是真,那些精确地、不可移易地表达了人类经验和精神之复杂、之疑难的语言才是美的。这次在广州采访的其他作家(马原、阎连科等)都单纯地捍卫文学谱系里的“经典”。但此种坚持背后是年轻一代所树立的经典(比如村上春树,比如卡波特)和过往的经典之间,有着视域和方法论的差异。作为始终活跃在文坛一线的作家、评论家、编辑,您如何看待那类尚年轻的经典和严格意义上的经典之间的分野?“严格意义上的经典”,本来也没有。我说的是,那种类似于哈罗德·布卢姆所说的,提供了意义、情感、形象、隐喻的经典谱系。在一种文化中,这是相对的常量,同时,它也不仅仅属于文学和作家,它是一个公共空间,在长期的阅读、交流和选择中形成,会有变动,但终究是,我们大家在深思熟虑后认为,这些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它证明了我们是谁,从根子上把我们联结在一起。
——这个意义上的经典,中国古代有,现代以来,恐怕还没有形成。你只要看看我们的教科书就知道了,不断在变,没有什么共识,没有相对坚固的东西。在布卢姆那里,是与经典的紧张关系,在我们这里,其实不存在坑爹弑父的问题,人人都是齐天大圣,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你所说的“经典”,只不过是作家的私人图书馆,它并不具备足够的公共性,只与作家的阅读经验有关,有时它可能来自一代人的阅读经验,但那也还不是经典,那是时尚,它封闭在一个人或一代人的记忆里,并没有在文化中扎下根去,向着过去和未来充分敞开。你觉得中国作家对这个时代的诸多表达(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等)中,欠缺对哪些深层命题的思考?在一个蓬勃又扭曲的时代,作家如何穿越复杂的描写,去抵达比普通读者所领悟的那个现实更为本质的现实?他不是“穿越”,而是要以复杂的感受力和理解力去抵达人的形象。当我们要做一个故事讲述者时,我们总会感到虚弱,似乎这个时代过于庞大,它已经提供了无数匪夷所思的情节。当今的小说家有句顺口溜:生活比虚构、想象、小说更神奇。这话十几年前我就听过,现在好像说的人越来越多。每当听到有人说这个话,我就从内心深处怀疑他:他还根本没搞清楚小说家这个职业是干什么的,他只是在说,这个世界也许只需要网站编辑或小报记者,而不需要文学。
我们忘了,《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等,很多小说都是从社会新闻来的,这根本不是什么新事,18、19世纪的小说家同样要面对那些稍纵即逝的、每天发生很快被忘掉的新闻,他们同样认为自己身处一个沸腾的、难以把握的、匪夷所思的时代,就像狄更斯那段如今被频繁引用的名言所说的,最好的、最坏的等等。但他们没有被吓住,他们意识到,在表象之下,还有更深广的事物,那就是那个叫于连的人,那个叫包法利夫人的人,这些人都比新闻要大,比新闻更为本质。我们现在可能是被表象吓住了,以致无法想象比表象更多一点的东西。
什么是“深层命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人心、人的基本经验其实所知甚少。这个时代的人是怎么说话的、怎么爱的、怎么恨的,怎么励志进步又怎么沉沦而自得其乐,怎么过着一重、二重、三重、四重的生活而自在无碍,我们的罪在哪里,罚在哪里,等等等等,昔日的小说家们面对的那些问题,那些人间的沉溺和虚妄,现在依然摆在那里,沉默无声。沿用断裂问卷里的问题: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你(作家)的写作有无重大意义?当代文学评论家是否有权利或足够的才智对你(作家)的写作进行指导?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作家宣称批评对他的写作毫无意义,那么,在他如此宣称的同时,就暴露了他是多么在乎这件事。用你提问的话说,批评的职责恰恰包括考量一个作家的写作的意义。批评家当然不是掌握标准或律条的法官,他只是把作品带到社会意识和文化场域之中,做出分析、解码和估价,任何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都逃不脱这个命运。当然,批评家经常说蠢话,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有时会很紧张,但正是在这种紧张和争辩中,社会获得了一种不断修正和扩展的自我意识。
抽象地谈论是作家更聪明还是评论家更聪明除了伤感情不会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结果。评论家通常写不了小说,小说家通常也写不了论文,这都没什么丢人的,他们本来就是做着不同的事。作为一名作家,又曾任中国最重要文学杂志的主编,您如何抵御过量阅读对自己(的写作)造成的创伤?你所说的过量阅读大概是指由于工作需要而读很多垃圾。那确实不是享受,但也不是你想象中的噩梦。尽管很多作者会感到恼怒,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你不必把一个臭鸡蛋一口口吃下去而且仔细品味才能断定该蛋是臭的。就我个人而言,一直有大量时间读很多并非工作需要的书。对年轻作家的三个忠告。我年轻的时候没听过谁的忠告,我想他们也不需要忠告。
2013年9月11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