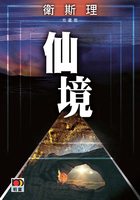建波的两个朋友都是刚结过婚的,也是喜欢玩笑爱凑热闹的人。来了都嚷着要看失而复得的宝贝是什么。建波笑而不语地拿眼瞟瞟吴宁。那两人就恍然若悟地大笑。吴宁说:“别听他胡说,没有得哪有失?”看到建波有点丧气的脸,又笑,“再说,我也不是什么宝贝呀!你们结过婚的不知道现在还拿不拿老婆当宝贝,没结婚时不都一样的甜言蜜语!”
“错!我们谈恋爱时就是大男子主义一个,哪像高建波这样柔情蜜意的!我看这小子已经被你驯服了——看来以后还不能让你嫂子们多和你接触。小吴啊,绝对是驭夫有术!”
“那当然,谁叫我老婆是那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人,”建波洋洋自得地笑,“所以说,错过我就等于把这世上最后一个好男人给错过了,”无视他两个朋友的夸张的取笑表情,用力握握吴宁的手,有点意味深长地,“亲爱的,要懂得珍惜知道吗?”
那两人就大呼身上要起鸡皮疙瘩啦,本来多少有点尴尬的一次吃饭,在吵吵闹闹中过去了。建波下午还要去单位,嘱咐吴宁要先去做个美容,然后可以逛街买件衣服,又凑在她耳边说“早点回去把咱们屋收拾一下,你要补偿我的哦!”
周围乍一冷静下来,吴宁倒有点无所适从。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好久,抬眼一看,却是走到那个本市数一数二的高档服饰卖场。她忽然想起皮包里那张卡,上面应该还有一万多元吧!她下定决心今天要去狂购一下——手机还关着机,明天再开机吧,这一关似乎就可以把与陈家生的一切拒之门外,不再有任何的牵连。她给自己买了两件衣服,又给建波买了套价格不菲的西装,用这个男人的钱给那个男人买衣服,多么幽默的笑话!她在心里狂笑自己。
建波的房间里堆满了啤酒瓶,吃完后的快餐面桶,一大堆没洗过的衣服横七竖八地被遗弃在椅子上沙发上。床头烟灰缸里无数的烟头一无数的吸半截就被残酷地拧进里面的烟头,无一不在诉说着主人苦闷烦躁和郁闷心情。吴宁一一整理着,心里有歉疚,也有凡懊恼:她该对建波怎么办?这是一个她需要负责的男人,要过一生的难道一定得是这个孩子气的,永远不可能有所作为的男人吗?
建波下班回来时,房间里已经窗明几净,饭也做好摆上了桌子。建波感动得跌脚大叫,说还是老婆好啊,老婆不在就迷失了方向,说着就唱起《情网》那首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做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歌星表情,去拥抱吴宁。吴宁忍不住笑了,这样一个顽皮的可爱的,让你无法不开心的男人呀。是的,她是爱他的,那种母性的温柔而疲惫的无可奈何的爱!
当晚,两人免不了云里雾里缠绵一番。建波匪夷所思的强悍激烈,他把她压在身下,在疯狂而猛烈的冲撞中,在她的痛苦而快乐的呻吟声中,他觉得舒畅无比。他觉得他胜利了,他多日来的苦闷烦躁似乎荡然无存了。这个女人,他想象中,仿佛在他强有力的进攻中已经被臣服,从此她将逃不掉,变成真正的他的温柔而忠贞的妻……
云雨过后,吴宁心平气和地说起这次到田雪家的所见所闻,单只拣好的说,比如他们的房子,家具,司机,车一一她无时不想刺激一下他的野心和勇气。建波很不以为然地说“你不能只看表面,幸福不幸福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吴宁本来想反击说他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想想田雪,也失去了反攻的兴致,心想建波有时也并非是毫无心思的人。
“吴宁,”建波说话了,她一听他这样叫她的名字,就知道是有慎重的话,“我想了,你明天去还是把工作辞了。咱爸妈手里有点钱,我想把它要过来,你自己选个项目做生意吧。你不是有经验吗?我相信你的能力。我会尽量配合你的,好吗?”
“现在别说这些!”吴宁转身背对着他,她不想和他面对面谈这个话题,但是她的声音里多了些潮湿的柔情。停了一会,她说,“你放心,我会想好、处理好一切。”建波够对得起她,够体谅她,可是,做生意并非他想象中那么简单,现在假若不是家生的钱,假若不是家生的实力不在乎那点钱,她敢这样冒险地去做吗?只是很幸运她成功了。假若是建波父母多年来那一点积蓄,她未必有那样的胆量了,赢得起赔不起,何况是他父母的钱!可是究竟怎样让他放心地处理好这一切,她心里没有底,只是她觉得总会有更折中的办法在前面,在那黑沉沉的未来闪闪烁烁地等着她,召唤她。
十一个她无法不爱的男人
第二天,建波走后,吴宁打开手机,数不清的短信叮叮当当地扑面而来,有建波的,她哥的,更多的是陈家生。“你在哪你在哪你在哪?”“想你爱你!”“如果你想让我死,也会有可能!”“爱你如果有错,全部都是我的错!”一个个的感叹号、问号像一枚枚的小炸弹,在她周身砰砰作响,把她心里那层刚刚坚固起来的硬壳炸掉了。她咬着唇不再看下去,摁着手机键全部清除掉。她起来,冷静地洗漱,打扮,拿起包,出门。
到公司门口,迎面就碰到家云。家云停住脚步,冷笑道:“你可真够潇洒!我哥住院了你知道吗?车祸!”
“怎么回事?严重吗?在哪个医院?”吴宁一下头脑慌乱,忘记了和家云的芥蒂。
“如果严重了,你就是罪魁祸首!”家云恨不能让眼中的鄙视愤怒窜出来,掮这女人几个耳光。如果不是哥的再三警告,她真怕控制不了自己。一个聪明的男人一旦在男女的事情上被迷惑,智商往往变得惊人的低。“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辞职吧,别在这祸害人了。我嫂子一直在医院,请你自重点!”家云眼中寒意飕飕。吴宁顾不得理会她,茫然地往前走,到办公室门口整理一下自己的表情,推门进去。同事们围着她问长问短——她对别人说是去考察一个上超市的产品,好不容易话题转到家生身上,大家都吃惊她的不知道,说是前天出的事,陈总开车不知怎的会闯红灯,然后为躲一辆货车撞到旁边的栅栏上了。伤得不算重,不过腿骨折了,打着石膏,头上也包扎着,一时半会儿估计出不了院。大伙都去看过了,告诉她地址劝她赶紧买点礼物去看看。
吴宁随便买了几样东西,往医院走去。今天是个阴天,老天也好像特别不如意,皱着眉愁苦着脸,把人的心都绾成一个疙瘩。他老婆会不会知道她和他的事?可是她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她要见到他,急切地,她要亲自看看他伤得有多严重,是不是她害的……
她敲门进去时,惠芬正坐在床头削苹果,得知她是公司的职员,马上热情地招应,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的。吴宁问伤得重不重,何时才能出院,会不会留下后遗症之类。惠芬眼圈就又红了——每来一个客人问到这些,她总是止不住会哭,好像那恐怖的恶梦般的事情就发生在刚才:“你知道我们家生平时开车多稳重!更别说闯红灯,还是大白天,我说真是遇上鬼了。改天我要去找个地方算算——幸亏没和那辆车撞上,那是个大货车呀!真是老天保佑,赶明儿我一定要上山去拜拜,如果我们家生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孩子们可怎么活下去……”
同样的话,见了无数的人,被重复了无数遍,还能保持同样的伤感动情。家生看着他的妻,他的苍黄的、柔弱的妻,两夜之间,在她好像经历了十年,连鬓角的白发、她的眼袋,都是那样的突兀和触目惊心,房间里似乎全飘荡着她的悲伤的、劫后余生的感叹,绕梁不绝,挥之不去。他抬眼看着吴宁,多天来第一次看到她,看着她玫红色的呢子大衣,黑色的高领毛衣,高高挽起的头发,她像一个熟透的水果一样鲜艳诱人。他叹口气:如果那天一个不小心,他死了,惠芬这一生就完了,可是吴宁还会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也许还会活得更加精彩……他回过神,对惠芬说:“你下去给我煲点鸡汤吧,嘴里觉得特没味儿。”惠芬惊喜道:“老天爷!终于想吃东西了,我马上去马上去。小吴你坐着聊一回,我一会就回来。”吴宁说她也有事很快就走的。等惠芬出去,两人一时没有了话。家生只怔怔地冷冷地盯着前方,吴宁说:“你怎么就那么不小心……”说完又暗恨自己明知故问。
“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个很果断的,也很冷静的……心肠也很硬的女人。”
“幸亏你知道得早!现在还不晚,嫂子很好很善良……”
“是的是的,一切都是我的错!”家生粗暴地打断她,少顷,他看着她的脸问:“如果我死了,你会伤心吗?”
“不,我会很高兴!”吴宁看着他,眼里全是笑意,笑容溢到外面,成了两条滔滔不止的河,“你死了,我就不用苦恼,没有烦心,没有痛苦的挣扎。我会安安静静地过我的生活,你说我该不该高兴?”
家生一把把她拉坐在床上,“傻丫头,你总是会把人心揉碎!”吴宁再也止不住,伏在他身上哀哀地痛哭不止。家生抚摸着她的头发。叹口气,“我不会让你委屈的,你回来就好,总会有办法的。”
吴宁把脸贴在他的手上,幽叹:“你说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吗——伤害不到爱你的人,又能长相厮守?老天总给我们出些没有答案的疑难题。”她把他的手放在唇边亲了一下,这是一个她爱的,也爱她的,值得她托付终身的男人。但那又怎么样,她不能嫁给他,不能全部拥有他,这是铁一样的事实,除非她狠了心——是他们两个人狠了心,作出所有人不齿的事,单为自己的自私的爱。如果,到时候这种爱也许会因为环境、别人的看法、孩子、慢慢趋于平静的激情,等等,有一点点的变质变味,那时他们该怎么办?她站起身,从包里掏出纸,把眼泪擦干,对着窗外说:“你不能这样,连自己都招呼不好,这样失去理智的男人,我会爱他吗?”她回过头,斜瞥着他,刚才还盛着悲伤的眼里露出她一贯的顽皮的挑衅,“你要是心里想着我,就赶快好起来,赶快出院!”
家生又恨又笑:“你调教男人真是有一套。我会马上好起来,”压低了声音,“你就是我的良药。”这些天失魂落魄的那个陈家生又复活了。他每每这样诧异自己:一面对她,那个在公众面前稳重寡言的他马上陷落到尘埃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活力、有激情、会说俏皮话肉麻话的生龙活虎的男人。
“我得走了,在她回来前,”吴宁看着椅子上惠芬的外套,也许刚才走得太急,连外套都忘记穿了,“如果我们还有点良心的话,永远都别让她知道。”她郑重地说着,同时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自责。
“别说了,”家生拉着她的手,“我会尽早出院,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天天。”
“你不要打,我会打给你的,”吴宁脱口而出。她不能不顾及建波的存在。看到他的阴郁表情,她笑了,“我给你打是汇报工作嘛,我会天天打给你,通过电波把药效发射过来好不好?”
家生看着她回眸一笑,拉开门飘然而去的身影,他觉得腿不怎么疼了,头上的伤口也许已经长好,待会他要问问医生今天可不可以拆线。惠芬把炖好的鸡汤提来时,他笑着说味道一定好极了,他都等不及了。惠芬看着老公津津有味吃饭的模样,有点诧异和惊喜。这么多天来,他一直是忧郁烦躁没有食欲的,今天一定是老天开了眼。她笑眯眯地,无限满足地看着他——心情好得绝对可以和家生媲美。
家生看着惠芬兴冲冲地忙上忙下,心里是愧疚的,在他内心阻挡不住的快乐中愧疚着。为了别的女人,把自己同床共枕十几年的老婆这样折腾着——在残酷的欺骗中,他一定要在别的方面加倍补偿她,如果人的寿限可以借出,他也会毫不怜惜地给她几年。可是,前几天他的失魂落魄是真的,现在他的快乐也是真的,他挡都挡不住的情感是真的——过去那个头脑清楚思路严谨的陈家生已经不复存在了。
吴宁走在路上想着一会要把几个超市的人员召集一下,开个会。元旦马上要到,她一定得想出更好的销售措施,她要很忙很忙地过一阵儿。晚上回去她一定会想好说服建波的理由——她有意识地把数不清的小事充溢整个脑海,她甚至有意识地让步履轻盈,把手挎着的皮包在空中翻飞了几下。她走过一辆小车,小车的玻璃窗像镜子一样清晰,她无意中照了一下自己,她看到一个眉眼间都是风情的女人——蔑视的风情,她笑了。是的,她蔑视自己,蔑视生活。早上出来时,她还是抱着坚定决心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完全两样了。一切似乎都不在掌控中,一切都可以瞬息万变,不管是合理的,还是有悖常规的,她想,都是有理由的。
建波晚上回来的时候,看到了吴宁的信。电话里她说晚上要去她哥家,给他写封信在桌子上。听到信他就有点悚然心惊,不会是……他早早地结束饭局回来。信是这样写的:
建波亲爱的:
我想了很久,做生意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也决不会拿你父母的钱去冒这个险。如果你相信我,我想再做一段时间,一是自己赚点钱,二来学更多的经验,到自己独立干的时候也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你还能等下去,我想最迟明年五一吧!也许到时我们会结婚,也许你还可以遇到更适合你的女人。现在,请给我足够的自由空间!我们都是自由的成年人对吗?我们都有理由选择任何生活的方式!我爱你,这是真的,可是你并不太适合我,这也是真的。但愿我们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你的吴宁
这是一封既让他笃定——她爱他这是真的。她已经决定五一可能会结婚,他毕竟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同时又让他不安一她有理由选择任何的生活方式!他知道这是一个他左右不了的女人,陈家生他见过,在她出走那些天,他躲在公司的门口看他出来开车离去。他并没有和她一起失踪,也许那些谣言只不过是人多嘴杂的嫉妒,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呀。他打听到陈家生是一个很稳重的并不花心的男人,儿女都那么大了。吴宁又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定力和判断力的平庸女子,她那么精明的人……不会的!刚才预报天气说明天阴转晴了,这在建波看来,明天就是个毫无疑问的晴天,绝对不会有阴天的影子——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一直觉得相信一个人比怀疑一个人更愉快。
所有的一切都按照吴宁潜意识下的设想进行着:建波妥协了,同意她继续上班,并且也给了她足够的自由,她暂时还住在自己租的小屋里;家生很快出了院,恢复了以前的干练和意气风发;吴宁的市场策划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她的小荷包第一次有了自己赚的鼓囊囊的钞票。他们时常有心有灵犀的约会,只不过在人前他们表现得更为庄重,行动更为周密,连眉眼间的会话都尽量避人。一边忙碌在生意上,一边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吴宁不是不累,却自信游刃有余,可是脑海里往往不经意间冒出些古训,譬如:多行不义必自毙之类的。痛并快乐着——已经是第二年的三月份了,这时候,连那快乐都被蒙上忧愁的面纱。这决不是长久之计,她时刻都没忘记提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