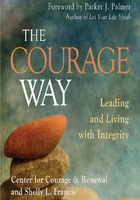刘双喜原本沉甸甸的心头肉被齐意昂一句话给拴到了平世剑上,他自己也把那迷茫困惑的年华,牢牢地系在了206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椅子上,从那天开始,他刘双喜,生是公司的人,死是公司的死人。
第二天一大早,刘双喜把自己那辆小货车驶出了公司的大院。车上载着欧阳大侠、王炸、老灶和大狼狗666,在大马路上披着新一天的光景,带着新一天的心情来到了县城的新城区,新城区里热火朝天的工地里总是洋溢着人们对于未来的无限憧憬,尤其是所有工地上最卖力的那个,心里面一定有个最美好的理想,哪怕它是个鼠头鼠目的外星人。
老鼠人停好了手里推着的小推车,用身上那件黄色的短袖抹掉了脸上的污渍,像是生怕来人认错了似的。老鼠人来工地上也没几天,但是它的努力得到了工地上所有人的认可,虽然长得丑了点,干得活可是一点也不粗糙。老鼠人甚至还拿到了工头汰换下来的衣服,有好几身,它最喜欢的就是现在穿在身上的这一套,浅蓝色的牛仔裤,绿色的胶鞋,黄色的短袖上面模模糊糊地印着一只大脸猫。
老鼠人第一眼看到眼前的四人一狗就知道这是来找它的。它脱掉脑袋上的安全帽,脸上带着期盼,心里惴惴不安。
第一个冲上来的是刘双喜,他取下背后的卷轴,抖出卷轴里藏着的平世剑,把只到自己胸口高的老鼠人按在地上,把平世剑架在它的脖子上,然后再慈悲地给了它说几句遗言的时间。
正在刘双喜得意于自己的无匹勇猛之际。一块砖头狠狠地拍在了他的后脑勺上,握着砖头的那只手的主人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的短袖,短袖上面印着一只大脸猫,穿短袖的人,正是这块工地的工头。
作为平世剑的传人,刘双喜的后脑勺当然不会输给一块平凡无奇的砖头,工头手里的砖块已经被碎成了好几块,而刘双喜的后脑勺仅仅只是发麻而已。就在刘双喜头皮发麻的时候,以他为首的四人一狗已经被收里拿着各种器具的人们给围了起来。
人们的脸上摆着一副最凶恶的样子。他们把老鼠人护在身后,把手里的钢筋铁锤捏得吱吱作响,只要这四个外来人有一点点异动,他们必定以命相搏。
就在双方都陷入了不知是进是退的僵局之后,老鼠人再次从人群当中钻了出来,双眼当中饱含着眼泪,耷拉着一双大耳朵,经过一阵感天动地的吱哇乱叫后,大概意思无非是它苦难的前半生,以及更加苦难的后半生。老鼠人抱着身边的工友的脑袋放声痛哭,哭声当中带着对这块工地无尽的眷恋,更让人觉得凄惨的是那声竭尽全力的回气,真真是把刚刚嚎出去的一辈子苦难都吸了回去,咽进肚里,让人忍不住地抹眼泪,想要把眼前这个外乡人当做自己最最熟络的好朋友。
老鼠人知道自己的一顿干嚎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他趁着工地上的众人都陷入悲痛当中轮回的时候,脱掉了身上的衣物,趴在地上,将欲逃走之际,被刘双喜一剑剁掉了那根胳膊长,杯口粗的大尾巴,痛得慌不择路,窜到了搅拌机里。
要说老鼠人倒霉,那是真的倒霉,但这地球上比老鼠人倒霉的人那可是繁不胜数,比如说刘双喜,仅仅几声干嚎,怎么可能动得了他坚如铁的心,要不是手里的剑耍得还不太顺手,那个老鼠人的脑袋早就骨碌碌了。是的,方才那断尾一剑,刘双喜是瞄着脑袋砍过去的。
搅拌机里面不仅有逃命的老鼠人,还有数以吨计的水泥,老鼠人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张开自己的尖嘴巴大口地吞起了搅拌机里的水泥来。
吞了水泥的老鼠人见风就长,一直长到有两层楼的高度才停下来,先前庇他周全的搅拌机,这一会也已经被他庞大的身躯压扁。变化后的老鼠人从嘴里吐出的浓痰,如同鬼魅一样裹住了还在为他战斗的工头,老鼠人那坨混着水泥的浓痰,把工头化成了一滩比例完美的水泥。
老鼠人用手抄起工头化成的水泥,向着四周胡乱丢洒,吓得他的工友们哭天喊地地到处乱窜,有那么几个跑得慢的,直接步了工头的后尘。
这里说的慌乱,并不包括来自206路公司的铁观音小队,三人一狗挤在小货车的驾驶室里,看着眼前的光景,面露期待。
期待的是持剑而立的刘双喜。刘双喜也不扭捏,心里谋算着给同事们来一场惊喜,用以确定自己在公司里的威望。只看那剑士在扬尘当中绝世而立,风轻云淡地切开扑面而来的一口浓痰,人随剑动,直奔不远处那只有两层楼高的老鼠人的脑门而去。动作倒是简单,只是跃空一刺,既不辗转腾挪,也不勾挑劈砍,剑尚未到,敌颅已破。
大老鼠的脑门上被切开了一个口子,喷洒而出的是灰色的泥浆。泥浆像是喷泉一般直上四楼,落下之后把大老鼠的身体化成一滩水泥,和先前那个倒霉的共同别无二致。剑客刺罢收剑,双手背在身后,完全没有去看自己刚刚一剑的成果,凌空当中一步一步地走了下来,大老鼠喷薄而出的泥浆像是怕了刘双喜一般,刻意地避开这位正在得意的剑客,不愿去触他的眉头。
等到刘双喜走到小货车前,不远处那只喷着泥浆,不断融化的水泥老鼠人如同得了恩赐的样子,霎时间凝固作一尊雕像,那是一个巨大而强壮的敌人,被点破眉心,生命喷薄而出。雕像的时间就停在了敌人最痛苦的那一刻,为的是彰显剑客的强大之处。
那位强大的剑客现在正站在小货车前。刘双喜的头发冲冠而起,一张涨红的脸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拼命地往一块挤,脖子上盘桓着暴怒的青筋。刘双喜原本的打算是轻描淡写地喷出心中的郁结之气,但当他眉毛将将扬起时,胃里突然一酸,扶着车头把前一夜吃得零零碎碎吐了个干干净净,到了这里好像是还没尽兴,又干呕了半晌,这才虚弱地回到了车里。
小货车回去的时候显得格外安静,开车的刘双喜满脸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