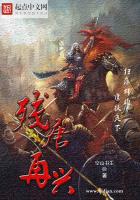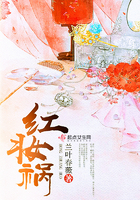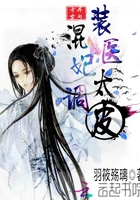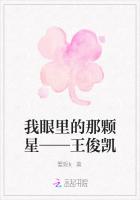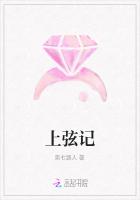县学的日子平淡而紧张,不知不觉间秋天已到尾声,小班新生们入县学也已两月有奇,诗赋的学习如常进行,方星河在黄教谕布置的课业之外另加了任务,每天背诵赋文一篇,诗作五首,日课二百字雷打不动。
诗赋读的越多,背的越多,文字的感觉越好,尤其是赋,只要积累足够,根本不惧考场。
诗赋的学习顺利推进的同时,五经的学习却出了问题。
随着《诗经正义》通经的结束,现在开始进入辨经的内容,辨者辨析之义也,也即是对五经主旨与经义的总体把握与探幽发微,从某种层面讲,学经学到这一步才算刚刚入门,同时也是士子们分水岭的开始。
方星河从未经过辨经训练的弱势瞬间显现出来,极大的遮蔽了他在通经过程中表现出的足以让人惊艳的见识。
譬如《诗经》第一篇的《周南.关雎》,在对其主旨到底是“颂后妃之德”还是男女情歌的辨析上,方星河就完全摸不着头脑,甚至感觉有些莫名其妙,这有什么可辨的,不就是情歌嘛。
他的这一反应引发小教舍内一片大哗,原来前两个月在通经中大放异彩的方星河只会拾人牙慧,死记先贤固有的成果而已,一到开拓便天分全无。
黄教谕目睹此状,再度轻轻摇头的同时油然想到了自己,这个他越来越喜欢的学子真是跟自己当年很相似啊,勤奋诚朴足以面对默经和通经,辨经上终究是差了许多。
但辨经又委实太重要,从做学问的角度而言,学经能否登堂入室乃至成为儒学大家,默经通经只是基础,最后的辨经则是根本,这一步跨不上来便是泯然众人,跨的上且上的越高就越能一览众山小。
即便不想成为儒学大家,只是在科举上下功夫,州学以下还没什么。州学以上,尤其是最后的礼部试,考经考的就是辨经,也只有辨经才能将来自大唐各地的佼佼者们区分开来。
简而言之,默经,通经是辨经的基础,辨经则决定了一个学子学经最终能达到的高度,不管是在学问上还是科举之路上。
方星河在辨经上迟迟进入不了状态,此前始终被他压着一头的周博文却突然逆势而起,表现惊艳。
关键的是白胖子每次意兴遄飞之际,还总喜欢喊方星河与之同辨,而后借方星河将他衬托的愈发光彩夺目。
这是周博文尽情驰骋的舞台,意气风发莫此为甚。
他越是扬眉吐气,便将方星河衬托的越惨。
一时间,县学内议论蜂起,众学子皆言入学考试时若有辨经,周博文必是第一,方星河胜在诚朴,但潜力已尽,难有长远前途;周博文虽则跳脱了些,但潜力深远,未来不可限量。
这一日,周博文又在课堂上好好让方星河给自己陪衬了一回,心怀大畅之下,放学便直奔柳宅求见表小姐。
柳家花厅,周博文刚坐定未久,白衣人与半个脑袋对视一眼后问起了他在县学中的趣事,经此两月,她们已经知道住在县学荒园中的青矜少年就是方星河,也知道他是周博文的死对头。
当然,这些消息也正是从周博文口中得知。
这事不问周博文也会说,何况开口发问的还是他日日魂牵梦绕的白衣人?
周博文呷了一口桂花饮子后当即绘声绘色的说了起来,把一场《周南.汉广》的主旨之辨说的天花乱坠,他本人如何旁征博引,探幽发微;方星河如何目瞪口呆,质木不文描述的绘声绘色,哪怕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
终于说完,有些口干舌燥的周博文看到白衣人凝神静听时微微歪着头的可爱模样,一时看的呆了,竟连桂花饮子都忘了喝。
半个脑袋“咕”的一声怪笑,周博文如梦初醒,素来在县学张扬自信的他竟难得的红了脸,白衣人没好气的瞥了半个脑袋一眼,“之前听你说那方星河通经功底甚是坚稳?”
周博文不乐意的点了点头。
白衣人微微侧着头陷入了沉思,周博文贪婪的看着,大着胆子道:“久闻表妹琴艺高妙,未知可否惠赐一曲?”
“你无琴心,性子也不合适,倒是琵琶更适合你”,白衣人一摆手,“我乏了,你也去吧”
周博文怏怏而去,直到走出柳宅时才高兴起来。以前屡屡求见而不可得,现在每次来都能见上,能在她面前享受这一待遇的唯有自己一人吧,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花厅内,看着周博文不舍而去,半个脑袋又是“咕”的一笑,“有人求着你不弹,有人不求你主动弹,可惜,那方星河竟是个笨鸟”
白衣人以手支颌犹如海棠新睡,“他能听懂我的琴,诵经和通经功底又不差,断然就不是笨鸟”
“那为什么……”
“周博文是有家学功底,方星河欠缺的则是点拨之功”。
白衣人自己点了点头,“对,就是如此。从通经到辨经本就不易,黄教谕本人的辨经功夫又差了些,导致方星河始终难以转换,若有人能为他拨云见日,他必能豁然开朗”
方星河自己也急,感觉一处不通整个学习节奏都被打乱了,一急一乱就难免心躁,连下午的功课都无法安然进行,索性离了县学奔县衙探望阿耶方之广,也算发散发散。
“钱叔,方叔,李叔,看到我阿耶了吗?”
县衙一进右侧院,方星河边问边随手将带来的桂花糕放在了桌子上,顺带拎起茶瓯给三公差续满了茶水。
“你阿耶在都头的公事房,坐这儿等等吧”,钱差官笑着回了一句。
自打方之广入职以来,方家小子已来过不止一次,每次来虽说带的都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但从不空手,脸上也是不笑不说话,这样的后辈当真是不喜欢都难。
方星河坐下静等,也不多话的听他们闲聊。
不一时,方之广回来了,两个多月时间过去,他脸上的蜡黄开始慢慢消退,整个人精神了很多,虽然依旧话少,但看他与其他公差打招呼时的样子,性格分明也开朗了不少。
方星河目睹此状倍感欣慰,看来当初的判断没错,阿耶以前脸色总是不对并不是身体有啥问题,而是干活太重伙食又太差的缘故,让他来做公差的决定真是太对了。
两父子出房说话,方星河先是问了问家里阿娘和小妹,得知一切安好后又问起了刚才的事情。
方之广如今只是普通公差,上面有班头管着,论理有事也是班头通知安排,都头直接叫人的情况可不多见。
“有个姓冯的名士要到咱县来,这人不仅名声大得很,跟州衙别驾也是好友,赵都头对此事很看重,调我在他身边随身护卫”
方星河放下担心的同时又起了好奇心,“姓冯的名士,冯什么?以何知名?”
方之广摇摇头,“都头没细说我也就没问,明天人到了自然就明白了”
“嗯,这差事不坏,至少比站在公堂上杵水火棍喊“威武”强,再则他那么大个名士,阿耶你都贴身护卫了,他走的时候好意思不表示表示”
方之广难得的笑了笑,看他笑一回真的很难,但这两个月倒是很见着几回。
方星河见阿耶诸事顺遂就准备再到雅芳斋走走,这是他当下唯一的收入来源了,有活儿没活儿都得殷勤着点儿。
方之广也没留他,从怀里掏出两吊钱递过来。
方星河愣了一下,随即赶紧笑呵呵的接过来,从阿耶手上拿钱这还是第一遭,那感觉就是美,接完收好之后才贱兮兮道:“阿耶你都会藏私房钱了,有前途啊!放心,我肯定谁都不说”
方之广脸上一抽,“你娘知道,另外家里雇长工的钱也够了”
方星河哈哈一笑,走了。随后到雅芳斋画了一幅画回到县学,却见县学里很是热闹,学子们聚在一起议论的都是冯子愚要来乐乡的事,一个个兴奋激动的跟什么似的。
原来阿耶负责护卫的名士叫冯子愚。
方星河慢慢听明白了,冯子愚乃江南道人氏,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读书时就以颖悟闻名乡里,后来成功出仕,先在秘书监,后来转入国子监任国子博士,五年前以母病辞官归乡,不及半年其母病逝为之守孝三年。守孝期满,冯子愚并无复职之念,读书漫游至今。
其人自幼好《诗经》,在国子监时同样专攻《诗经》,又经过秘书监中秘阁藏书的浸润,几十年功夫下来已经成为当今公认的治《诗经》大家。
这样的大神级人物居然会到乐乡县,且还明确说要到县学,难怪学子们跟打了鸡血一样,毕竟这样的人物本是他们不可能接触到的,就连方星河听完事情原委后也莫名的心热。
第二天上午的课几乎没怎么上成,大多数人都有些走神,翘首期盼着冯子愚的莅临,结果一整天人都没到,黄朴亲往县衙打探后带回个堪称惊天动地的大消息。
冯子愚会在明天莅临县学,并有意在县学中找一侍书童子为其舒纸磨墨,直至其离开乐乡为止。
此消息一出学子们彻底疯了。这个机会有多难得,里面又蕴含着多少可能性谁都清楚,所以得到消息后极短的时间里县学就空了一半,走的还都是家住县城的,不用问也明白都是找路子去了。
至于剩下的另一半大多都在狂翻《诗经》冥思苦想,希望明天冯子愚来讲学时能一鸣惊人,或许就此入了先生法眼也未可知。
方星河是极少数的例外,要路子没路子,总不可能为这事再去找赵都头,上次的人情都还没还呢,况且找了也未必有用,就赵都头的身份在冯子愚面前远远不够看。
至于一鸣惊人更是不敢想,在一个治《诗经》的宗师面前就他称霸的领域想一鸣惊人,方星河自忖没这个本事。
该狂躁的依旧狂躁,方星河回房读书写字作日课,一如平常。
冯子愚是在第二天上午第一节大课后到的县学,县令、县丞、县尉、典史、主簿、都头,县衙中但凡能叫上名号的全员作陪,阵势之大在乐乡县已是无人能出其右。
隆重的介绍过后,冯子愚登坛开讲,县学六十学子齐聚明伦堂洗耳恭听,县令等一应陪同人员散坐于四周同听。
开讲时间不足一个时辰,但其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处已将冯子愚的宗师风范显露无疑,众听者振聋发聩之余频频会心而笑,那种时时醍醐灌顶的畅爽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冯子愚前面讲的越好,开讲结束后众学子们越是激动难捺,对于成为其侍书的渴求使得明伦堂中好像燃着了一把火,气氛激动而焦躁。
到底是谁能成为这个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