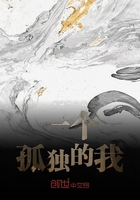小引:
《写于》这个题目应该曾经在我的日志当中出现过,但是不知为何被删除得一点痕迹都没有。我是个习惯守旧的人,往往能够通过回顾过往一些很简单的细节就获得很无比的感动。许多人称这种态度为虚伪,难道在你们眼中只有善于遗忘悲伤的人才是真实?又或则快乐才是你们做人的根本。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不再愿意解释和否认,因为在我看来,人最难得得不是对光辉的过往不能忘怀,而是在许多年以后,还依旧能够用过完的心思来对待过往的经历。当然这种现象,在某些人的眼里,会有另外一个称呼。固执。
有一次不小心在百度讨论吧看到了张敬轩在一次演唱会上关于这首歌演唱的一些故事,现在抄录下来,至于他说的方法是否属实和有效,相信比我更有眼光的你应该更能见仁见智:
“1997年开始,我在广州的一些西餐厅或者酒吧里边唱歌。我记得有一个星期,一位女士自己包下了一张台,点一些歌让我唱给她听。我收过她的点唱纸,她说:“我的丈夫因为外遇而离开了我,有什么歌可以反映我此刻的心情呢?”我想了很久,选了以下这首歌给她。其实,我希望在我唱歌的时候可以传递这样的信息给大家:无论是他自愿离开你还是因为有了新欢而离开你,这是因为上天觉得这个人还不是最适合你。当大家有类似经历的时候可以做的有两件事,一是听林忆莲的歌;二是等,等一个真正心爱你的人出现。”
恐怕自己有些得意的原因还不止于此,连丢了整整一年的日志都有办法找回来,看来我的《春城往事》要开笔并不难。
张彧,2012年1月20日,6时。
有人说,常听听音乐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觉得不一定。不然这个世界上的碟片就不止卖现在这个价钱。从来含着止痛药的胶囊是要比一般的胶囊要贵上一倍,或者以上。人之所以经常碰到不开心的事情终其原因是心里有太多想得到而得不到的东西。视这些“东西”的大小和数量而定,如果不足可以叫做不知足;如果很多,那么就是贪婪。但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不论大小多少都应该叫做孽欲。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一个人活在人世间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还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我身边太多这样反面的例子。于是看似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我根本找不到合理的答案,哪怕直到现在活了整整24年。其实一个人开不开心,或者痛不痛苦,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有时别人也会这样想,看到我们不开心或者不幸福,他们会无偿地拿来当做衡量自己幸福与否的标尺。说得难听一点,是被别人的感性利用了。但有朋友说这种态度其实是自我安慰,或者自我蒙蔽。这一点我承认,但不承认这是虚假。
因为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活着。至于有没有伤感的情歌或者如火如荼的恋爱经历,还是为人处世该闪出怎样耀眼的光芒,恐怕都是其次。
这个日志不知道会写到什么时候,但现在开了头应该就会一直坚持下去。我习惯早起,有时太阳还未出门,我就已经在上班的路上。每天路过那么多条不同的道路,看过那么多复杂的街景,我真的差点每天望着的这个人来人往的人世间,可以抵过一个城市的繁华。眼睛也许不会累,毕竟新鲜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但是心会因为重复关注一点而感觉到疲惫。关于亲情,在2009年结束之前,我曾默默地向大地和天空祈祷,愿我的亲人朋友,以及别人的亲人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关于爱情,却希望往事能够随风而化。越是接近岁末人的心越乱,当初许愿的时候知道这是个奢望,现在发觉自己不是神也无权给他们幸福,我竟还没有死心。
可我有心,难说有这个就已足够。但是说到底,“奢望”这个东西不好,看来害己,其实终究也可以终究害人。更何况这话是从我口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