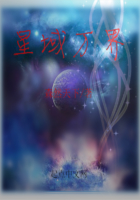春光探进了窗户,我一个人翻看着相册。忽然间,就有了新的发现:人在夏天拍照,满脸油汗,像从工地上刚下来,而且强烈的眼光让人眯缝着眼,样子像仇视;秋天作为背景也很不相宜,落木潇潇,心境苍凉,照片上的人面部表情像一片落叶一样无奈;冬天虽然可以手握一个雪球,有点情调的样子,可是,笑起来面部像雕塑。
只有在春天拍的照片最美。照片上,妻子对着一朵花微笑,似乎要与一朵花PK娇容;儿子像一条顽皮的小狗,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撒欢;而我在江南的一面山坡,右手握着一棵细细的毛竹,大有江河奔流青山不老的架势。
喜欢翻看相册,自己的,别人的,都喜欢。相册形象直观地记录了一个人的历史。打开尘封的日子,能看到一个人童年的稚气,少年的壮美,青年的青葱,老年的从容。在不同的年龄段,青春无疑是最美好的,像四季中的春天。一个人很难做到美丽一生,但要保证美丽一瞬。所以更喜欢一个人在明媚的春光里拍下的照片。
春天里江山美,人也美。在春天里,拍一张溢光流彩的照片,并且把这个美好留给未来,是一件“爱江山又爱美人”的好事。
一年一年与大自然做一个美好的约定,春天,我们踏青去,并且摄下美好的一瞬。可是,就冗繁中这点小小的愿望,也未必能够实现。
前年冬末,我与妻子相约在即将到来的春天里的某个周末去附近景点。接下来的情况是:要么妻子加班,要么我在赶稿,要么儿子补课。有几个周末是空闲的,三个人能聚在一起,准备出发时,天空飘起了淅淅沥沥的雨。终于,到了一家人可以在一条小河边一起说“茄子”。此时,春天已经走远。
春光是易逝的。这正如我们一生,很容易与幸福擦肩而过,而被烦忧苦苦追赶。悄悄地走过,静静地回想,心中又有多少昔日那些乐而忘返的深深陶醉呢?愉悦身心的事,总是习惯性地让我们觉得可以放弃,而把心灵的空间让位给一地鸡毛的琐屑。
今年的春天,我们去了此地风景最美的山中,心中感受到湿漉漉的春意。我和儿子一起喊“田七”的时候,妻子手中的数码相机却出了故障,春光总是这样恃宠而骄地折磨人。阳光很好,我说,就让太阳当相机给我们拍照吧。太阳一次次曝光,背景是青葱的山。而不远处的青草,正在掀起一场风暴。
我知道,我们还会来的。走进大自然的相册,一页页翻下去,一种迟到的觉醒,会让我们对着满目春意,对着蓝天飞鸟,一遍遍说着“茄子”。
大自然是一本相册。即便不带相机,都市里生活中的人们,置身绿色的背景,心境也会被蓬勃的春意渲染。你的倩影,会被绿水青山记住,定格在春天的相册里。
说出你的名字
查一路
人生有许多惬意的事。其中一件是,走在大街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未见面的熟人,一口能叫出你的名字。这给我们一个幻象:自己的影响力何等深远!自己给别人的印象有多深!虚荣心和自大意识顿时得到满足。全然不去想这可能跟对方的记忆力或者某件事有关。
偶然一次我走在街上,遇上了我初中的同学。他脱口而出就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心中一喜,毕竟时隔二十多年了。他说,其他同学的名字他大都忘了。我心中又一喜。并且鼓励他继续往下说。
他果然接着往下说,但接下来的内容让我大失所望。他说,之所以还记得我的名字,是因为在初二下学期,我借了他二斤饭票,一直未还。他一直想开口又不好开口,后来做梦都喊我的名字。所以对我印象特别深。
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别人记住,这是“我很重要”的心理结出的果。可事实上,我们的心灵并不是碑石,上面刻满他人的名字。罗素说:“要明白别人想到你的时候,远没有你想到自己的时间多。”生活就像河流,在流经生命的河床时,帮助人们吐故纳新。一个人不可能只固定在过去的记忆中,生活日新又新。
不久前,我们一群同学在母校聚会。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跑着,笑着,虽然嘴角长满了胡子。围在老师身边,还时不时还流露出当年的顽皮和天真。都争着问,老师,您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学生记得老师的名字,是因为在学生的一生,经历的老师也就那么有限的几十位,当然这不包括“三人行必有我师”中的“师”。而在老师的教学生涯中,教过的学生可能数以千计。学生就是老师的庄稼,一茬又一茬,他不可能记住每一粒麦穗的形状和大小。
老师在努力地回忆着,他唯恐想不起来而辜负了眼前热烈良好的气氛,和学生多年后仍记着他的情谊。我看得出白发的老师相当为难。说不记得吧,显得对我们印象不深,情谊不厚。说记得吧,他又实在不记得。想起老师当时尴尬与为难的样子,我至今于心不忍。
谁都想自己的名字传遍九州,自己的名字牢牢被别人记住,生命的半径强势地拓展出辽阔的疆土,这当然是人生的快事。可是,时间悄悄带走了记忆,平庸的你我,又何必要与他人的记忆力作梗,与强大的时间逆行,那是一种令人为难的情感挟持。
说出你的名字——这是多年后偶遇故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何须等待对方开动思维的雷达,搜寻“百家姓”中所有的姓氏来试探着与眼前的你对号。何须期待对方的记忆力带给你惊喜。
坚信他人的情谊,宽容他人的记忆。
对我一生很重要
查一路
看着他剖鱼,我无法容忍他慢腾腾的速度。只好反方向提醒,你的速度太快了,可能是这个菜市场最快的。他听了,直起腰,忽然眼睛一亮,你也是这么认为啊,刚才也有个人这么说,看来我还真是慢不了!我听他这么说,差点没笑出声来。
这位卖鱼的男人,苍白瘦削,矮小的身子弯得像一张弓,好像有重重的心思,言词间多有抱怨。
当他重新蹲下身,我看到了另一种速度。仿佛神站立在他的手臂。动作有一种超乎想象的飞快。又好像这种速度,在他的双手蛰伏已久,突然间爆发出来。
随后几天,我从他鱼摊边走过去,留心观察了一下。发现他的状态变化很大,他不再向人抱怨,而是埋着头,身子蹲等更弯,剖鱼的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专业,一招一式似乎都在渲染专业意识。我笑着走过去。
轮到我再次买鱼时,他很牛气地跟我说,他仔细观察了一下,整个菜市场就他剖鱼的速度最快。他奋力地努着嘴,说,不信你看看,你看看。当他蹲下身子的时候,想了想,停住了手中的刀,请我帮他一个忙。
我能帮他什么呢?我纳闷。他说,你能不能把你那天说的话,在我老婆面前说一遍。我点点头。他站起身,无限醋意地看着老婆和临近摊位的一个男人聊天,忽然大叫一声,拿个塑料袋过来!
词是现成的。我故作惊讶,你这人剖鱼的动作怎么这么快呀?是全菜市场最快的,你太专业了!他蹲下身,用动作配合着我的赞美。眼睛偷偷向一边瞥,享受妻子投过来的欣赏的目光。这样的场景,让我意识到,这男人特别在意妻子对他的看法。
几天后,他见了我,执意要送我巴掌大的扁鱼,我坚辞不受。鱼被重新扔进盆里,哧溜溜向前游去。他叹一口气,你那天说的话,对我一生都很重要。
我很他开玩笑,我是沙漠中发现了甘泉,荒山里找到了矿脉。他扫一眼妻子,说,我说的是真话,我老婆总是骂我一无是处,现在知道我很专业啦!对我的态度也比以前好多啦!
我劝慰他,我老婆也天天骂我。他摇头否认,扫一眼临摊的那大汉,说,不是你说的那种。我只能同情地拍拍他的肩膀,老兄,别想得太多!
这个瘦小又自卑的男人,我不便去揣测他是否陷入了一场感情危机,或者臆想中的妄加猜测,抑或深度自卑导致出悲观结论。但我知道,他确实需要来自外界的某种肯定。
苦弱的心,在黑暗中泅渡,需要一根意外漂来的横木,或者不经意点亮的渔火。
蚊子的死法
查一路
我儿子活捉了一只蚊子,欢欣鼓舞。为了讨点表扬,他启发我,你说,一个人的一生能活捉几只蚊子啊?更重要的在后面,他刚刚从一本杂志上看了一篇文章,叫《虐杀蚊子的七种方法》。他拿出镊子和小刀,动作犹如外科医生手术时那般精细,他告诉我,先把蚊子的四肢截断,然后再切除吸管。
本来,他想让我欣赏他的手术做得漂亮。不知怎地,我就说了一句,你那么大的人,和蚊子计较什么?
这下捅了马蜂窝。儿子的悲愤如洪水决堤,他说,去年春天我弄死了一只小鸭,你打了我一顿,我心服口服。可是,现在你说蚊子该不该死?他向我举起了拳头,拳头上一个大包,这是被伤害的证据。儿子很伤心,你竟然替蚊子辩护,难道你儿子还没有蚊子重要?
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蚊子是该死,但应该给它一个正确的死法。
弄死小鸭,是戕害弱小和良善;可蚊子作恶多端,怎么就不能行正义之名,以恶惩恶呢?一个孩子很难理解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可能源于近期一则新闻报道。
报载,龙泉驿区一对父子私设“公堂”审小偷。此小偷在前一次的偷窃中,立下保证书,如若再犯,甘愿拔掉三颗牙。不幸,小偷再犯,被父子俩逮个正着。于是,父子二人当众执行保证书,在鲜血淋漓中,拔掉小偷3颗牙,小偷哭爹喊娘,经鉴定为轻伤,父子二人也因此触犯刑律。不过,对此结局,二人不解且愤怒。
我并不认为小偷可爱。小偷固然可恨,但丢失了财物,并不意味着你就因此获得了“牙医”资格证。正义越出边界,同样是恶。
在我们的价值观里,从来不缺乏对于善的呵护,就此也容易达成共识。任何小善,被无限夸张地推上道德祭坛,也无人以为过。而对于恶的惩罚,在一片愤慨的声讨中,多数人大乱方寸,尺度无限放大,直至无所忌惮。
往往也正是在对恶的惩罚中,善良的心里,逐渐累积着恶,日后当这种恶释放而被惩,自己却感到委屈且茫然。因此,我不愿儿子的小手,从肢解一只蚊子开始,变得坚硬冷漠,变得不知怜悯和宽容。
“啪”地一声响,儿子说,送了它一个“安乐死”,这下你满意了?
是的,我感到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