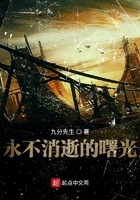纸上月光
查一路
仰望城市的星空,当最后一缕月光转背离去。留给我们的仅仅只有诗意的缅怀吗?
也曾经那样向往和迷恋城市,记得大姐第一次接我到城里看难得一见望眼欲穿的电影。记忆中那是一个永远芬芳的时刻。走在去影院的路上,夕阳把它的余晖抒情地撒在街道两旁宽大的梧桐树叶上,电线柱的大喇叭里播放的是柔曼的流行歌曲。黄昏的风和风里弥漫的气息是那样地令人熏熏欲醉。夕阳,晚风和歌声,使我敏感而多情的心第一次苏醒过来,像胶片最强烈的一次感光。
如今已在城市漂泊,在城市里读到尼采、叔本华,并学会了思考,却触及到了城市冰冷的内核,从而认同了英国诗人库珀的名言:神造的乡村,人造的城市。在一个城市浸入意识中的,是钢筋丛林的灰白色的冷漠,高层建筑的峡谷里,人们无休止地谈论的是物价和住房,期货和股票,IT和网络,基因和克隆。爱和美的过程被无限制的缩短,已很少有人关注与情感有关的事物。大量繁衍和复制的是,在高大楼群压迫下产生的渺小感和随波逐流的茫然感。
自然才是十分美好的,然而,城市已不允许我们轻易就那么见到十分美好的自然,见到远树斜阳、烟渚月流、寒林暮鸦、篱角黄昏、松窗竹户、芳径平芜、疏柳淡烟。城市阻隔和禁锢着我们的陶然向往。它只允许人们在百忙之中抽出几天时间,到有山有水的地方来个隔靴搔痒式的几日游。然后让人们带着眷恋依依不舍地回来,殊不知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现在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是城市割断了我们与乡村的脐带。
然而,作为一个固执的个体存在,厌倦的还是城市的矫饰和虚伪。城市里生活的人们都需要胸藏丘壑,兴寄烟霞,松下听琴,散发弄舟吗?亲切的柴门与炊烟,灶火与锄头,往往热爱起于怀念,而止怀念。对于物质的依赖,已使人无法走出物欲光环所笼罩的城市,唯一所能坚守的,只能是纸上还乡。
而另一个方面,城市的生活准则又太容易诱发人们对自己固有的道德和传统的背叛。损人利己即使在毫发之间,也已被时尚地当作精明和智慧大肆兜售,高尚的人格和品行自然日见式微。文明与落后的含义,已超越了城市与乡村的地域限制,在当今更具体地体现为个体所呈现的精神光芒。可是,人们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印象中,每一条通往城市的路,是康庄大道;而回乡的路仍然预备给游子漂泊后的失意。
乡村的事体还是那么沉重。我回到我热爱的故乡,乡村的声音微弱,相闻唯有鸡犬,青壮年劳动力已大批去了城市,大片的土地被抛荒。农民已不愿在田野收获希望,而是去城市追逐梦想。乡村,这大自然富饶的乳房,曾经原始地滋养了城市,现在已渐渐地干瘪下去,失去了生命力的博大和强健。
汽车行驶在回程的路上,灰白色的混凝土马路把坚硬和冷漠无限地向前方延伸,宽阔的道路还在向两旁的农田和庄稼地里扩展,路边应运而起的炮楼状的小楼房把钢筋和混凝土打向土地柔软的腹部。汽车——豪华的钢铁宫殿,飞快地奔驰,往来如织……
但是,我看到了道路两边的庄稼,坚韧地低着头,沉默不语,却没有半点后退的姿势,这是土地悲怆的对峙和最后的坚守。
冬日暖阳
查一路
冬天风大,摇着树的影子。我看见了三十年前的我,和同学们挤在学校前的一面土墙,用后背在砖块上蹭痒。昏黄的阳光笼罩大地。
操场一角有一位老人,戴绒线帽,穿黑色棉袄。他用红薯糖做糖塑,卖五分钱一只。一只火炉,火炉上一只铝锅,加热后的红薯糖,像柔软的琥珀,温润光泽。老人拿一只小勺,舀一勺糖,他抖动手腕,液体的糖从小勺中流出,流到铁砧上,铁砧上有一只竹片。围绕这只竹片,掌勺的手,时而浓墨重彩,时而惜墨如金。
竹片拿到手里,上端的糖塑栩栩如生,晶莹剔透。要么是花脸典韦,要么是手提哨棒的武松。这是位民间高人,他稔熟四大名著里的形象,用糖来一一勾勒。糖塑再好,无奈舌头贪婪,昔日英雄,几分钟后,终将在舌尖上落难。
一群孩子簇拥在周围,高举手中的五分钱。我挤在其中。突然,身后有人清晰地叫了一声:“查一路,你没有爸爸!”回身一看,竟是我的同桌,我踩了他的脚尖,没容我解释,他已经拔剑出鞘了。一下,就击中了我。
是的,这年的秋天,我父亲死了。这是我的疼痛和短处。我成绩优异,品行端正,长相清秀,老师喜欢。可是我没有父亲。我羡慕那些有父亲的同学,他们的父亲大都是农民,高大剽悍,孔武有力。扛着锄头在教室外巡视,透过破窗向教室里偷看,用目光打压他人,呵护儿子。
呆在那里,我试图抓住什么来抵御内心的疼痛。我没有哭,因为我没有哭的习惯。但无力反击,因为说不出话来。这年我才八岁。
老人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用小勺敲打着锅沿,又用小勺指着我的同桌,大声呵斥,臭小子,这么小就知道往人心窝里捅刀子,不要想吃我的糖塑,你滚一边去!他最终没有给他糖塑。
轮到我时,他递给我两只。举起其中一只,是举棒的悟空。这只很大,悟空刚劲神武,一棒冲天,横扫阴霾,是送给我的。放学的路上,我把它举起来,对着太阳。阳光透过糖塑照过来,深红的,暖暖的。我看了很久,风很大,人并不觉得冷。
我把它插在窗台上,有时候我把它拿到屋外对着阳光扬起脖子,阳光变成了深红色,暖暖的。我想把它留很久。可是,第二年的春天,它粘住了几只飞虫。母亲说,吃了吧。我舔了一个上午,吃下了一个冬天的心情。屋外,阳光热烈而凶猛。一切都会好起来。
人生的路上,我努力去遗忘别人曾经给予我的伤害,而将那点点滴滴的温暖一一攒起。积攒多了,心里就有一轮太阳。心中有了一轮太阳,站立在风中,寒冷来袭,爱与激情不会离我很远。
风雪夜归
查一路
这只老鼠太可恨了,母亲恨恨地说,也不知怎么的,最近闹出忒大的动静。它推倒了油瓶,咬破了米桶,甚至试图掀翻锅盖。
我去母亲所在的城市看母亲,正赶上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母亲命我去买老鼠夹,她要亲手将这只鼠给灭了。给老鼠夹小心地挂好猪油,母亲说,今晚就看好戏吧。睡到深夜,听得咔嚓一声脆响。
第二天,我和母亲都起了个早。上厨房一看,老鼠没死,鼠夹只是夹住了尾巴,这只大而消瘦的老鼠拖着鼠夹,像爱斯基摩人的狗拉着雪橇,叮叮当当在厨房兜圈子。我提出处死这只老鼠的各种方案。母亲听了直皱眉头。她认真地观察着老鼠。走过去。竟把它放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母亲决定的事总有她的道理,刚愎加上老年人的执拗,也容不得下辈置喙。我只好讪讪地说,这以后您又得遭殃了。
前不久,母亲的老同事来我这里。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母亲真是个儿女心特重的人啊,没见过她那样。
他说起了一件事,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次全县教师集中学习,散会的那天天下着大雪。因为会议延时,散会时已没有了班车,五个人说好了在旅社里歇一夜再走。可是你母亲突然想起来了,她说她跟儿女们说了当天回家,她说我的儿女在等着我呢,就是天上下刀子也要回去。说完就顶着风雪拔腿往回走。
我记起来了。那天我们确实等待了一个下午,夜晚又爬到一个山岗朝着母亲的来路张望。风雪几乎要将我们扑倒,姐弟四人只好拽住一棵树。就那样缩在树下等。见到母亲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在失望中突然欣喜欲狂,至今那种感觉我仍然能清晰地忆起。母亲为了在我们的等待中回家,走了整整八十里的风雪夜路。还记得当时我大姐说了一句,好了,妈妈回来了,天塌下来都不怕了。
似乎找到了答案。我打电话给母亲,提起了她老同事提及的事,并且问到了老鼠。我是想弄清,上次放鼠的事,跟她老同事提及那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是不是有着某种联系?
果然,母亲说,她头一天倒垃圾,在垃圾堆看见了一窝五只刚刚睁开眼的小老鼠,可怜又可爱,那天夜里她又似乎听到了小老鼠的叫声,第二天早晨她看到夹住的那只就是一只母鼠。放下电话前,母亲说了一句,可怜在风雪的夜里,小东西也像人一样等着它们母亲回家啊,毕竟也是生灵!
不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那场风雪夜归的图景,是不是一直印在母亲的心里。在儿女的等待中回家,这是被天下母亲们看得比天塌下来还大的事——也许就是母亲怜悯并放归那只母鼠的理由。爱,终会在生灵之间找到支点,并将超越一切功利。
秋风故乡
查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