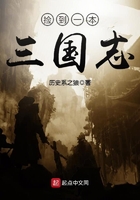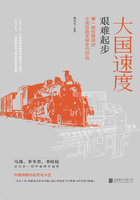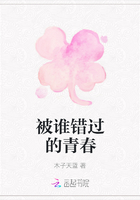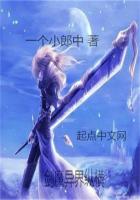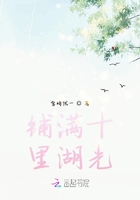乌衣巷,姜府,下人住处。
王伯因为夜里要打更的缘故,所以白天基本都是在自己的住处补觉。
人年纪大了,睡得不深,有一点响动就容易被警醒。
就比如现在,在床上小憩中的王伯就被屋外的开门声吵醒了过来,他在床上翻了翻身,又打了个哈欠,猜着应该是对面住的那位‘二少’回来了,本想接着再睡,可接下来外面传来的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却让他吓了一跳。
招贼了?
王伯从床上翻身坐起,等走到屋外,看对面屋子的房门果然大开着,声音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到这会儿王伯已经知道不是贼了,哪有贼开着门偷东西的,可又是什么人在房里翻什么呢?
------
姜洛回到府中住处,在床边怔怔的坐了一阵儿,脑中还是想着那让他欲罢不能的书。
好书就是这样,让人看的时候是一种感觉,等再回味起来又是另一种感觉,故事中的道理经得住人咀嚼,常想常有新滋味。
而这滋味又不免与现实世界产生反差,让人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在他二十载的人生认知中,他所生活的大明皇朝可是建立在四书五经上的国家,整个意识形态都在推崇道德唯一和道德至上。
朝堂无论是对社会规范的制定还是对官员的选拔任举,都是以道德教条做为取舍衡量标准。
如此治国,本应使社会民风淳朴,官员清正廉洁。
结果现实情况却成了书中叙述的这个样子,成了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的虚伪世界。
而这,也才是大明中后期的真实社会现状。
原因是什么?
儒家的道德明明大中至正,怎么用来治国以后却与它追求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
姜洛觉得自己应该知道答案,他的经历肯定给他了找到原因的知识积累,只不过这些知识太多太杂,他也没有汇总整理去分析思考,而这点疑问也只是在他心中打了一个小小的结,他并不是十分急切的想要解开它。
眼下想做的,却还是把那一整部书买回来。
钱是肯定没有的,但看着自己半屋子的书籍,想着干脆挑一些出来,去夫子庙附近摆摊卖出去换钱,反正也是翻来覆去看腻的了。
将来清兵南下,大难临头,这些不当吃不当喝的东西也只是累赘,还真不如顾得眼前痛快。
也就在他整理出厚厚一摞书本的时候,王伯就靠在门框处突然出声问道:“嘿,干什么呢这是?”
“这些旧书看烦了,拿出去换本新书来看。”姜洛回头望了一眼,嘴中随便答复着,手中已经拿了块布将挑出的书本打包。
王伯伸长脖子瞅了瞅那一摞书,又吃惊的看着他反问道:“你能从府里拿东西出去?”
一句话,让姜洛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是啊,要能拿东西出去换钱,自己也不至于穷困到如此地步。
原来他一些值钱的小玩意都被赵夫人收走了,他又住在下人处不往别人的屋子里走动,所以没人会防着他。
可今天他若敢明目张胆的拿这一包书本出去,姜府人多眼杂,事情必定会被传开,到时岂不是要被他们看成家贼?
而府中厌恶自己的人本来就多,他们有了这一题名借机刁难,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一时无法可想,心里的念想自然就断了,可他却也不知道该继续做些什么,手按在了摞好的书本上又放下,又按上,又放下,重复了几次,心里总是找不到头绪,最终一下子坐到床边,又发起了呆来。
------
日子约莫过了半月,这天上午,阳光明媚。
东麓书院一位年约三十多岁的授课先生从书院风风火火的赶来,于姜府府门处稍微驻足。
不过半盏茶的工夫,进去通报的门房连同家主姜育良便一齐出来迎接他。
先生与家主随即互相谦让着进了府中待客的厅堂,两人一边喝茶一边说话,一谈便谈了半个时辰。
等先生要走时,姜育良连忙叫管家安排车马,顺便再给先生封一锭银元宝做谢礼。而他,又亲自将对方送到门外。
不过与刚才进府的时候不同的是,先生依旧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姜育良却有些黑脸。
揖别之时,他歉疚的对先生托付道:“谭儿这孩子我只当他娇憨,想不到在书院中竟也如此顽劣。我平日诸事缠身疏于管教,只得还请先生多费心了。不求他将来有多大作为,只要有稍许出息,我必定以厚礼相谢。”
“为人师表,我自然会用心教他的。只不过今日实在是太过了,竟跟着书院里的一帮顽童闹起了罢课,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才不得不来对员外发发牢骚。”
中年先生负手而立,神态很是激扬,一副并没有把厚礼不厚礼的放在心上的样子。
“要知道今天可是大名鼎鼎的蕺山先生来我们书院讲学的头一天,他们这么一闹,让蕺山先生看了成何体统?再说员外家富贵有余,唯独不是书香门第,再有钱也只能捐个员外官,如何能跟正经科班出身的大员相比?我是想给员外家培养一位状元郎的,可谭儿若这般下去,只怕连秀才身份都保不住。”
姜育良的脸色又黑了一些,微低着头也不接话。
他知道这先生是看不起自己这样的商贾的,奈何他腹中确实没什么墨水,姜谭儿在对方口中又那般不堪,着实显得自己教子无方。
诚如对方所言,自家富贵是真富贵,但后继者里面没有人有功名在身,在文人眼中真是就要低人一等。
他出身社会底层的父亲,也就是姜府老太爷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财富积累,于南京城这样繁华的大城市中都可称得上是有钱人,靠的不是什么作贾行商、操奇计赢、小往大来等等正经生意人的手段,而是官商勾结。
而他在与达官显贵多年的交往中,也已了解到,在本朝的制度里,商人,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它不像文人能安邦,武人能戡乱,农民能种地,工匠能制器。
在统治阶层眼中,它是不能够创造价值的,而经商通过倒买倒卖的手段赚取差额,反而会抬高物品本身的价格。
这一群体,还会因为利润的诱惑,具有做出因利害义之事的隐患。
至于会影响本朝政治所追求纯善质朴的社会风气,那也自然也不在话下。
所以不管是制度还是认知,商人之外的群体都排斥和贬低商人,即使有必要的交往,也是为了取之于利。
除此之外,上层阶级不屑与之为伍,下层百姓又仇视商人说什么无商不奸。
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让人动心的利益开路,商人可以说是举步难行。
他让家中的孩子去学文识字,并尽可能的参加科考,既以说明他察觉到了商贾之家在本朝处于这尴尬位置的弊端。
家中没有官员,财富就是浮水,是别的官员的聚宝盆,办什么事也都要用银子说话,这算不上根基……
中年先生见姜育良只是静静的听着自己讲话,却不知他在想什么,还心说这老孺子倒比小孺子可教,起码态度并不像一些暴发户那般鼻孔朝天,便又伸手一指府门牌匾上的‘姜府’二字。
“员外,你知不知道一般人家是不能自称为某府的,这从礼法上讲就是僭越,若在明初那会儿可是要杀头的罪过。想我大明崇尚德教,伦理等级是第一紧要的。你看现在这世道成了什么样子?不循礼法,尊崇富侈,岂是一句人心不古能形容的……”
姜育良暗道你也知道在明初才要杀头,现在讲这些作什么,又不是我一家这么叫。
这迂腐文人,也不知平日对富人有多大抱怨,今日竟一股脑儿的讲给自己听?
听对方滔滔不绝听的烦了,他便开始左顾右盼起来,希望这已经而立之年的先生懂点眼色,能够自己闭嘴告辞。
不想这扭头一看,却见自家二小子正手捧着一本书念念有词的从府门处走了出来,那全神贯注的样子不由得让姜育良眼神一亮。
“阿难,快过来见过先生。”
------
姜洛拿着书本边走边小声读着,很像是卷不释手的学究模样。
他这几日一直这样,外人看着他是在刻苦攻读,真实情况却是在装样子。
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怀中其实还藏着一本,等到了外面将藏着的书卖掉,再读着书回来,目地就是为了攒钱买书。
现在已经有了三两多银子。
说来几本书才卖了这点银子也是由于他着急出售的缘故,不然慢慢卖,还能多卖几钱。
姜洛自以为这事情做的稳妥隐蔽。
其实,他若只一本本的偷拿出去倒还好,可这么连续几天偏偏要读着书往外走,却难免有掩耳盗铃的嫌疑。
这反常行为已经让门房觉得可疑并报告给了赵夫人,赵夫人想要知道姜洛在耍什么把戏,也安排门房今日等姜洛出去以后偷偷跟着去看看他都到了哪里,又干了什么。
此事儿要是被赵夫人捉贼捉赃拿个正着,那可就麻烦了。
却不想也就在今日,事情竟弄巧成拙,姜洛的装模作样反倒被姜育良当做了撑脸面的人样子。
姜洛眼中只看着书本,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小名,这才放下都有些发酸的手臂,抬眼却看到父亲正在几步远的地方向自己招手,便连忙走到了他们近前。
“这是犬子姜洛,家中排行第二。素来喜欢读书,整日钻研文章,先生瞧瞧是否可堪造就?”
“哦?虽是头次见二郎,但看他连走路都书不离手,但还真是副读书种子的模样。”
中年先生点了点头,对姜育良应承几句,又看向姜洛问道:“你平日都读些什么书?”
“朱子集注罢了,史书也是读一些的。”
姜洛随便答了两句,心中还想着今日把怀中的书卖了,若能凑够四两银子,就先买两册书回来过过书瘾。
“那在八股文上可下过功夫?”
中年先生问到了自己想知道的问题,若姜洛回答没有,那自己也依旧不用太看重对方。不钻研八股,纵使博览群书也只算得识字,因为只有精通八股才有考取功名的资格。而没有考取功名资格的读书人,在他眼里也只比目不识丁的愚夫愚妇强一点。
“学过一些,只是本领不强。”姜洛还是心不在焉。
不想中年先生倒是来了精神,略一思索便道:“我且问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两句话你用八股格式可能解得?”
这个倒是简单,虽然八股经常让姜洛头疼,但怎么说他也是累年攻读有文学积累的人。
此时他才专注了精神,按说自己真是鬼迷心窍,平日里总想让父亲刮目相看,这时有了天赐的机会,怎么还有心思想什么书。
在姜育良目光炯炯的注视下,姜洛略微在脑中组织了一下语言,然后才认真答道:“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
好!
中年先生暗赞一声,想不到这姜府二郎看着一副木木纳纳的样子,腹中却真有文采,这破题与承题竟答的很好,称为精彩也不为过。
姜洛继续缓缓说道:“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盖谓君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
好!
起讲就抓住了关键,想来后面的文章更加精彩,先生聚精会神的听着,生怕错过了一个字。
可这时姜洛却不说了,他注视着这年轻先生,眼睛里充满了疑问。
等先生与父亲都看向自己时,姜洛才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讪讪道:“时间仓促,实在是答不出来了。”
真实原因则是他把后面的文章给忘干净了,这是哪年的科举状元曾做的答案呢?
八股文无非就是按照‘朱圣人’朱熹的观点诠释义理,两句话的题目,据题立论要写出几百字的体悟理解,但翻来覆去所阐发的道理总结起来还是那两句话。
两句话能说明白的道理你要用一大段话再讲一遍,这就造成八股文的内容极为空洞。
这种形式化的东西对姜洛来说不但难写,就是连背都背诵不了一整篇,因为实在是看不下去,枯燥。
原本听得一头雾水,但又满怀期待的姜育良心中顿时不快,脸色更黑了些,训斥道:“你往常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怎么足与不足这么简单的题都答不了?”
他此时指望着这小子给自己撑脸面,生怕在先生面前再次丢脸,语气很是不善。
没想到先生却维护起姜洛来了,“不简单不简单,这破题承题答的很厉害了。再说这场合也确实不对,要知道科考时学子们都是一人独处一室,关上三天才能写完一篇八股,写出的文章还不一定精彩,令公子短短时间就能达到如此程度,足见才思敏捷,将来不可限量啊。怎么不送二公子去我们书院读书呢?难道另有名师?”
姜育良忽听自家小子在先生口中的称呼从二郎变成了令公子,心说你这就震惊了?可我还什么都没听懂呢。不过文人吃这套就好。
既然这小子能撑脸面,索性就让他撑足些。
“哪里有什么名师,只是犬子向来喜欢独处,所以才一直在家中读书。哦,对了,谭儿和他的一些同窗不是在闹罢课吗,先生不妨将我这儿子带去给他们开导开导。你不知道,阿难以前也是顽劣,只是这几年才肯发奋读书,想来必是有什么心得体会,他们同龄人交流一番,说不定也能让不少人改改性子。”
“呃…”
先生犹豫一下,想着带姜洛去书院恐怕没什么名目,难道说去授课吗?这么个年轻人去授课难免会让那里的同龄学生难以接受,不过他是真的看重姜洛了,又想多交流交流,最后便痛快答应下来,“好,那便与我同去吧。”
这时,老管家已经把要送先生回书院的马车连同车夫一起从侧门带了出来。
先生在管家手中接过姜府准备的谢礼,又被车夫搀扶着登上了车厢,姜洛随后也要跟着抬腿上去,姜育良却开口叫住了他。
“等一下,去书院这么重要的场合不可穿戴的太随意,去换身衣服。”
姜洛此时还穿的是过年时的那身衣服,虽然干净,但确实显得旧了。
姜育良对这身衣服还有印象,这么一回想就又想起了那一股让人反胃的臭味。
看姜洛望着自己面露难色,在人情世故上极为精明的姜育良略一想,便知道赵夫人应该是许久没有给姜洛添过新衣了,此时哪里能换得好衣服,便对在一旁的老管家说了一句,“带去韵亭那里。”
老爷一句话便让老管家明白了其中意思,他连忙带了姜洛又回了府中,在厅堂便让人找几个使唤丫鬟过来给姜洛梳洗打扮,又亲自到大少爷那里去借衣服。
大少爷白天基本都在外面店铺里学做生意,今日也照样不在家,院里就只剩大少奶奶主事。
老管家亲至,大少奶奶自然也不敢敷衍,仔细挑了一身玄色弹墨、绣有祥云纹彩的新衣给了出去,这是近日才新作的,姜韵亭也只在屋中试身了两次,还未穿出去过。
姜洛与姜韵亭身材相仿,穿上也基本合身,负责梳洗的丫鬟给他重新束发,又用带金丝的黑色绑带系住,腰间则也给他挂了两串玉牌彩珠制成的腰挂。
不过姜洛觉得太招摇,又让她们解了下去。
临出府时,姜洛特别托付老管家,让他叫人把自己原来的衣服和那两本书送回到下人住处,至于那三两多银子则带在了身上。
当在马车上等候的先生再次看到姜洛时,便吃了一惊,心说人配衣裳马配鞍这话没错,但这变化也太大了些。
短短不过一盏茶的工夫,这姜洛刚才还是看着老实稳重的读书种子,此刻竟成了光彩夺目的风流公子,真真是判若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