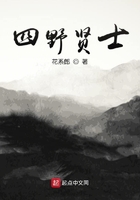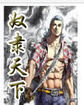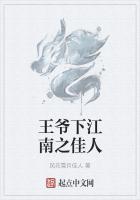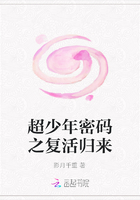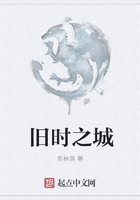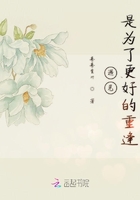太阳渐渐西落,天空却并不阴暗,而是呈现出一种明丽的蓝色。
市井传说中,由本朝开国元勋刘伯温所建的八臂哪吒城,在傍晚的阳光映照下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红晕。
偶尔刮过的晚间微风让万岁山上的树木轻轻摇晃,几只北京城内常见的小小灰麻雀便从某处树枝上飞起,互相追逐着,又漫无目地的翱翔于广阔无边的蓝色苍穹之中。
等它们飞到了一片鳞次栉比的辉煌建筑上方。
或许这片建筑的屋顶只用红黄两种暖色,让它们看起来十分的赏心悦目,带头儿的那只麻雀便于空中盘旋一圈,引着后面跟随着它的同伴落到了一座比较大的屋顶正脊上。
它们在屋脊上好奇的跳来跳去,无视于那些造型庄严的吻兽,甚至在对方的头顶上踩过时,它们此刻不会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的是。
踩在脚下的这座名为乾清宫的内廷正殿,乃是它们所生存的这个国家中身份最为至高的天子住寝和其处理日常政务的所在。
离天黑还早,宽阔九间,进深五间的乾清宫却已是灯火透明。
殿内,稳重厚实并雕饰金龙祥云的髹金屏风最为惹人注目,它的正中铭刻有‘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义’十六字楷书发人深省。
这十六字之下,就是下部以须弥座式为底座,承托上部为圈椅式椅背的龙椅。
身为大明国君的崇祯此时就坐于此上,端端正正的捧着一本书在默读。
刚到而立之年的崇祯皇帝在登基之后便再没有过过养尊处优的日子,长期为国事劳心费神,身子因此看着就有些清瘦,位于高大的屏风与宽阔的龙椅之间,就更不显得伟岸,这倒也与他眉目清秀皮肤白皙的面相协调。
只是脸上总似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忧愁,让人望之如玉山之将崩般动人心神。
正殿两边,各有一间暖阁,一处为天子的内房寝室,另一处则摆有书柜书案等文房家具。
一个当值的年轻宦官正伏在书案上轻轻的研墨。
当特殊的松烟墨香随着宦官手上的动作缓缓弥漫开来的时候,在一旁看着他的秉笔太监王承恩挥了挥手让其在一旁侍立,然后不发出一点声响的走向心无外物认真读书的崇祯。
“皇上。”
在离着有三四步远的距离时,王承恩放柔和了声音轻言一句,等确认自己不会突兀的惊吓到皇帝,才又迈步迎上前去服侍。
崇祯的注意力从手中书本上转移,先将书递给了王承恩,然后站起身来,原本只搭在肩上的织锦披风在滑落之前也被王承恩接过,又递给了见状碎步快走过来的另一名小宦官。
盘领窄袖袍的皇帝青色常服这时才完全显露出来,颜色已经有些发旧了。
“皇上,今儿个练字写些什么呢?”
王承恩将手中的书放在书柜上,熟练的又从一旁拿了本论语将其覆盖,掩住了那本书皮上的韩非子字样。
在其之下,还有《管子》《商君书》《慎子》等法家名著。
崇祯这几年常常钻研法家思想,但是这又不便让官员们知道,所以只是偷偷的读,为避免被人看到,王承恩在皇帝读完放回时便要做些掩饰。
“……写首诗吧”
已经站在书案后面的崇祯接过小宦官双手递来的毛笔,微微抬头想了想,然后落笔填下了题目。
哭,李,商,隐。
身为一国之君,其实并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能发展个人爱好,而官员们对皇帝的爱好也极为警视。
不正常的炼丹修仙、声色犬马、酒色财气、以及做木匠活儿,和正常的对经济、技术、军事等感兴趣,都被官员们给否决掉了。
基本上,上一任天子在反复学习儒家思想寻求治世道理之外有某一项爱好,他们在下一任天子身上就要对此项爱好加一道防范。
等到了崇祯这里,也就片刻钟的写写字练练书法能够被官员们所接受。
‘成纪星郎字义山,适归高壤抱长叹。’
遒逸秀润的字体在宣纸上落成时,多思多虑的崇祯皇帝不会想到,在遥远的南京城里,在几个时辰之前,有位名不见经传的商贾之子曾对自己暗暗做了一番评价。
那评价总结起来就是两条;
不知世务。
轻举妄动。
若是知道,崇祯却也只能接受一半,否定一半。
接受的是,那商贾之子确实把自己执政初期的行为看的透彻。否定的是,事出有因,责任并不能一味归咎于自己。
虽然皇帝作为国家及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最高负责人,出了事有被问责的义务,不怨天不尤人的态度也应是帝王应具有的基本心态,但是,现实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因素也不容忽略。
而造成自己不知世务的原因就要追究到成祖,乃至于太祖身上去。
因为他们为本朝设定的制度里面,有一条与其它朝代都不同。
那就是在先帝早逝,天子年幼的情况下,为了坚定的执行强干弱枝,杜绝帝室不被旁支觊觎的隐患,绝不允许让叔叔伯父一类的自家长辈帮着进行辅佐的事情发生。
因此,一些不能让外人所知的帝王心术在天家父子之间没来得及传授,或者传授的不完全时,这种心术就只能靠继位者自己去琢磨学习。
当年天启皇帝病来如山倒,从落水到驾崩连一个月都不到。他一个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年纪,继位之前又完全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帝王教育,又从哪里去懂得那些。
再说,天启皇帝自身估计也不懂。
登基之后,自己名义上的老师,也已经变成了自己的臣子,他们会教自己怎么制衡他们防范他们的方法吗?
不会的。
所以当他们要求自己要相信道德的力量,也就是要相信他们这些有道德的东林人士时,自己才会听之任之。
因为东林党人在印象中是那么的刚正不阿,他们当中那么多人为了践行心中的正义与使命,面对穷凶极恶的阉党集团,不惜以死殉道,怎么能不让自己感动和敬佩继而信任?
当他们所有人都说克勤克俭推崇德治就能中兴大明时,对政治还处于懵懂状态的自己又怎么能保持对此种说法怀有半信半疑的态度?
谎言重复千遍,就会被当作真理。三人成虎,岂容小视。
初登皇位,自己也由此而轻举妄动。
彻底铲除魏忠贤势力的同时,也促使了本就庞大的文官势力更加膨胀,使自己继承的这个皇位早就不剩多少的权力失去更多。
这情况和自己的祖父万历如出一辙,他的皇权不就是被首辅张居正夺走了吗。
张居正要祖父严格执行儒家垂拱而治的主张,他却握住了实权一点不放。他限制祖父的日常开支,以至于连赏赐宫女的钱都拿不出,他却占尽实利。
这与现在的大臣何其相像?
但两者却根本不同,并不会上演一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戏码。
张居正对上僭越皇权,对下压制官权,主要目地是为了实现心中的政治蓝图,开创万历中兴的局面,大体上并不愧对先帝托孤托国的遗言。
而现在的官员却多是为了各自的私利在做欺上瞒下的勾当。
‘词林枝叶三春尽,学海波澜一夜干。’
等终于发现无论再怎么学做圣人也于国事无补时,自己也就不得不摒弃旧有观念,并尝试开辟出一条新路。
原本被官员们说做苛政害民,让自己批判着看,最好不要看的法家思想,也就在那时对自己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
说起来,帝国的威胁无非就是百姓造反,外敌入侵,吏治败坏。
这三种威胁都需要诱因,需要生长壮大的土壤。
天灾频繁,贪腐严重,加征三饷,是百姓造反的土壤。
占据辽东,不断从大明掠夺百姓财富是建州女真发展的土壤。
官员结党,兵将自重,地方无约束,是吏治败坏的土壤。
现在是三者齐来。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试错,自己终于明白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统治阶层自身,也就是要进行政治改革,重新集权,对文武官员和地方官厅恢复强有力的管制。
不先解决这个问题,内忧外患就都无法解决。
因为朝廷连年用兵,外输建奴,内输反贼,把国家财政拖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国家没有钱,朝堂自身也不创造财富,要应对突然兴起的女真与流寇就要额外增加三饷税收以支持军事。
而本朝的政治制度中向来就缺少理财这一项,整体性的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地的改革也只有张居正执政期间做过,其它时间段内的主要政策则只是以维持被统治者丰年不饥不寒,荒年不至于饿死的低标准为目标。
所以广大的被统治百姓两百多年中从来没有富裕过,今日收粮,明日交税,留下也仅够糊口,因此他们是不能提供三饷来源的。
而国内能提供额外税收的就是商人与地主,但是因为地方吏治败坏造成了官商勾结的集体腐败现象出现。
像北方晋商勾结边军靠走私发财,南方浙商勾结东林党靠逃税发财,一个贪字,把帝国文武官员全部拉下水。
有了军政两层权力保护,不但额外税收加派不到他们头上,就连他们应缴的那一份也都被转移到底层百姓身上。
这就又逼返更多百姓,内乱更加严重,使对建奴本就不足的抵抗力量越发衰减,建奴一但入寇就能劫掠走更多的百姓。
内忧外患,是典型的乱世。
乱世无秩序,地方就更加无约束,对朝堂中枢的政令阴奉阳违就成为常态……
这是一个死循环,自己作为最高决策者和最高统治者必须要从这个循环中跳出来,以高屋建瓴的角度去整体的解决问题。
要釜底抽薪。
而这个让大明皇朝处于水深火热的薪,是百姓糊口的粮食,是兵将作战的给养,总结起来就是一个钱字。
大明并不是没有钱,只是钱不在它该在的位置。
边防军队因为领不到粮饷经常哗变,受灾百姓因为得不到赈济铤而走险,自己富有一国却穿旧衣服,帝国财政的收入与支出早已失去平衡,而这也说明管理帝国的整个官僚体系也已经腐朽不堪。
普通人要有钱,就要有权。
大人物要有钱,就要集权。
若要改变,集权是重中之重。
像袁崇焕初到辽东时,第一步也是在集权。他整肃军纪,厘清军饷度用,甚至直接把在军饷上自收自用又不听调遣的毛文龙先斩后奏,就是集权行为的体现。
不集权,他连下属都调遣不动,就更没办法兑现他对自己五年平辽的诺言。
可惜苍天不公,在这关键的时候偏偏让建奴长驱直入到了北京城下。
自己虽然对其没有能阻止建奴入寇的行为心生不满,但勤王大军中,却只有他所带的辽军能与建奴进行野战而不溃败,其它各部基本都一触即溃。
有如此鲜明的对比,自己不该也不会杀他,所以才在兵临城下之时还能忍着内心的不满将自己的衣服披在他的身上。
这就是向大家说明虽然他此时未能打败建奴,但自己却还是要继续重用他的。
后来那件事发生之后,虽有人猜测自己当时的行为是缓兵之计,是一种政治欺骗,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以皇帝作为天下表率的政治地位之尊崇,能明面做出的一举一动必然都要符合正大光明这四个字。
出尔反尔,言行不一,不是皇帝该做和能做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自己与他都不能得偿所愿,则是因为他犯了众怒,或者说是众人将对建奴暴行的愤怒发泄在了他身上。
建奴没有攻下北京城,却围着北京城烧杀劫掠了一圈,王公大臣乃至近臣宦官在城外的庄园因此被扫荡一空,他们岂能不对不能将建奴抵挡在关外的袁崇焕恨之入骨?
各种流言蜚语也就在那时层出不穷。
说建奴兵马是袁崇焕领进来的,说他在与奴酋皇太极私下议和,说他是建奴奸细,替建奴杀了伏在门口的一头叫毛文龙的猛虎……到最后,连普通百姓都对袁崇焕咬牙切齿。
袁崇焕犯了众怒,自己却不能犯众怒,守成之君的统治基础就来自于他所继承的帝国中官员与百姓的集体支持,支持者所共同主张的诉求,自己也不得不接受,更何况是在那个需要上下一心的时候。
判袁崇焕凌迟处死遂了他们的心愿,那些不明事理的百姓甚至花钱买他的肉吃来消心头之恨,真是可怜了他那‘忠魂依旧守辽东’的绝命诗。
逝者已矣,收拾山河的事情还要继续做。
但具体做事的方法自己并不比手下人清楚多少,能做的也就是官员的任免调用。
而集权的关键恰恰在于首辅的任免,因为自己不可能把全国的事情都做了,也不会做。不能都做不会做,就还要依赖文官帮助治理。
自己也不可能跟臣下打成一片,皇帝的权威在于神秘,要时刻保持表情心情的平静,不能让人看出自己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否则就会被臣下抓住弱点进行利用。
魏忠贤就是抓住了天启皇帝对做木工有浓厚兴趣的弱点,每当天启沉醉于做木工的专注状态时,就拿出政务问策,得到的回答也总是:‘朕要你是干什么的?自己看着办,别来烦朕。’
自己的哥哥因为这一弱点被一个太监耍的团团转,自己吸取经验就要清心寡欲,要表现的对什么都不关心。
不但不能痴迷酒色财气,就连国事都不能太过在乎,因为只有皇帝不做事,臣子才能做事。皇帝做事,臣子不做,那位置就颠倒了。
但很难呐,前者自己本就没什么兴趣,后者却实在不能视若无睹,嫂子都掉进水里要淹死了,难道还能眼巴巴的看着吗?还能忍住不伸手救援吗?
国家局势如此,心中焦急似火,中兴家国社稷的使命压在肩头,官员们却还在犯糊涂混日子,自己又怎么能够垂拱而治无动于衷?
这就又轻举妄动了。
这其中的原因是,自己能罢免不听话和不能做事的首辅,但就是找不到一个既听话又能做事的首辅。
首辅作为百官之首,有着至关重要的责任。
他在皇帝不懂事或者不是明君的时刻,要像张居正那样夺权并以国家为重。
在皇帝发愤图强励精图治要当明君的时候,就要放权以皇帝为主,并在百官与皇帝之间居中调和,讲明利害,使朝堂所发出的每一条政令都能获得双方的认可支持并严格执行。
可自己的首辅都是些什么货色?
听话的对自己马首是瞻,阿谀奉承,既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又让百官们所厌恶。
不听话的,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站在百官的立场反对自己。
还有滥竽充数,混吃等死的……
唉……一国天子,能换掉十几个对抗与糊弄自己的首辅,却换不上一个能真心为自己做事的首辅。
思贤若渴的自己也就不得不发出感叹: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还是隆庆皇帝有眼光,给祖父万历留下了能开创中兴之世的张居正。
反观自己的哥哥天启帝给自己留下了什么?
想以女色诱惑自己荒于政务,以使他继续擅权专政作威作福的魏忠贤吗?笑话。
‘风雨已吹灯烛灭,姓名长在齿牙寒。’
既然首辅不能带领百官刷新政治,就还得自己来,但开始却又用错了方法。
自己是学习理学成长起来的儒家子弟,就真的将理学的那套东西视为真理了。
也认为刘宗周说只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就能救国的办法没错。
就像齐景公对孔子说的那样: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即使有粮食,我如何能吃到?
是啊,那套东西确实对自己有利,自己是全下人的父亲,臣民都孝顺父亲,无条件服从父亲的指示,要钱给钱,要命给命,那治国有什么难的。
天下大乱,多因弱肉强食。要想国家太平,就要重振纲常。
这对自己来说是没多大困难的,自己的生活规范也从未脱离过儒家制度的指导范围,臣民们则需要进行一次警示,从而使三纲五常重新深入人心。
恰巧那时因为官员们的党争而被揭发暴露出了一个不孝的官员。
那官员名叫郑鄤,他的政治敌人说他用妖术逼迫父亲打母亲。
妖术之说实属荒唐,自己便派太监去调查真实情况。
原来郑鄤的父亲娶了一位小妾引起了他母亲的妒忌,他父亲为了教训自己的妻子就假借要以扶乩术来请示神仙看妻子嫉妒有没有错,该不该打。
扶乩,就是假装被神仙上身,拿笔在纸上写出所谓神仙指示的骗人把戏。
郑鄤饱读诗书,自然知道父亲的真实用意,就自己代笔请神仙上身,得出的指示是:虽然有错,但是不该打。
可他的父亲还是仗责其母。
这才给不明事情原委的人造成了误会,并被有心之人利用这误会进行迫害。
这人明明没错,还是孝子。
可那时自己一门心思的想杀鸡给猴看,希望抓个典型震慑一下世风日下的朝野市井,以为乱臣贼子戒,自然也就不能放过他。
自己想的是,你没错只要被人举报不孝都要被杀,那些有错的就更该要心惊胆颤不敢忤逆自己这位君父,那上下一心就能做事了。
政治,从来不在乎个人的公平与生命。而以一人之死给天下人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也值得。
为了以儆不忠不孝者效尤,自己判的是剐刑,割三千六百刀,比袁崇焕的还多。
结果呢?
不但没激发人们当忠臣孝子的决心,反而让不少人觉得自己残暴,觉得大明皇朝暗无天日。
‘只应物外攀琪树,便著霓裳上绛坛。’
事与愿违,却不是自己做错了,而是没找对原因,等再加深学习法家思想,才知道造成这结果的因素是自己的权威不在。
就像法家道破天机时说的,尧舜能治理天下是因为自身德行好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有专制的权威。天子的威势一但坠地,就跟能任人评价的凡夫俗子没有区别。
唐太宗李世民杀兄盗嫂,影响他治国了吗?没有。影响他创造出不输强汉的盛唐之世了吗?也没有。
他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就是因为他保持了不容质疑反对的权威,而不是靠自身的仁义道德。
问题就在于权威存在与否。
没有独断人间的绝对权力,就是尧舜在世,也连三户百姓都治理不了。
用势立威,用术御臣,用法制民。
皇帝无术,就受制于臣下。百姓无法,就犯上作乱。无术无法的国家,也就不能抵御外敌入侵。
这便是现在的根本问题,法家主张的皇权专制就此成为自己的目标。
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韩非子的五蠹中所讲,要像一个人用刀子割去身上生疮流脓的烂肉一样,将那些影响国家秩序的人进行肉体消灭。
文臣讪君卖直,欺上瞒下,损公肥私,要杀。
武将杀良冒功,拥兵自重,不听调遣,要杀。
地主兼并土地,扰乱地方,动摇国基,要杀。
商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追逐的利益不是皇帝与国家的利益,要杀。
读书人讲仁义讲道德,为了仁义道德敢于与皇权对抗,以求杀身成仁流芳百世,他们的行为都符合道德观念,但对皇帝的权力产生了威胁,要杀。
……
政治改革,要杀一大批人。
太祖为了政治稳定,消灭的异己和不稳定分子何止十万人?自己面临的情况比太祖时期恶劣多少倍?杀人难道要杀上百万?
可现在是什么时候?
以前没有流寇反贼和建州女真,他们除了受死之外确实没有其它选择,而现在如果表露出自己的意图,那他们岂能甘心受死?怎么不会投向反贼和建奴对抗自己?
但没有别的办法了,哪怕没有反贼与建奴,或者有折中的方法,自己都不愿做一个暴君。
可站在想要做事就必须要集权的立场,不如此做,又能怎么样?
好吧,既然有了目地和预见这目地所带来的后果自己能承受时,那就只差一个机会。
今年朝堂两线作战,杨嗣昌内剿叛贼,洪承畴外御建奴,只要两者一个能剿灭叛贼主力,一个能与建奴打成平手,就能实行招抚议和之策。
然后在大致稳定的环境中,通过权力的授受以及利益的分配,建立一个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体系,就能实现中兴大明的目地。
不,不只要中兴,还要超越太祖,使大明真正成为远迈汉唐的存在……
手中的笔挥洒自如,崇祯胸中却慢慢憋了一口气,等写出‘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一句时。
想到自己缺少的机会还没有到来,自己渴望至高无上的权威还没有获得,自己的中兴之事也因此还没有真正做过,思绪被拉回现实,胸中的气就突然散了。
以为自己总结出的方法正确无疑,恐怕会给后人留下一个刚愎自用的判语。
而出于现实考虑又不能将这方法马上付诸行动,也会被人说为优柔寡断吧?
可大明现在的情况是,不改则烂,改则乱,改革的时机与力度把握不好则马上会四分五裂而亡。
刚愎自用,优柔寡断……不身临其境,谁能体会这其中的难处?
朝中重臣也好,宦官内臣也好,他们都不明白,若是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都没了权威,那他们的权力与富贵又如何能保持长久?
一生襟抱未曾开……
老天……千万不要让我也一生襟抱未曾开,不要让这家国社稷在我手中就此断送……
“皇上?”
王承恩见崇祯写至此处便停笔久久不动,脸色还有些忧郁,忍不住轻唤了一声。
“屋里有些闷,朕出去透透气。”
崇祯烦躁的将笔扔给在一旁躬身伺候的小宦官,迈步便往殿外走去。
因春寒料峭,晚间更甚,王承恩怕崇祯着凉就先去要了对方刚才脱下披风,脚上就慢了崇祯两步,等接过披风回头一望时,却见说要出去的崇祯停步站在了殿门处向外面看着什么。
王承恩连忙跟了上去,一边给崇祯披上披风,一边也向外看去。
远处是皇太子与定王永王以及坤兴公主在一些侍女宦官提着绢纱宫灯照路向这边走来的身影,想来是给崇祯问安的。
晨昏定省是子女侍奉父母的日常礼节,皇室虽然更加隆重,但王承恩见得多了也不感觉有什么。
只是此刻夜幕已从东方逐渐笼罩大地,落日给临近的几朵乌云镶上了一层金边。
晚霞即将消失,如血残阳洒下最后的余晖,却将那些缓步而来的天家子女衣衫尽染成了红色。
这怪异的画面,让王承恩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
而崇祯心中也莫名生起了一种百苦难咽中夹杂着惶恐不安的凄凉感觉。
他的鲜血犹热,他的克勤克俭,他的中兴明室……这些抱负,这些年里支撑与折磨着他的身心。
但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独自坚持信心,静静等待时机的出现。
有志者,事竟成。
可无情的上天却做好了让他救经引足的打算,并为他与他的大明江山安排了覆灭的结局。
崇祯十四年的初春,他作为大明天子也已有十四个春秋,今后还有三年,等他在彷徨无措中用尽命运所赋予他做皇帝的全段时间后。
那么身为明成祖朱棣世孙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使想在他祖宗所建造的这片宏伟建筑中再多留一日,也是不能为时势所容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