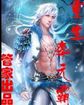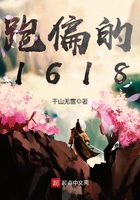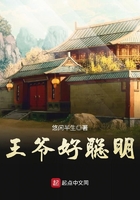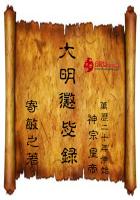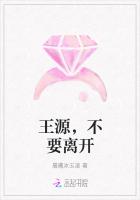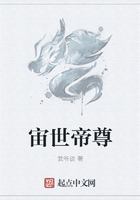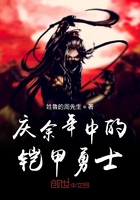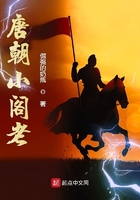事实上,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
自宋朝被金人用弓马刀剑驱赶到了南方,华夏的经济重心也就在那一时期完成了从北向南的转移。
而宋朝虽然繁缛,但相比辽夏金三国来说,在对百姓的态度上倒还算是宽柔。
因此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得,南方百姓就有了经济基础,便能做‘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长久性事业,等这事业积累起来,即造成了如今东南地区人杰地灵的现象。
明初时,洪武三十年的一场科举会试就将这现象进行了一次直观展示。
那次会试所录上榜的五十一人名都是南方人,北方士人则全部名落孙山,这种差异是历朝历代科举所未曾见到过的。
后来朝廷根据这种情况设计出了因地取士的制度,即按南六北四的比例选取考生。
但别看南方比北方多出了一成的名额,可南方读书人毕竟基数大,所以在这项制度中并没有得到好处,倒不如说是将原本属于自己那四成名额给强行分了出去。
是以,南方士人读书做官的机会变少,内部的竞争就越发激烈,个人发奋读书的上进心也被提的很高。
又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在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下能在南方读书人中被算作人杰的,就必须得要有真才实学方能被认可。
而现在,在场的这些人里面,其中不少更是足可称为人杰当中的佼佼者,不但是青年才俊文坛大家,很多还是东林党及东林党之后所兴起的各种学社中的领军人物。
再加上文人自古以来互相轻视的弊病,他们自然不会在姜洛这年轻人面前表现出一副虚心静听的样子。
实际上,他们若不是顾忌大儒刘宗周在场,而且对方还没有表明态度如何,其中有些人早就按耐不住性子要随着钱谦益对姜洛鸣鼓而攻之。
到那时,一个人要应对一群思维不一样的人进行激辩,基本就没有招架的可能性了。
也幸亏刘宗周没有表态,这才让姜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避免了舌战群儒的困局。
“好,从‘治’上来说,事情其实很简单。本朝军事不如女真,不过就是兵员和武器这两项因素所导致的。”
姜洛好整以暇道。
“武器因素就是造出来的刀剑一折就断,盔甲一捅就穿,火铳一点就炸。这只要杜绝贪腐所造成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并统一管理生产,严格控制工艺就能解决。”
大明军队所使用的武器除了朱元璋朱棣时期,质量差是很多人的共识。
万历朝时,明军在与建州女真萨尔浒之战前,督师杨镐要给出征的大军杀牛祭旗,结果拿的那刀又软又钝,捅了几次都没把牛杀掉,最后还是请出了皇帝赐的尚方宝剑才解决了杀牛问题。
而由不同铁件制作而成的盔甲是需要进行长期保养的,可就连堂堂京师武库所储存的盔甲也基本不保养,任其大量生锈。
等用的时候,兵将们才发现他们领到的盔甲一碰就坏,在战场上面对刀枪箭矢之际,这种盔甲除了消耗体力之外,基本不能增加任何防御力。
督师的刀,京师武库的盔甲都是如此,地方上就更不用讲了。
如果说刀剑盔甲是属于传统型的武器,那归类于战争新产物的火铳则更是不堪。
因为它从原料选取、制作工艺、验收标准上连统一的管理机构都没有,而是由全国各地的不同匠户作坊,选各种不同的原料,按各自的手艺制造出来直接供应军队。
这哪怕工匠们在制造时不偷工减料,其质量也会因为供应地和原材料既多且杂而变的无法控制。
原材料不一样,铳管的强度就不一样。
各作坊工序手艺不一样,管壁厚度和口径就不一样。
这对于使用不同来源火铳的军队来说,根本无法计算出统一并精准的装药量和弹丸尺寸。
同样的弹丸,有的轻易就能落入铳管,有的则要在战场上二次加工才能塞入。而同样的火药量装在不同的铳管里击发,有的可能没事,有的就会直接爆炸。
这导致火铳在战场上不要说是杀敌,能不炸膛把使用它的士兵崩死就算是上等工艺。
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已经开始普及火器的时期,高瞻远瞩的戚继光将军却依然只将火铳作为阵战之外的辅助武器,而不是视为划时代的,能改变军队组织及战争形式的利器。
原因就是戚家军所领到的火铳质量根本不可靠。
大明的火铳即使只在吓唬人上面,它给使用它的士兵所造成的担惊受怕,也远比给敌人造成的威慑力要大的多的多。
后世称为战争之神的火炮在大明也有此类问题。
像是本朝仿制西方的红夷大炮,北方生产的就跟南方生产的质量相差很大。
其中一个很重要但又一点都不复杂的因素就是,北方用煤炼铁,所以铁的含硫量高,炮管强度不够,而南方用木炭冶炼就没这个问题。
虽然制造铳管炮管在这个时代来说是大事,但也不是造不出来。问题是,明明能造出来,但却没造好。而且是有的能造好,但有的偏偏就没造好。
这种纯技术上的东西,就像姜洛说的那样,解决起来确实很简单,都用木炭冶炼不就完了?即使再有别的因素,那只要在统一管理的制度下持续改进优化也能够解决。
可惜在以追求道德的文官所治理的国家内,其工业并没有主动发展技术的可能性。
而文官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就是,既然南方的火炮质量好,那就从广东制造完成再往北方运过来就行了。
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
一句话说的容易,实际做起来造成的麻烦可就太多了。
……
“兵员则就困难一些,那要将陈旧糜烂的军户卫所制度彻底放弃。”
考虑到在程朱理学培养下的文人们对工业基本一窍不通,姜洛对导致武器不行的因素便一句话就带了过去,因为他对在后世所看到的数理化学科也是一知半解,充其量只能算知道那些东西很重要,是国家崛起的基础。
而且那些东西要靠大量实验进行证明,光靠嘴说,这些人未必肯信,所以解决方法也只说了要依靠‘人治’的管理,这样应该还在文人们的理解范围之内。
接下来说兵员,因为兵是活生生的人,而什么制度造成的兵员不行姜洛则就多说了一些。
“其实我们的军队不是不能打,那些将领的家丁就都很厉害。用同等数量的家丁和女真兵打,我们可以说是稳赢。
可是家丁是怎么养出来的?
假如说一卫有兵员一千,按道理说这一千人都应该是有战力的,可实际情况是,将领把其中的九百人贬为种地的农奴,一百人选为家丁,平时就只训练这一百家丁,因此有战力的也就只有这一百人。”
这时崇祯皇帝招吴三桂进京勤王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因此那个每年几百万辽饷就养了三千可战家丁的例子姜洛没法讲。
但是喝兵血造成军队战力锐减的案例历史上从来不缺,想来外面那些人对此也应当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姜洛觉得只笼统的对他们说说制度方面的因素就行。
“所以用一百家丁对阵一百女真兵,我们必胜。
可若是用一百家丁与九百农奴对阵一千女真兵,我们必败。双方交战兵力越多,我们败率就越大。
像是崇祯二年的女真入寇,女真兵加上蒙古兵还不到两万人就能横扫北地无敌手,尤其是在野战中,除了袁崇焕部还能与之抗衡一下,其余明军几乎都是触之即溃,因此就有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说法。
不管史书如何记载那是本朝王师与女真兵马的战争,真实情况却是我们一帮拿着破枪烂甲的农奴在抵抗人家职业化的杀戮军团。
女真人数极少,却能深入敌境不断创造以少胜多的战绩,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田忌赛马?”
“比女真更厉害的是倭寇。
嘉靖三十四年,有六十七名倭寇在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竟然敢攻打驻军十二万的南京城,之后他们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朗县,迫近芜湖,然后去袜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虽然本朝军队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终于在浒墅关将这几十名倭寇剿灭。
可他们流窜数千里,攻下过两个县城,杀伤大明军民竟在四五千人以上。
如此战力,呵。
女真满万不可敌,若倭寇满万,那我大明不早就亡国了?”
姜洛用尖刻、辛辣的话语嘲笑和讽刺着这一史实,并接着说道:
“可是,这不是我们人不行,是世袭制的军户卫所制度不行。
想想看,戚继光将军靠募兵制,招的还都是半路出家的矿工,怎么就能轻松击败从小学习武艺并曾在大明气吞万里如虎的倭寇?
事实胜于雄辩,只要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奖惩有序,一帮矿工都能胜过什么百年传承的将门世家。
改良兵制的效果显而易见,可朝廷就是不彻底改变,到了今日再来谈这些问题则已经太晚了。”
明朝的军户来源是只要祖先中有一人当兵,那后代男丁都要当兵,不能改做其它的,这种家庭就叫做军户。
而军户里面不光兵员身份是世袭的,就连百户、千户、指挥这样的官职级别也是世袭的。
就是说你当兵时是什么级别待遇,你就一辈子都是这个级别待遇,你的子子孙孙也永远都是这个级别待遇。
只要不立大功和不犯大错,军人职位在军队中就没有上升或下降的可能。
而缺乏了和平时期也能进阶上位与竞争淘汰的军队是会出问题的。
可这个死水一潭又非个人自愿的世袭军户制度在设立之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却是很满意的。
因为他出身底层又身为皇帝,知道朝廷在民间随意拉丁入伍时的残暴与国家发生战争时的花费之巨,所以就一刀切,规定军队只能从国家设立的两百万军户中产生。
朝堂给军户也不发粮饷,而是给土地使其归于卫所管辖,让他们一半时间耕种一半时间负责战备执勤。
但就由于军户有了土地,他们反而除了参军打仗之外,还要承担比民户更多的徭役赋税。
像永乐时期,国家一年从民户收税是三千六百万石粮食,而数量只有民户十几分之一的军户却要交纳两千两百万石粮食。
这可真是朱元璋说的那样: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岂止是不费米,还能收米。
至于这种既要马儿跑还要马儿贡献草的制度是否有持续可行性和合理公平性,我们的开国之君是不考虑的。
因为朱元璋皇帝设想中的国家就是一亩地,而臣民就是这地上生长的没有个人思想与追求的植物,把你种在哪你就长在哪,别谈其它的。
他还得意的对子孙说:我事无巨细,把维持帝国运转的整套制度都设定好了,你们完全不需要添砖加瓦和进行改动,轻轻松松的当个守成之君就行了。
把帝国完全当做自己的家业,殚精竭虑的为接班人设立一整套家国制度,不可谓不用心良苦。
可他越操心,为帝国种下的祸根也就越多。
他没有驾崩时候,被划为军户的百姓就开始大量逃籍。等他一死,尤其是到了正统皇帝被瓦剌俘虏之后,军户卫所制就再没顶过什么用。
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到北京保卫战开始,就是这套制度彻底崩坏的时刻。
对于这种传统军队不能打仗的情况,文官们对帝国军事力量进行补充的方法就是又弄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募兵制。
也就是朝堂通过授予将领特权,让他们可以自己征募训练兵员作为主要作战力量,这便是本朝军队家丁的由来。
这方法虽然保证了军队在作战时有能打仗的家丁应急,但又使得本朝军队整体战力低下的问题彻底固化。
而且,家丁是将领养的,忠于将领,不忠于国家,这种将领壮大了就可能会成为割据军阀。这就像客大欺店一样是明摆着的事情,在政治中对此没有一套合理的管制方式之前,是没有办法杜绝这种隐患的。
而且文官们也不相信粗鄙的武将会具有永远忠诚的高尚道德,他们的处理方式就是谁壮大了就打压谁,为国家立过大功的戚继光将军就是因此类原因被罢免的。
及至等到现在,已经实际成为军阀的将领多了,并不再甘心受文官的打压,文官们管不了也就又不管了。
……
能够神游后世的姜洛,在今日才被动的认真整理了一下他所处这个时代中的一些问题,越说的多,就越发觉得本朝的政治制度原来很多都是互相矛盾乃至于荒唐的。
这样看来,大明皇朝的行将就木也不单单是小冰河期与内忧外患叠加所导致的。
因为统治阶层为帝国所设计的规则很多都是建立在个人想象乃至于妄想之上的产物,它完全无法顺应时代发展。
既然政治制度不能与时俱进,那就要限制社会的整体进步,以免随之而产生的实际问题超出统治阶层的管理能力。
这是一套不负责任的办法,也是没有出息的办法,只求稳定自保,不谋发展,而且统治阶层还天真的认为这自保的办法有效。
就像乌龟一样,以为有了一个壳子,面对危险缩进里面就能应对一切天敌,却不知道有的敌人是能将它抓到万米高空再狠狠抛下摔死的,或者一铁锤将这看似坚硬无比的乌龟壳砸个稀碎。
落后陈旧的政治制度,就该被进步崭新的所取代,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大明皇朝自身不能去旧迎新,也就应该亡国。
只不过按姜洛他所知道的历史发展,破坏了旧制度的农民军所取得的成就是被建州女真窃取了的。
不幸中的不幸,这个国家因此还是走了老路,并且在不断退步,尽管她的名字已经从大明变为了大清。
“只要用本朝的政治制度与建州女真的进行对比,就能发现他们还处于从部落迈向国家的初级阶段。
这一阶段与秦朝‘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的状态很像,而他们的八旗也是为了实现武力征服所建立的,其组织结构以最大限度动员力量为优化目标,所以他们能征善战。
我们的朝堂则是为了实现皇帝集权专制而存在的,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以维持全国稳定、镇压内部叛乱、维护少数人的特权为目标,所以我们超级稳定,哪怕有皇帝荒淫无道或者几十年不上朝也不会被朝堂官员领导百姓将其赶下皇位。
建州女真的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都太少,内部也有矛盾,思想也并不一致,只要他们高层的决策出现重大错误,马上就会分崩离析。
我们的问题是军事力量基础不堪,而且分布太散并主要对内。所以即使本朝国土再大,人口再多,若不能将其变现为统一对外的战争实力就没有办法解决外患威胁。
两者虽然各有长短,但,以彼之长,攻我之短,如何?既然追求对内统治,对外就只能不断牺牲了。”
对于本朝军事不如女真的原因,姜洛用悲观的话语进行了最后总结。
说完,他亦是深深的叹了口气。
今日说了这么许多,他自己也了解到本朝的问题既错综复杂又积重难返。
此时他更加明确的是,若有人想理清头绪进行改革的话,那这人必须要有皇帝那样的合法地位与权力才能做,或者说就只有皇帝才能做。
因为本朝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皇帝要对这个国家的一切事情负责,而事情该怎么做也只能由皇帝进行计划布置或者许可他臣僚们的建议。
张居正僭越皇权去搞改革,本身就违背了君主专制的设计,所以等皇帝要求文官们对他的政策进行纠正时,他的事业与家族就都完了。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都不行,普通人若是处于文官集体之外的身份,又没有皇帝独断人间的权力,还想着学他行救国之举,那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也是为什么姜洛会将保家卫国这种事认为是不切实际想法的根源所在。